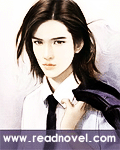阳光穿透毕业的日子全本 姬流觞-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谢亦清似乎卸掉了什么重担,神色轻松地讲着带团的经历和挣钱的技巧,甚至说到了团员们给他介绍的种种赚钱的行业。我听出他有创业的想法,但是这又如何呢?不一样是辛苦劳累吗?我看不出任何区别,只看见他白皙的脸愈发苍白,尖尖的下颌越发尖锐,就连原来婴儿肥的两腮都深深地陷了下去。
“你瘦了。”我突然冒出一句话,打断了他的眉飞色舞。
他愣住,我亦愣住。
这是句很暧昧的话,通常用来表达关心,但我却想的是另外一层意思,一层不打算说的意思。
“还是胖点儿好。”我赶紧加上,试图淡化自己本意中的刻薄。
他摸摸脸,半晌才说:“是吗?没,没太注意。”
我本来想告诉他“君子不重不威”,我本来想刻薄他“你现在变得和电视里的奸贼一般”,但听了这句话后却突然截住了,听着他口气里的辛苦……算了吧。
他喝了口酒,“出来太久了,习惯了。”他按按脸颊深陷的大坑,“我四年……没回家过年了。假期是旅游的旺季,回不去。”
“是很辛苦。”
“那天你来,吓了我一跳。知道你直来直去,可不知道直成这样子。”
“我知道,我不够含蓄。”我一直很期待能和他讨论一下那天的情况,但是真的碰到了,却不愿再提。是不是女人都是这样反复无常?
“没想到你能为了我进北京……真没想到。那天,你说要回家,我,我以为你不想来北京了。”
“是吗?”我斟酌着,因此你决定分手,毫不留恋地分手?这大概就是薄情吧。幸亏那天没跟你有什么,若是真有了,还不知怎样后悔。
我谢天谢地,谢谢祖上积德,在关键时候让我想起了那句话——始乱之,终弃之。太容易到手的东西,他不会珍惜。
我把菜推到他面前,完全是公子润带给我的习惯。他吃得比我多,又是个漏嘴子,菜盘越近越好,不然桌子上肯定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谢亦清停了一下,说:“当导游的时候,都是客人们一大桌,我和司机一小桌,菜就那么点儿,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团员有什么事随时就把你叫过去,如果有孩子,你还得先帮着人家看孩子,等你吃的时候,大家都吃完准备走了,根本吃不上什么。唉,四年了,都是照顾别人!”
“嗯,我在学校也接过地陪,见到过全陪,很辛苦,什么都得操心,累得不行。”
“你也做导游?怎么没听你说过?我以为……呵呵。”
“我在的城市就是旅游城市,没道理不做导游啊!不过,我不常做,给老师和朋友搭把手而已,不像你这样。”
“嗯,其实导游也是挣的辛苦钱。这个行业现在竞争很激烈,也不规范。我打算捞到第一桶金之后就转行。”
“转行?”
“对,我想做国际贸易。”谢亦清说起这些事的时候,神色是我从没见过的凝重与严肃,整个人甚至都闪闪发光,“北京是个很不错的口岸,而且笑纯的爸爸有很多关系。我们不需要去开拓市场,他们有很多现成的业务。”
“等等,开一家进出口公司……有很多限制吧?”我约略知道一些,不知道他哪儿来那么大的野心。
谢亦清说:“没关系,我们可以挂靠在一家大型进出口公司下面做自己的业务。我刚和笑纯的爸爸谈过,他很支持我们创业!”
“你……刚谈过?”我听到自己在乎的内容。
谢亦清愣了一下,场面突然安静下来。
随即,他有些磕巴地说:“嗯,我见过……”
我挥挥手,自嘲地笑了笑,“没什么,我觉得你的想法不错。不过我不懂国际贸易,英语也不好,可能帮不了你,但咱们是同学嘛,总是支持你的!”
一下子,我们的关系从男女朋友就退到了同学,如此的轻而易举。
我以为他会有些尴尬,可他似乎松了口气,竟顺着我的话说:“对,同学,呵呵!”
女生想做女王,把天下的男生都变成衣橱里的衣服;男的想做皇上,把所有的女子都关进后花园。时移世易,开学之初我努力要实现的暧昧竟然在绕了一大圈之后如此轻易实现!
只是主体发生了变更,是谢亦清而不是我想要这种暧昧。
落地的玻璃窗外,北京的夜空看不到星星,也没有涛声。天地连在一起,大楼似乎在不停地旋转。我突然觉得一个学期之前的我遥远得好像一个被玩旧的布娃娃在某个角落落满灰尘。如今不过是偶然地一瞥,只勾起些似是而非的回忆。
疲劳地躺在床上,大家都睡了,周围传出沉沉的鼾声,我问自己:“为什么要纵容谢亦清的暧昧?”
我肯定不是感情高手。在与谢亦清的角逐中,我始终被牵着鼻子,一脚踏进去。
现在,我习惯了,习惯有个男的在你耳边说着不靠谱的话,习惯有个男的眼光躲闪着和你聊天,习惯有个男人天天规划着没有你的未来。可习惯了,就很难改变。
我希望天上掉下一块石头把他砸死,这样我就不得不放弃习惯了。
说清楚?不,我算计着是否有翻盘的机会。
和谢亦清见面后,又恢复了每天晚上通电话的习惯。我似乎不是在谈恋爱,而是在玩一场智力加情感的游戏。刻意地逢迎和猜测,我发现自己真是善解人意!
也许有一天他会放弃这份暧昧,求着恢复以前的关系,到那时,我就很女王地告诉他:“不。”
这只是一种假设,没想到却来得很快,快到各种先决条件都不具备,我自己已经主动说了。
在我还有一天结束实习的时候,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澄清了一切!
唐笑纯坐在我对面。
就在我们宾馆的咖啡厅里,很气派地点了一份卡布奇诺。
“你要什么?没关系,别客气,我埋单。”她跷着二郎腿,包裹在牛仔裤下的小腿显得更加修长。谢亦清抱怨过——自豪地抱怨过,她穿牛仔裤非里维斯的不要。
“白开水,谢谢。”我穿我妈给我买的衣服,干净整洁就好了。就像白开水,自己舒服即可。
“来份苏打吧。”她招呼waiter(那是我的同事),神态倨傲。我觉得她想模仿什么,可是道行差了点儿。毕竟我在宾馆工作,就算只有几个礼拜,但各色人等多少都见过一些。
我的同事比我见得更多,他们甚至看出我和唐笑纯近似谈判的架势。后来他们告诉我,一定不会让那个女人得逞的!
“我的杯子,谢谢。”我告诉同事。
同事送过来一份咖啡,一只装满菊花和红枣的杯子,“对不起,我不习惯用别人的杯子喝水。”
“难道你们宾馆不消毒吗?”唐笑纯一脸的厌恶。
“不是。我有精神洁癖,想起这些杯子被不同人用过,我就恶心。纯粹是心理原因,和现实无关。呵呵!”
我们针锋相对,实在是因为唐笑纯来的第一句话就让人生气。“听说你要走了,我代亦清来看看你。”
你是何人?有何身份?
就算我和谢亦清从朋友降格成同学,他似乎也没有告诉我你是什么人!
“你知道留京有多难吗?”唐笑纯开始念经,“要是党员,是学生干部,还要连续拿奖学金,像我们学校如果不服从分配自己找留京单位,还要交一笔赔偿金。唉,你们这些外地的学生是不会知道的!”
我笑着点头,“的确是。”这女人有很强的表演欲,就让她露一手吧!
“谢亦清能每年拿奖学金就不错了,他还要挣钱准备赔偿金,就根本做不了学生干部。他要留京必须自己找,通过学校留京是不可能的。”唐笑纯夸张地瞪大了眼睛,我发现她虽然是小眼,却似乎有甲亢的后遗症,眼珠子有些往外暴。难怪那天要戴墨镜!
“是吗?我以为他是万能的。”我喝了口水,对自己不厚道的评价翕然一笑。
不过唐笑纯显然没听我说话,自顾自地说:“就算留京了又怎么样?你喜欢读书,一定知道‘京城米贵,居之不易’的古话。就算现在社会条件好了,可大家都挤破了脑袋要进来,没点儿本事也只能做社会底层!”
有人因出身而富贵,有人因特权而高傲,难道还有人因城市而鄙视别人的吗?那人类百年的民主斗争简直都是白瞎了!
唐笑纯一定是憋得太久了,喋喋不休地讲着,“亦清是个有头脑、有本事的人,我喜欢他有目标、有行动力,我相信他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一定会做人上人,所以,我会全力支持他。”
我有些不耐烦,“嗯,是吗?没看出来。”
唐笑纯不高兴了,“嗤!平时亦清就跟我说,你是个混吃混喝的人,连发稿子都靠亲戚关系。不过这次你能来北京实习,可见你家里也很有关系。但是,我听亦清提到过你的父母,好像就是大学里的教师,哦,对了,你妈妈只是中学教师,父亲好像还不是教师,是搞后勤的?能给你在北京找工作吗?”
吵架、打架只管放马过来,别捎家带口的,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我绷紧了肌肉,慢慢地放下杯子,“不能。”
唐笑纯咄咄逼人,“还有,你懂不懂留京和打工的区别?”
我垂下头,“不懂。”
她有些得意,“留京是要有户口的,是北京人;打工没有户口没有福利,和民工一样。你父母给你找的工作,是留京还是别的?”
我的实习机会就是父母找的,这一次我没有可以反击的武器,抿紧了嘴巴,因为我不想说得太难听。
唐笑纯显然不需要答案,“哦,对了,亦清说你是很有个性的女孩子。你要自己找吗?这个社会是很复杂的,很多女孩子找不着工作就进酒吧、宾馆了。唉,你是实习,不知道北京的宾馆里都干什么,脏着呢!反正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不远处有我的同事,他们的脸色非常难看。即使我同唐笑纯不对盘,可她说得太过分了,难保不会被人记在我的头上。
我提醒她,“谢谢你,不过这里就是宾馆,我和这里的人相处得很好。他们很友善也很正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这个话题不要说了。你还有别的事吗?”
我相信自己的脸色非常难看,因为我已经准备起身了。
唐笑纯往座位里缩了一下,似乎不想走,缓和了脸色说:“对了,你知道吗?为了你我还被亦清他们宿舍的人埋怨。”
我略微放松,低头喝自己的保养水。
她继续说:“那时候我和亦清闹别扭,他正好准备给你写信。他们宿舍的都知道你是他同学,就起哄让他追你,说你肯定不会答应,至多气气我。信寄出去以后,他们还讲给我听,说亦清给别的女孩子写情书。呵呵,内容都告诉我了——I will spoil you forever!对吧?呵呵,这话我都听腻了!他们跟亦清打赌,说你如果答应就每人输给亦清五十;如果你不答应,亦清就付给他们五十。亦清是个争强好胜的人,那信写得一定很动听吧?呵呵,我听的时候都有点儿动心呢!结果,你不仅答应了,还在第一时间赶来,害得他们每人付了谢亦清五十块钱。唉,其实我挺佩服你的,现在像你这么简单纯洁的人不多了。”
脸皮上臊臊的,原来这是个透明的玻璃盒子,所有人都在看,除了我自己。
“对了,亦清和我说你当天就走了,怎么走得那么急?”
难道谢亦清在和我煲电话粥的时候竟然同时和她在一起?我突然想起杨燃天和穆茵,一股怒火冲到了头顶,连呼吸都粗了起来。
“还有事吗?”我的嗓子有些哑了。
也许我的表情很难看,唐笑纯撇撇嘴,“呵呵,没事了。对了,今年过年亦清和我回家了,我爸妈挺欣赏他的。对了,听说你在海边上学,我们家也是海边城市,什么时候你也来玩儿吧。”
“唐笑纯,啰唆这么久,你不觉得咖啡上火吗?”我终于怒了,“我没见过女孩子拿放屁当说话使,你不觉得难为情我还替你不好意思。放了这么多废气,你能不能说点儿有用的?你想说什么?”
唐笑纯噌地站起来,尖着嗓子喊:“孟露,你个死贱人!谢亦清是我男朋友,你离他远点儿!”
我亦站起来,手里拿着杯子,准备忍无可忍时送她些水喝,“唐笑纯,你不像蠢人,你是真的蠢!捧着一坨大便当巧克力,还怕别人来抢,视力和嗅觉都堪称极品!你愿做屎壳郎没人拦你,请便!恕不奉陪!”
我也受够了,忍着忍着再忍着,终于骂了出来,扭身就走,走的时候被沙发椅绊了一下,伸手一推,竟远远地甩了出去。咣当,不知道撞了什么。
后来,同事告诉我说,他们找唐笑纯赔偿。那家伙傻大气粗,又不肯丢面子,结果被狠狠地敲了一笔。
我第二天就走了,坐上回学校的火车,要开始我最后六个月的大学生活。但我记住了唐笑纯的一句话:
你知道留京和打工的区别吗?
谢亦清没再给我电话,我终于知道这一切真的起于一个误会。他的勃勃雄心,亦只有唐笑纯可以完成。
回到学校,发现公子润在学校里忙活,段姜却没回来。据说她的毕业论文要在上海写。
“你怎么回来了?”我问公子润。
“不许吗?想回来就回来了。”公子润看起来有些沮丧。
我们做不到喜怒不形于色,只是相对好些或不好些。
“你呢?工作找得怎么样?”公子润显得有些疲惫,完全没了上学期的神采飞扬,“看起来你气色不太好,跟人吵架了?”
“不怎么样。没找到,没消息。”我同样沮丧,“不过实习而已,我不喜欢在宾馆伺候人,做不了。”
“晚上有空吗?一起吃饭?”公子润说。
“你不和三爷他们喝酒去吗?”我笑着,以为他说的是学校食堂。
“我请客,去校外喝酒。”公子润笑着靠近我,把胳膊搭在我肩膀上,离得很近。闻着相同的沮丧气味,我忘了羞怯,只觉得大家是一条船上的难友,不自觉地点点头,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刚答应下,就看见公子润一贯整齐的头发有些凌乱,“你头发乱了,梳梳吧。”我随手从兜里掏出宾馆顺出来的梳子递过去。
“你连牙都不刷,怎么还带梳子?”公子润不愧是公子润,心情一好就翘尾巴。
“不可以变吗?”搁在过去我是一定要损回去的,现在只能郁郁地回一声了。
大四就像一台加速的搅拌机,让一切都脱离了秩序。我们一只脚踏进社会,一只脚还在学校,生生地被分成两半,天生就有无所适从的惶恐。
公子润看了我一眼,没了嬉笑的样子,“怎么了?”
“没事,找不到工作心里比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