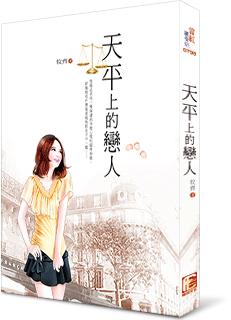独木桥下的恋人-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慢慢起立,一抬头便看见于曼从食堂那边向他走来,脸色憔悴,秀发飘逸,步态袅娜犹如仙女下凡。
昨天晚上,于曼从医院值班室跑出来,发疯似的跑出医院大楼。她头脑一片空白,面对茫茫黑夜,不知如何是好,不知何处是去路,也不知与谁诉说悲惨的
遭遇。
她迈着机械的步子,在医院前无目的地走了好长时间,然后在一个花坛边的青石凳上坐下,抬起头仰望夜空,祈求上苍的帮助。
人在遭劫时,在绝望时,往往本能地呼天唤地,祈求上苍的帮助。
然而,九天之上那个万能的上帝并未显灵。幽远的夜空闪烁着稀稀落落的星星,忽隐忽现:银河像一群从南向北行走的银白色的羊,仿佛缓缓移动:夜风习习,花香幽幽,恍若幻境:楼上病房昏黄的灯光透过玻璃窗,投射在地上,斑斑驳驳,恍恍惚惚,像鬼怪提着灯笼在游荡,阴森森的,十分寥寂可怕:草丛里有几只秋虫,断断续续地鸣叫,那声音悲哀凄凉,令人觉得世界已接近末日。
于曼好像变成了木头人,对这一切没有丝毫感觉。她仿佛失去了思考力,甚至记不清楚刚才发生的事,仿佛还在那个噩梦中。她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再也不是她自己了,变成了与她自己毫不相干的另一个人,一个经受了暴力蹂躏完成了退化的人。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突然想起了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书上读到的一句话:你对什么都觉得可笑,你就成熟了。只有饱经沧桑的人才能理解这句话。于曼初涉人世,自然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可能深刻,也不可能全面,但这句话像一星微弱的光亮帮助在黑暗中行走的她看见一线光亮。她暗暗地安慰自己,要笑对它,正视它。想到这里,她站起来深深地吸了几口带着寒意的空气,回到了苏平的病房。
于曼躺在孙平身旁的一张空床上,似乎什么也想,什么也不想,思绪像纠缠在一起的一团乱麻,无法理清,也无心理清。
此时,苏平睡得很安宁,一夜没有动静,如果不是均匀的呼吸声,真以为他到了另一个世界。
第二天一大早,于曼就爬起来,含着泪水写了个纸条,放在苏平的枕头旁边,望望酣睡的苏平,悄悄地离开了病房。
苏平还在梦乡徜徉,双眉紧宁,嘴角微微抽搐,眼帘不住跳动,仿佛痛苦的样子。他正在做一个噩梦。
马俊看见于曼,气不打一处来,心里盘算着如何开口和她要钱。他朝于曼一边招手一边用命令的语气喊:“你过来!你过来!”
于曼本来打算把钱尽快还给马俊,没想到一回校就碰到了他。
于曼走到马俊面前,看到马俊精神恍惚,两眼迷茫,一张哭丧脸子如丧考妣,淡淡地问道:“你生病啦?”
“……”马俊鼻孔翕动了几下,双唇紧闭,满脸怒色,心里大声骂道:“你他妈的别来这一套了!快还老子钱!美女人没有好东西!”
于曼看透了马俊的心肝,知道他在想什么,没等他开口,就从书包里掏出一沓百元人民币,塞到他手里,不动神色地说:“这是我借你的3千元,你点点。”她说完扬起头从马俊的身边走开。
马俊十分惊愕,老半天没有反应过来,手里握着票子,呆呆立在那儿望着于曼曲线优美的倩影消失在女生公寓。
马俊手里攥着一把票子,疯疯癫癫地抬起一只脚要踹食堂的一扇门。
他用脚踹开门的恶习经常受到别人的指责,但他置若罔闻,顽固坚持。他这个粗暴的行为是从小向他父亲学来的,久而久之,习惯成了自然,成了他一种深根蒂固的素质。以脚代手开门,自然很费鞋子,因此他得经常买新鞋。有时候一
双新鞋在他脚上呆不了几天,左脚的那只还精神焕发,右脚的那只已精疲力竭,
张着嘴巴,向他呼喊着要永恒休息,他只好遵命。
马俊的右腿伸直,脚尖鼓足气力踹那扇门,不料里面也有一只脚在踢那扇门,两只脚互不相让,隔着门激烈争斗,持续了两三分钟,里面的那只脚才屈服。可是马俊因用力过猛,门突然被踹开,随着门的吱嘎一声愤怒的叫声,他的身子像一个装满干草的麻袋软绵绵地闪进了门内,跌倒在地上,手里的票子洒落了一地。几乎同时,他身边爆发出一阵兴灾乐祸的女声大笑。
原来是一对恋人,男的背上扒着个女的,像连体人似的立在门旁。那男生样子长得像个大水缸,身材矮胖,留着板寸头:又短又粗的脖子上,套着一条筷子粗的金项链:横肉堆满的脸上闪着一对老鼠眼。那女生倒是长得有几分姿色,俊眉俏眼,细腰长腿,臀部圆润:染成淡黄色的披肩发像瀑布似的垂洒在背上,风姿潇洒,勾魂醉魄。
这一对恋人很奇特,你看了立即会联想到一只癞蛤蟆扒在一个水缸沿上往里瞅。
马俊不认识他们,但多次在校园里,楼梯上看到那男生背着那女生,气喘吁吁,吃力地走动。
男的背女的被称为长在一起的热恋。时下,不论在国办大学或民办大学,这种热恋形式像毒品似的在一部份恋人中起着梦幻般的消受作用。马俊打心里羡慕他们,每逢看到他们长在一起,总是想入非非,魂飞魄散,目瞪口呆欣赏一阵儿,玩味半天。
然而,这种长在一起的热恋形式如老鼠过街几乎遭到人人喊打。有一次,夏颖教授在教学楼道里,看见一对长在一起的恋人,说服他们要注意影响,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乐意!”
“这不太雅观!”
“那我们不管!我们不违法!”
“可是你们的行为不受欢迎。”
“我们用不着别人欢迎。”
“大家讨厌你们的行为。”
“那是嫉妒!”
“你们父母看到你们这个样子该怎么想?”
“我们不知道,不过他们会很高兴的。”
“……”
在一次会上,夏颖提出要耐心教育那些“长在一起”的恋人们,引导学生文明交往,在学院里禁止这种不雅或丑恶现象。这个提议得到了到会的系主任们的赞同。可是钮文革和胡来运却坚决反对,他们狡辩着说:“无论用什么方式恋爱,都是学生们的自由,是他们的人权,我们要尊重人权,不能干涉,也没必要管他们。如对他们要求太严格,他们就要求转学或退学。他们的人数不少呀!招生竞争很惨烈,我们招一个学生要付出成本5千多元哪!”不言而喻,郭宝才完全赞同他俩的看法!
马俊从地上爬起来,呆呆地目送这对奇特的恋人从那扇门挤了出去,那门随即在他们身后嘎吱一声自动地关上。
门缝儿里飘进了那个女生惊叹的声音:“那家伙真有钱!”
马俊像根木头柱子愣在那儿半天没有动弹,几乎忘了洒落在地上的票子。
第十九章
那天晚上,苏平服了应大夫开的药,不一会儿,就觉得意识不清,视线模糊,面前的一切都变得朴朔迷离,仿佛进入一个古怪的陌生世界。他的眼皮越来越沉重,他想睁开眼睛,可是用尽浑身的气力也抬不起眼皮,最后终于放弃了,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于曼遭受应大夫强暴时,苏平正在做梦,一个很长很奇怪的梦——
苏平牵着于曼的手沿着一条小道散步。
小道蜿蜒曲折,通向一座苍松翠柏覆盖着的山丘,颇有曲径通幽之趣。正值傍晚时分,夕阳像硕大的灯笼,悬在西山顶上,不遗余力地将蓝森森的余辉投射在大地上。四周的景象五彩缤纷,光怪陆离:道路一旁长着奇花异草,香气袭人:另一旁树木成行,弯曲如虬,千姿百态,红叶翻飞,像无数只红色蝴蝶聚集在一起欢乐嬉戏:狂风骤然四起,摇撼树木,撕扯红叶:瞬间红叶凋落,树干变成黑色:突然一个霹雳在头顶炸开,天空闪起蓝光,像无数条草蛇在乱窜舞动。
苏平拉着于曼的手赶紧转身往回走,但惊愕地发现,那条来路消失得无影无踪,面前横着一截残垣,上面用鲜血般的紅墨汁写着一首诗《无题》,墨迹未干,散发着海水般的腥味。
苏平和于曼停下细读:
路啊路无尽头的路
承受着无限的蹂躏
蕴藏着无数的脚印
回响着无数的心声
有悲歌也有欢语
路啊路无尽头的路
洋溢着深情
记忆着厚意
潇潇秋风瑟瑟红叶
诉说着哀伤与欢乐
路啊路无尽头的路
倒空了行人
留下了悲欢和哀愁
有你的欢歌笑语
也有我的哀怨叹息
苏平和于曼读完这首诗,互相对视了一下,发现对方的眼里闪烁着一团疑云。他们俩都不太喜欢文学,对诗歌的理解较差,因此虽细读了几遍,仍不解其意,只觉得一种无名的悲凉向心头袭来,感到一阵揪心扯肺般的惆怅。
苏平赶紧拉着于曼的手,跨过一个墙豁口,只见前面不远处有一泓湖水,望去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水波粼粼,水鸟悲鸣,空旷寥寂。他们前面没有路,只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旷野。他们踩着杂草,向那湖水走去,走啊,走,一直走。那湖仿佛与他们同步向前行走,总是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展现在他们面前。
苏平只顾朝前走,松开了于曼的手。不知过了多久,苏平想起了于曼,停下来四处环顾,可是不见她的影子。他惊恐万分,大声呼喊:“于——曼,于——曼,于——曼……”
然而,应答他的只有耳边呼呼的风声。
苏平从梦中惊醒,像跑完了马拉松,大汗淋漓,浑身疲乏不堪。
他睁开眼,定了定神,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在梦中。
阳光明晃晃地从玻璃窗射了进来,室内静悄悄的:病友们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扶着床头站着。
苏平坐起来问病友:“现在几点?”
“9点10分!”一个病友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苏平正要呼叫于曼,突然在枕边发现了一张纸条,一片从《高级英语》课本封面撕下的空白书页,上面只有五个铅笔字:“我回校去了!”,没有署名,也没有注明日期。苏平双手捧着纸条,怔怔地盯着简短的留言,好像要逼迫它回答为什么?他把纸条翻过来调过去细细地查看,发现有几处好像被水洇过,感到非常震惊。
原来于曼在给苏平写留言时,痛苦万分,凄然泪下,泪珠子一颗接一颗从眼里滚出,连成了泪雨,免不了有几滴洒落在纸上。她咬着嘴唇,忍住没有哭出声来,以免惊醒苏平和其他病人。
苏平对于曼突然不辞而别感到很纳闷儿!
打那天起,于曼再没有为苏平陪护,也没有来看他,苏平由纳闷儿转变为痛苦,感到无尽的寂寞,尽管有同学们常来看望。
没有于曼陪护,苏平呆在医院简直像坐大牢,难熬难煎,度时如月。他心急火燎,要弄明白于曼突然离开他的原因,正好住院处通知他,预交的医药费已花完,他再没有钱继续住院,因此他办了出院手续。
回到学校,苏平听说于曼请假回了家,感到非常困惑和惊讶!
苏平出院后右臂上仍戴着一个硬邦邦的石膏套子,每天还得打针吃药。他的内伤已治愈,没有任何异常反应。伤筋动骨一百天。他的胳膊还没有长好,还隐隐作疼,不能活动,生活很不方便。这一切他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痛苦,他简直无法忍受,觉得心肝仿佛被撕破,不住地滴血。他恍恍惚惚,几乎到了发疯的地步。
他去当“特招”只是为了赚钱替于曼还借马俊的钱,没想到不仅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经济上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肉体和精神蒙受极大的痛苦和侮辱。他有一种感觉:在于曼身上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她可能因此永远离开他!但他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失恋,他要弄清楚于曼突然离开原因到底是什么。
苏平cool得很,是那种对周遭发生的事不易动神色的帅哥:他外表上看上去像天空一样沉静,内心却似大海波涛般的沸腾。为什么于曼突然离开他,这个问题日夜纠缠着他,折磨着他。他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从来不和别人诉说,连他的好朋友杨鹏也听不到他近来的心声,以为他还没有从被打的那个Blackday走出来。
“苏哥,Forgettheblackday!振作起来把身体尽快养好。你这样整天躺着不行,应该经常到外面走走,散散心,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杨鹏见苏平一连几天躺在床上昏睡,为他的身体担忧,建议出去活动活动。
“……”苏平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面朝墙壁躺着,睁开眼呆呆凝视墙上贴的那张招贴画,画上是世界篮球锦标赛的一个投篮镜头:正在投球的是他最崇拜的一个美国公牛队队员,那个球仿佛从篮板上跳到篮圈里,飞快地旋转了几圈,然后跳出了篮圈,好像和投球者开玩笑。“非常遗憾!”苏平每逢看这张画时,都在心里情不自禁地发出遗憾的惊呼。可是今天,他没有感到丝毫遗憾,却突然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悟:世上的事情,都包含着定性和不定性两种可能。一切事情都像这个球,看上去一定成功,结果失败了。有时成功和失败实在难以预测,因为命运、机遇、条件、环境和别的不可言说的东西在起作用,在作弄你。他和于曼的关系突然发生了变故,也是这个理儿。这么一想,苏平的心里好受多了,也亮堂了一些,好像一间封闭着门窗光线幽暗的屋子,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随即射进了阳光,开始亮了起来。
见苏平继续躺着不吭声,杨鹏用英语说:“Wouldyougooutforawalk?”他说着拿起桌子上的暖水瓶,给苏平倒了半杯水
“好吧。”苏平一跃身子坐了起来,穿好鞋袜,端起杯子,一仰头喝了个底朝天。“Thankyou。”
“Yourewele。”
苏平和杨鹏刚走出公寓,孙同正迎面走来,他右手握着手机,习惯地边走边玩。
“你们俩去哪儿?”孙同停下玩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