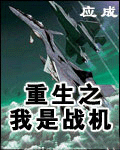我是北大留级生-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鑫珊,于1977年晚秋
第二部
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1)
即便是今天,我也是从心坎里鄙视这场阴谋和下流。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引蛇出洞”,不是我个人受到了什么大伤害,而是我们民族,千万个家庭在流血。过些年,我一定写本政治哲学书,追问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国家?政治理应是科学,不是权术。好的政治同数学物理方程式都是永恒的。
这场风暴发生在距今46年前。当时我19岁,读大二。
幸好,当年我并没有形成一整套世界观,否则我就是右派无疑。其实我已经到了右派边缘,在团内受到的处分是:劝告退团。我的政治结论是:在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去捍卫党。思想右倾,有右派言论。
1957年4月中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北大,全校师生都出来欢迎。这件事给了我很深印象。因为苏联电影《保卫察里津》里出现过伏罗希洛夫的艺术形象。这回他从我身边走过,墩实、健壮,身高不过1米70,让我有些失望。
记得就在他访问北大的前后,北大出现了大鸣大放的“民主墙”。中文系有同学写了一首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诗,题目叫“是时候了!”
很有鼓动性,张贴在大饭厅的东墙。46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这首诗和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东墙的位置。我仔细读了两遍,深受鼓舞。
这首诗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一大片大旱季节的草原。每天都有上百张向党提意见的大字报张贴在大、小饭厅的墙上,非常热烈,壮观,激动人心。
根据记忆,大字报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或叫个人集权制。个人崇拜(或叫个人迷信)是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潮;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如一言堂;外行领导内外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对苏联专家提意见;教育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关于自由……
涉及范围很广,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接触了中国的现实。有许多事物是我第一次听说,“哦,原来如此!”“哦,还有这么一回事!”
人民大学林希玲(后来被划为极右,投进监狱)来北大发表讲演,她站在方凳子上,激昂慷慨,听众有好几百,里三层外三层,我也在其中。当她讲到“科学、民主、自由”这些字眼,听众便鼓掌。我也跟着热烈一番,尽管我并不懂得讲演的全部内容。
据说,林女士已定居法国。1995年左右,她来上海,在一次聚餐会上,我还见到她,但没有同她交谈。
物理系毕业班谭天荣的大字报和讲演尤为震动。他大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旁征博引,我觉得他很有学问。当他站在小方凳子上,滔滔不绝地演说,在我的眼里,他便成了现实中的英雄,形象伟岸、高大。
后来他划为极右。1978年平反后,听说他成了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记得对谭天荣的处理方案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说不开除他的学籍,留校,作为反面教材。
是年秋天,反右结束,我还看到他在校园内扫落叶,那是他劳改的开始。不久他便从北大消失了,据说是送到外地去劳改,吃尽了苦头。
谭天荣的讲演吸引了许多同学。我们系的法文专业同学陆丙安便是一个。她是北大广播站的播音员。她崇拜谭天荣的才华和勇气。他的大字报正是通过她播了出去,扩大了影响。陆丙安为他买好饭,做他的后勤。——心理学上这就是“英雄美人情结”。
陆和我一个年级,不同专业。她身上的浪漫主义情调很重。她有“英雄美人情结”是必然的。于是她成了一般右派。1960年分配到广西。1978年平反后去了巴黎,同熊秉明结了婚。几年前我们见过面。现在陆丙安仍然在巴黎定居。
当年写大字报的学生有的签上自己的名,有的只签上自己的学号。我在两张大字报上留下了自己的学号。(别人写的,我表示同意该大字报的观点)
第一张:要有言论自由;
第二张:在大图书馆,放着18世纪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半身雕像,必须搬出,换上中国伟人的铜像。(后来这张大字报定性为反苏言论)
整整一个星期北大校园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的确是大鸣大放的自由局面,随便你写,谁也不出来干涉,阻挠。校党委,各系的党总支,支部,都保持沉默,给人瘫痪的假象。
有人在大字报前拍照或把签上的学号记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为“秋后算账”作准备。
中文系好几位同学(后来都划为极右派)创办《五四广场》杂志,呼吁赞助。马寅初校长捐500元。有些名教授也纷纷解囊。该刊物的寿命极短,只出了两三期。定性为反动刊物。
西语系有人组织师生准备到清华去煽风点火。后来因故作罢。但事后组织者、发起人被划分为极右派。
同学回到宿舍,便是大辩论。大致上分左、中、右三派。我的立场和观点是偏右。我总是附和别人的主张。
一个多星期,在这场大风大浪的政治运动中,每个人(包括党员)都作了充分的表演。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在“引蛇出洞”。
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2)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宣告全国范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有位中央首长在大饭厅作反击动员报告,非常保密,窗子紧关。
一夜之间,大字报全部被清除。各系各班级都在恐慌,大家都预感到了有场政治风暴来临。这就是按周密计划抓大小右派。按比例,我们班级(共20人)有3名右派分子。据说,有个班A同学并没有写大字报,言论也没有,但支部认为他有问题。于是星期天组织全班
同学去颐和园游泳,三名支委留在学生宿舍,对A同学的箱子进行搜查,从中翻出日记本,断章取义,摘出几段攻击党的农村政策的言论,作为划成右派的依据。
当时全校各个班级都在组织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前几天还是自己的同窗,今天却要撕破脸,进行面对面的批判。人人都要起来同右派划清界限,保卫党。否则,就是丧失立场,右倾,甚至成为“右派”。
英语专业有位泰国归国华侨学生(女)因过度恐惧,心理压力太大,在宿舍自杀。(其实她没有任何问题)
北大反右有如下几个特点:
1. 全校师生约一万多名,右派总人数约500。
2. 听说马列主义教研室几乎全军覆没。
3. 理科右派质量比文科高,说明理科学生比文科有头脑。
反右刚结束,有一天我走进大饭厅吃中饭,在大门口我看见约有20多位同学排成队,站在那里,低着头(有的不低头)。听别人说,这是某系右派在示众。这情景令我不寒而粟!我意识到划上了右派,竟是敌人的下场!问题严重了。
据我所知,对北大500多名右派作了如下几种处理:
1. 投进监狱(极少数,估计同肃反问题有牵连);
2. 送校外(比如斋堂)劳改两年,保留学籍。
事实上我也看到两年后有右派回校再跟班学习,直到毕业分配。
3. 一般右派跟班学习。不过他们很孤立,一般同学很怕同他们接触。怕扣上一顶帽子:同情右派,立场不稳。一般右派学生寒暑假可以回家,但要向当地居委会报到,目的是接受所在地的居民群众监督,不许乱说乱动。
那是一个时时处处讲阶级斗争、火药味特别浓的时代。不过当年批判右派的时候并没有戴高帽子、游街和“喷气式”,基本上是文斗。
9年后即1966年,文革爆发,则是一场比反右猛烈十倍,涉及面大十倍、疯狂十倍的非理性政治运动。
这两场运动我都经历过,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文革的冲击更大。记得有张大字报的标题就是:“把漏网右派分子赵鑫珊揪出来示众!”(地点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1978年三中全会后我接到北大给我的平反通知,我的问题才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没有查阅任何史科,仅凭自己的记忆,免不了有偏差。特此声明)
反右后的北大(1)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或摧残。
记得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
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理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1956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十年文革”,今天的中国会是多么强大和繁荣啊!“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时间就不是2003年10月,而是1973年10月或1983年10月。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这是全国知识界“惊弓之鸟”状况的一种反映。当时知识分子顾虑重重,不敢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怎样才算不离开呢?)
于是天下只有一种声音。全来自一个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吗?
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日子很不好过。大学生也不例外。记得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展开了讨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属于剥削阶级?”
这个政治标准或命题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今天来看,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作这样的总体估计和划分是错误的。这是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的总根源。其实党内不少人并不同意这一评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风细雨派。(他们都是留法学生)这个温和派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理性的产物。1962年春,国家科委、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合称“广州会议”——在当时此次会议精神是很鼓舞知识分子的)。周总理、陈毅元帅在两个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我把它看成是党内温和派的表现。
后来也是出于毛泽东对整个形势的错误评估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反右前,大学毕业生一年转正后的工资是62元。反右后,工资降为56元。这大概也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总评估有关。降工资是惩罚。
关于反右后的北大,我想分以下五个方面作些回顾:
一、 劳动锻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反右前,北大学生也下乡劳动。反右后,下乡劳动就更频繁,而且性质有些不一样:带有惩罚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有我们洒下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吃窝窝头和咸菜。白饭和馒头的比例较小。
1958年我们班级去怀柔县秋收,主要是白薯和大白菜。那里有两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
1. 山区的自然景色十分悲壮,尤其是落日薄暮时分。这有助于我后来形成我的“荒野之美”原理。
这样的下乡对于我的成长或世界观的形成并不是一件坏事,尽管很艰苦。从书本上是很难得到这些宝贵感受和经历的。
2. 乡土民居的墙这个词汇全是就地取材。我指的是以毛石砌筑墙体,从而成了厚实的石头墙壁,给我粗犷、剽悍和野性的感觉。许多年后,我把这种感觉写进了我的三本建筑论著。
6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动之余,晚7点到9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在劳动中毕业”?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不必过长)
其实1993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况。9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反右后的北大(2)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农民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OK?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二、 向党交心,个个争做左派
反右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