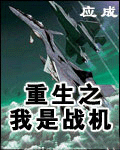我是北大留级生-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许由拉格朗日发现的“中值定理”便是一例。因为不久我便读到它的几何意义:明晰,清楚,简洁。
当我读懂了这条定理(它在整个微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内心有种难以言表的激动或激情。我知道,这是对真理的追求怀有一种激情(a Passion for Truth)。在当年那种非理性、混乱和不正常的政治现实生活中,数学真理之光于我无疑是种高贵的鼓舞和安慰。在这里我要说明四点:
a. 北大有些阅览室的自然科学图书都是开架的。不管你是哪个系的学生,只要你乐意,便可随手把任何一本书取下来阅读。这是当年北大最有利于我成长和发展的环境。
为了吃透中值定理,我至少参照、比较了五本微积分教程。因为每本教程解释的角度、语言略有不同。我是“兼听则明”,“兼采众长”,“兼收并蓄”,最后达到融会贯通。——后来它便成了我自学数学的方法。
b. 反右后北大的恶劣环境迫使我进一步退隐到自己的内心深处。这种心理也有利于我进入中值定理。因为我把数学王国看成是一种避难所,是一种拯救。
数学真理的惟一性、确定性和可靠性在我的内心深处可以构筑成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
白居易的话是对的:“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
此处“道屈”即指艰难时世,命运坎坷。所以黑格尔才说:“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精神逃避到思想的空旷和深邃领域,建立起一个思想或观念的王国,以反抗混浊的世界。
没有比数学更空旷、更幽深的领域了!
c. 那些年,我是随心所欲地阅读。精神非常自由。
我像个钟摆,在理科和文科这两头来回摆动:在理科呆得太久,怕冻僵;在文科停留的时间太长,又有被烧焦的危险。所以我总是在两头不断地来回波动,求得精神上的平衡,和谐,文科理科的统一。
d. 后来我读英国杰出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A.N. Whitehead, 1861—1947)的《科学与近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一书便恍然大悟。因为他是这样推崇数学和音乐的:这两样东西是人类性灵所能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产物。
数学王国的神性(4)
这个一语胜人千百的命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并使我终生受益。不过也只有我在1959年对音乐和数学有了一定的感受、体认之后我才能懂得怀特海提出的这个命题。不过我还想加进一样东西,而成为三位一体:
数学·理论物理·西方古典音乐
在北大最后三年,这三样东西占据了我60%的时间,也是构筑我的内心堡垒三块非常重要的花岗石。若是抽掉这三块基石,我的内心要塞便会轰隆一声坍塌。
2. 数学哲学
从19世纪末的一本德国数学杂志中(字体和纸张都显得古色古香),读到一篇有关德国著名数学家克罗纳克(L. Kronecker, 1823-1891)的文章。克罗纳克给数、数学、数学家和上帝下了一个幽默、绝妙的定义:“亲爱的上帝创造了整个数,其他的一切都是人的劳作。”(Die ganzen Zahlen hat der liebe Gott gemacht, alles andere ist Menschenwerk)
这个定义,这种表述方式,像道闪电,一下子照亮了我的内心世界。这是我在6年求学时期读到的最有启蒙价值的格言之一。我说过,格言在本质上是智慧,不是知识。克罗纳克这句话说出了数学哲学最高智慧,而且是言有尽意无穷。后来,模仿他这种说法,我说:亲爱的上帝创造了全部音阶(即全音、半音和其他音程),其他的一切都是作曲家的劳作;亲爱的上帝创造了时间、空间和物质,其他的一切都是物理学家的劳作。
十七世纪德国伟大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智慧也有力地启蒙了我。按他的天才本质,他是一位逻辑学家。他善于用少数几条法则——这便是形成逻辑的思路——去把纷然杂陈的现象世界整理出一个秩序井然的和谐。(比如一套微分公式)莱布尼茨有一句名言使我终生受益,发出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最伟大的画家也不可能随手画出一条无可指责的、像每个使用直尺的人都可以画得出来的那样的直线。”
所以制定出一套微分学条例便是莱布尼茨思维方式或他的“哲学世界观”的必然产物。章学诚(1738-1801)有言:“有天地之象,有人心营构之家”。莱布尼茨制定的一整套(共9条)微分学条例正是“人心营构之象”。他把它的形式搞到这样尽善尽美,以致于从1684年到今天(2003年),它都没有改变。以下是其中两条:
(cv)=c。
(uv)=u+v。
读到莱布尼茨的思维方式,我只有哭。我是以哭代歌。
明末清初贺贻外(江西永新人)削发逃入深山。他主张诗歌要像天地间的“雄风”,要“凄怆”,要“以哭为歌”。1959年春,也是在数学系图书馆我从一本德文数学杂志上读到一篇纪念德国伟大生理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赫姆霍茨(H.von Helmboltz, 1821-1894)的文章,其中着重提示了他的研究路线或探索轨迹,使我深受启发。
他因家境贫寒,只好通过当军医的途径去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当军医是公费的。所以他的科学研究生涯的起点是生理学。他解剖了眼睛和耳朵,探索这两大感觉器官的功能和机制。
不久他便发现,研究人的视觉和听觉的生理机制一定要研究光学和声学,否则便很难深入下去。
这样便引导他去敲开物理学的大门。
后来他又发现,不懂数学,敲开物理学的大门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样,他又成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具有开拓精神的数学家。
最后,他的归宿必然是哲学。哲学是人类知识大厦的金屋顶,或者说是中世纪哥特式大教堂的、直指蓝天的尖顶。
三、 古希腊哲学和数学
大学最后三年,我走进古希腊哲学世界,对我的成长是一件大事。这又要多亏北大图书馆。
记得在文史楼二楼大阅览室旁边陈列着好几套百科全书,我经常浏览的有两套(都是30多卷):德国百科全书和大英百科全书。对于我,里面尽是金币银币,我仿佛是一个一贫如洗的乞丐,只要一翻开它,便能拾得一个大金币,一个惊叹号,令我兴奋,激动。
比如对柏拉图、爱因斯坦、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介绍。不仅把他们的主要思想和论著列举了出来,还把人们评论、研究他们的生平和工作的代表作附上。这便于我去作进一步跟踪。
记得关于马克思,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开头第一句就写道:“黑格尔哲学的学生,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用来观察、解释政治经济学现象。”
这种说法,给了我难忘印象。
关于爱因斯坦,百科全书列举了他的一本著作《Mein Weltild》(我的世界观),1933年,德文版,并且说有英译本,书名是《The World as I see it》。这个书名比原德文书名更好,更形象,更有动感。它的意思是《我看世界》。
不久我便从大图书馆把这两本书同时借出来。由此可见北大图书馆藏书之丰富和珍贵!这在别处是不太可能的。它大大满足了我对世界的好奇心。我的求知欲和世界观得到了最充分的满足。
数学王国的神性(5)
再就是关于古希腊哲学的书。北大图书馆有丰富的英、德文馆藏。其中有两位古希腊哲学家分别给了我两个大大的惊叹号。
a.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0-490)。
在古希腊哲学史上,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使用“数学”这个词的人。他和他的学派是古
希腊数学的奠基人,认为数(Number)是万物的本源;万物是受数支配的。他用数学比例来说明事物之间的关系。他将事物的本质归结为数的规律。数的原则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或“第一原则”;数是万物的本体。他还把优美、和谐的音乐归结为数(Number),并发现了它的数学基础。
这使我茅塞顿开。因为当时我正在系统地欣赏莫扎特的全套钢琴协奏曲。我尤其欣赏莫扎特的慢板乐章,以及钢琴同整个乐队的对话。不管我是在朗润园还是圆明园,在我的书包里都装着有关毕达哥拉斯的书。黑格尔有言:“哲学自希腊开始。”
我忘不了我那段一日一个小惊叹号、三日一个中惊叹号和十日一个大惊叹号的急风暴雨、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太平洋生起台风的情景是:海浪有几米高,而在五千米深的海底却是平静的。我的情况刚好相反:外表是平静的,而我的内心却是波涛汹涌,时时在激荡、起伏。
我这种心灵状态完全是保密的,同班同学没有一个觉察出来。他们很规矩,只吃碗里的,我则自己去野外到处觅食,不拘一格,望野眼。他们为“5分”拼搏,我只满足及格“3”分。很明显,自1957年冬天,我和同班同学已经分道扬镳了。在精神世界上,我已经脱离了西方语言文学系,但又不属于其他任何别的系。不过我没有脱离北大这个大圆圈。我只乐意在这个大圆圈内漫游,上下求索,“登泰山而小天下”。
1960年我读到方以智(1611-1671)一段有关幸福的自白,颇有同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衷其间,岂不幸乎!”
每当我坐在大图书馆俯而读,仰而思,我就会记起方以智这段话,因而更加眷恋北大图书馆以及校园环境。——这也为我日后决定主动留一级埋下了伏笔。
b. 柏拉图(公元前428-348)。
走近柏拉图及其哲学世界是个很重大事件。尽管后来我并没有成为柏拉图学者,但我一直是柏拉图哲学的信徒,直到今天。
西方学者认为,柏拉图思想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源泉。西方两千五百多年的哲学,皆可归结为对柏拉图的注释和阐发。西方哲学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非柏拉图的。
记得1959年寒假,我在同温德先生交谈中,曾顺便谈起柏拉图。当我从书包里拿出R.S.Brumbaugh的专著《Platos Mathematical Imagination》(柏拉图的数学想像)的时候,他只发出了一个惊叹号:“你在读这种书!”
当我拿出J.Burnet的《Platonism》(柏拉图主义)一书的时候,他又“哦”了一声,也有些出乎他的意外。
其实,我这点进步同两年来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是分不开的。古典音乐营造出来的“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的心理大背景帮助我走进柏拉图主义和他的数学想像。
那天,我一口气聆听了五首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尤其是其中第20号,d小调, K.466和第26号,D大调,K.537。
30多年后,我把我这些感受和理解写进了我的书《莫扎特之魂》(1991年,上海音乐出版社,41万字)。
无意中掉进心灵土壤和犁沟中的种子在30多年后才破土发芽,最后长成为一株大树。如果九泉之下温德先生有知,他也许又会发出一声惊叹:“哦!”
柏拉图强调数学培养政治哲学家的独特作用,因为数学能把人的心灵提升到最高的理性认识。今天来看,如果当年我国最高领导人懂点数学,就不会犯“大跃进”的错误,到处刮浮夸风,报纸上登出诸如“红薯亩产62万斤”的特大新闻;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便不会横遭批判,一棍子打死。因为一天之内,13亿张饥饿的大嘴巴吃掉的粮食便需要1万节以上的火车车皮装运!如果懂点数学,才会看到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可怕后果!
柏拉图学园重视数学知识的传授和研究,特别是几何学。
在学园中,柏拉图作过“至善”的讲演。听众原以为柏拉图会讲到财富、健康的内容,但听下来却只字不提有关财富这类常人所关心的东西,只说数、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因为善的东西也是美的东西;善是美所追求的目的,善是美的原因。而“美又是善的父亲”。
数学的和谐美也是原因,善是美产生的结果。
这些观点对当年处在孤苦无告、穷困之乡的我,无疑是一种珍贵的慰藉。我知道,思考数学、理论物理学和自然哲学不需要复杂、高深尖的仪器,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和一个善于思索的头脑。
是的,一个人若能激赏数学的美和音乐的和谐,他的心灵必然就是善的。
数学王国的神性(6)
四、 罗素和他对数学真理的追求
按我的探索路线或轨迹,我走近、结识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B.Russell, 1872-1970)是逻辑的必然。读他的书,是我在北大求学期间一件大事。他的论著给我一种“夜深鹤透秋空碧,万里西风一剑寒”之感。正是罗素把我的精神世界提升到了一个较高境界和层次,进一步远离了平庸和浑浑噩噩。
罗素说,数学真理才是“永恒的真理”。人们能够追求“永恒真理”,途径就是研究数学。
数学的真理不是针对具体、个别的事物,而是针对普遍世界的。这样的真理不仅比涉及的人事要伟大得多,就是比起将来有朝一日会自行毁灭、寿终正寝的太阳系也要伟大得多。因为数学真理是永恒的。
“我一想到数学,我的崇敬之心便油然而生……”罗素如是说。罗素一再嘲笑哲学家太懒不研究数学,或是太笨不懂科学。——这嘲笑曾深深触动我,当时是1959年,我21岁。
罗素企图在宗教、数学和科学中去寻找与个人无关的客观和永恒真理。
当年的我,读到这些段落,如同在黑夜落入茫茫大海许久之后突然发现离我仅5米远的地方便是一个安全的小岛,这时黎明的曙光开始临照这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