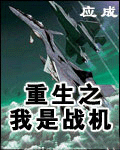我是北大留级生-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学生都知道,如果遇上彭真代表党中央作报告,那么,路线一定很左,知识分子的日子
不会好过。
1959和1960年都由彭真出来讲话,据说措辞很严厉,有时是指着鼻子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翘尾巴,必须夹起尾巴做人,好好改造。
幸好,我毕业的这一年,是由陈毅元帅出来讲演。所以一两千名毕业生个个兴奋。果然,陈毅元帅句句讲在同学的心坎里,掌声雷动。他主要讲了“红与专”的正确关系。讲得在理。
元帅讲话非常真诚,坦率。他承认在这几年中,批错了许多人,斗错了许多人,说:“我现在代表党中央向斗错、批错了的师生赔礼道歉!”
于是,元帅霍地脱下了帽子向台下听众深深鞠躬。不是一鞠躬,而是从四个角度朝台下的四个不同方向,四鞠躬。于是全场起立,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许多同学泪流满面,我也不例外。
我想,如果中国按照1961年这条总路线走下去,十年文革的灾难不仅可以避免,而且到200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强国。
由于陈毅元帅的报告,我们的毕业政治鉴定非常温和。当时有个术语叫“和风细雨”。(因为基调已经定了)
给我的评语是三条优点,三条缺点。其中一条优点是:学习刻苦,钻研心强,知识面广。
这出乎我意料。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这些留法学生是党内尊重理性规律的代表人物。
我想起中国古人说过:“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今天在上海外滩有一尊陈毅元帅的铜像。站在他面前,我总是记起1961年我毕业前夕聆听他的讲演和他脱帽鞠躬道歉的动人情景。
告别生出惆怅
惆怅是人类一种高级的感情。一个人越是会惆怅,他就越成熟。野生动物会惆怅吗?
科学、艺术、哲学的最高境界正是叫人惆怅。
1961年7月。学校宣布:毕业生可以回家等待毕业分配方案下来,但不准带助学金。看来,我只有留校等分配了。不久,校方改变了政策:毕业生可以领取助学金回家等待分
配。我是喜出望外。由此可见,助学金对我是多么重要!我对这14元5角一直心怀感激之情。
我决定回老家,但带了几本名著经典。我是念念不忘“最后冲刺”。把翅膀长得硬些,即使流放“西伯利亚”,也有飞高的本领。
8月下旬的一天,我在老家接到西语系人事科的通知,要我速回京办理离校手续,包括还清图书。
我报到的单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正是我填写的第一志愿。“你满意了吧?”科长问。
我只是点头。
在别的同学看来,农科院是同泥腿子打交道的单位,低级,不会有出息。我并不这样看。后来的十七年,证明了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地址,离北大南门仅四站路。过了人民大学这一站便是,红围墙,有座钟楼。
人事科发给我12元的搬家费。我打算两天后离校。
抽出一天,我绕着未名湖走了一圈。然后爬上山坡钟亭静静地坐了半个小时。我要感激这个地方,因为好几年,这个特殊的建筑空间安慰过我,给过我宁静。这时候,我反而没有古人所说的“世路如秋风,相逢尽萧索”。不,我的人生之旅才开始。
在北大图书馆的门前我也站了一会儿,但没有进去。在数学系和物理系图书馆前我默默无语地站了好一会儿。突然,从我的内心升腾起了一种根本的惆怅。什么叫“根本的惆怅”呢?很难用几句话来解释。唐诗宋词最高境界之一正是惆怅。比如这两句:“人言落日是天涯,望尽天涯不见家。”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几乎都有一个令人惆怅不已的结尾。越是能创造、表述惆怅美的作品,便越能拥有千千万万的共鸣。
其实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极至都是惆怅,或叫“普通世界的惆怅”。我既怕它又偏爱咀嚼它。清代李渔提出“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留连”,也是对“惆怅美感”的一种注解。估计李渔受到杜甫“篇终接混茫”的影响。在我向北大告别的时候,我的内心便有一种类似“篇终接混茫”的情绪萦怀。
我没有去圆明园。因为我相信以后还会常去那里对话和求助,不过四站路的距离。圆明园的废墟和残破给过我许多。以后我依旧少不了它的庇护和营养。因为那里有中国古人所敬畏的“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
燕南园我去了。因为许多年我在这里散步,感受清风所拂,花影零乱的诗意。当然,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还是向西南角63号马校长的旧居告别。院子里面好像还空着,没有人住,只有斜阳蔓草,往事低徊。我始终把他看成是我的校长。
朗润园两位老师家我去话别了。都为我高兴,原因之一是我留在北京,又在西郊,以后可以常来常往。
我爱当年北京西郊的幽静。我起身告别的时候,温德先生告诉我一件事:系副主任S原是地下党。解放前温德先生曾以他的特殊身份掩护过当年还是清华学生的S。有一天S作为当年的学生来看望温德老师。温德在闲聊中顺便问S:
“德文专业有个叫赵鑫珊的吗?”
“哦,他很调皮捣蛋,不务正业。”
“赵经常到我这里来听音乐,很用功,很有悟性。一个热爱莫扎特、贝多芬的学生能是坏学生吗?希望你们不要把他胡乱塞到外地边远省份的什么地方,这样会埋没他的。还是尽量把他分在北京什么合适的单位吧。”温德先生为我说情。
听后我很感动。我紧紧握着他那双特别大的手。
“以后我会常来看你,好在只有几站路。将来我也买辆自行车。”我说。
我遇上了“和风细雨”调整方针时期,否则像我这样的人不太可能留在首都。
又因为碰上了全国大饥荒,中央要加强农业,所以农业科学院要人。何况这样的单位也没有人愿去,没有竞争局面,只有我死心塌地想去,去走近“什么是生命”;去“对上帝的大自然凝神默想”。(这是18岁的爱因斯坦在一封书信中使用的一个泛神论术语。德文是:das Anschauen von Gottes Natur.正是这一信仰,引导他一生的探索。其实,Gottes Natur即GottNatur)。上帝—大自然这个泛神论概念是我大学6年最大的收获之一。它既来自书本,也来自我在荒郊野地的漫游,来自北大校园的一草一木对我的启迪)
我的最大遗憾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把古今中外母亲思念儿子落下的泪统统收集起来,恐怕会成为一个新的海洋,一个新的咸海。
在前面我说过,母亲死后多年,妹妹才告诉我,自我北上读书,母亲常常哭,哭了一年,经常搬出一把小竹椅,坐在马家巷口,对着火车站的方向,坐很久很久,然后就暗暗流眼泪。我埋怨妹妹为什么不早把这种真实情况告诉我?
唉,也不能责怪她,她当时小,不过10岁。
母亲因流泪过多,伤了眼组织,去看医生。医生只有一句忠告:“不要再哭了,再哭,眼睛会瞎!”
如果我在大学知道这些真实情况,我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比如:每个星期写信给母亲。不再是两三百字如电文那样简短,而是两千字,把我在校的点点滴滴生活细节详详细细告诉母亲。这样,母亲泪水便会减半。当然,有个原则:只能报喜不报忧。我受到的任何大小挫折,一点也不能让母亲知道。只能隐瞒。我说过,按性格或天性,我母亲的忧心太重,比常人重得多。她的忧心常伴有焦虑,不易化解。母亲太牵挂子女。她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为自己,只为儿女。
也是最近大妹妹告诉我一个重要细节:小妹结婚那天,母亲说:“这下好了,你们个个都成家了,我这台戏也唱完了,我可以安心走了。”
听后,我吃了一惊。母亲不识字,不知道莎士比亚,怎么能得出同莎翁一样的结论?因为莎翁说:“全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过是演员……”莎翁好像还补充了一句:每个演员上台、下台的时间都是安排好了的。
按我的理解,这便是命中注定。人算不如天算。
一个人活过六七十年,只要认认真真去体验、琢磨人生,便会自然得出近似莎翁的结论,即便他(或她)是文盲,压根就没有读过莎翁的剧本,连莎翁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道理很简单:戏剧艺术或人生哲学源自生活。
我今天才懂得后悔,把金戒指、手表和裤子卖掉,不应买书,应当买火车票。这样,6年我便可以回6次家,而不是3次。每次依偎在母亲身边,这样,她的泪水又会少些。
没有自己几十本小小的藏书,并不妨碍我走向“世界哲学”。因为我可以完完全全依赖图书馆。
当年中国经济不发达,电话普及率不像今天。如果五十年代我家有电话,我会每个星期给母亲打一个电话。母亲听到儿子的声音,思念、牵挂的泪水又会减半。
在校6年,我渐渐掌握了自学、自己开山劈路、逢水架桥的一套方法——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拿到了开启知识王国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它的核心是独立思考能力和将不相同的学科融会贯通),但也付出了代价。我指的是苦了母亲和弟妹。
又是大妹子告诉我一件往事:我北上读书后,母亲和妹子每天要去井头担水。当年我妹妹只有10岁,母亲的脚骨折过,两人只能担一桶水,且走走停停。
母亲心疼女儿,怕肩上荷载过重,影响发育,影响长个头,便把水桶的绳子往自己这边挪。女儿出于孝心,怕母亲的脚受不了,又把绳子尽量移向自己这一头。
母女为这事争执不下,只好停在巷子里不走。
这个细节久久回荡在我心底。近来散步、走在买菜的路上,或在咖啡屋闲坐,或是我写作到深夜,缓缓放下笔,抬起头看窗外一轮满月,记起《礼记》“日月无私照”这一句,我便会想起母亲和妹妹担水的那个细节。
孔子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好在在当今高科技的情况下(比如电话普及和发达的交通),母亲思念子女的痛苦可以减轻许多。这便是“游必有方”的意思。
空谷闻响——后记
这本书写得很快,只用了两个月。因为所有的情节都贮存在我的脑海里。写到动情处,我便放下笔,仿佛有空谷闻响的感觉。——那是从历史山谷中飘来的阵风,遥远,但清晰,悲壮。我崇尚悲壮。
回忆的本质是历史。历史的本质是回忆。
然而回忆是现在的回忆。人只有在回忆,处在曾经历过的历史的时候,他才是现实的。同历史和回忆完全割断的人不存在,也办不到。回忆使人的生命变得厚重起来。
我写作时的背景音乐,一直用的是巴赫、海顿、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肖邦。这些旋律把我带回到了朗润园那间典雅、古色古香的小客厅,清代民居建筑,外面下着鹅毛大雪。
我偏爱在寒冷的夜独自欣赏音乐,室内温度保持在不冻手冻脚,穿两件毛衣为宜的状态。这时候,我的内心便会升腾起一种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这种感觉的起源一直可以追溯到朗润园。
那里有我的精神世界的根。
2003年8月,我的好友、忘年交李传海特意开辆车从山东枣庄市跑来看我。见面时,他说给我带了一点礼物。我以为是三五张唱片。一看,原来是他为我收集了好几百张唱片!这着实让我感动。他是枣庄市的优秀钢琴老师,在他周围有一批音乐铁杆哥们。小提琴老师刘钦勇便是。当然还有他的正在布达佩斯李斯特音乐学院学小提琴的儿子。
有了李传海的礼物,我现在可以按A、 B、 C、 D……字母来排列我的几百张珍贵唱片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当然还有布鲁克纳的作品放在前面,因为都是B字打头。紧接着便是肖邦,因为是C打头。瓦格纳放在后面。因为是W。
这套科学的排列方法便是我早年从温德先生那里学来的。今天我这样做,也是对先生的一种怀念方式。
夜深人静,当我的客厅回荡着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我便会加倍怀念起先生和他的屋:客厅、书房和卧室,当然还有卫生间。透过小窗,越过窗外北大围墙,便是圆明园的地界。
哦,“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人生在世,羁旅之人永远有无法排遣的愁思,当我们一旦触及人生根本的时候……
过去的一切再也回不来了。时间是一支射出去的、永不回头的箭。时间也是一辆无形的马车,我们用100根碗口粗的钢绳索也休想把它拴住,叫它在原处停留哪怕是一分钟!
不久前有朋友问我,我的最后一部总结性著作将写什么?我想了想说:《五大秩序》。这是一套丛书,共5本,每本约20万字。包括《自然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人的内界(精神)秩序》。共100万字。
这五大秩序的胎观或种子又要追溯到我在北大求学的那些年。是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播下的种子或胎观。写完了这套文明哲学丛书,我就可以死而无憾地向人世告别,回到我母亲身边:“妈,你的傻儿子回来了!从今以后我再不离开你了。妈,读书的时候,我为了不让你操心,忧虑,只好偷偷地卖掉了金戒指、手表、毛料裤和羊毛毯,却换来了一把开启知识世界大门的金钥匙。妈,这是怎样一把金钥匙啊,它比1万只金刚钻戒指还珍贵!你的儿子不傻!世界上哪有读书读傻人的?”
人生是万米赛。读完大学只是跑完了1千米。后面还有9千米。要坚持跑完整个1万米,尤其是毕业后的9千米。
今天我已经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前面只有1500米。我仿佛听到“永恒女性”在为我摇旗呐喊:
“赵鑫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