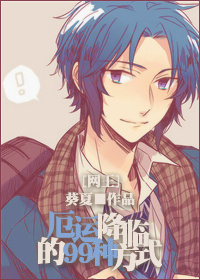高峰体验-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魔力究竟来源于什么呢?
究竟是我的错觉,还是其他人的错觉?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我出差去深圳,阴差阳错要从广州白云机场飞回北京。行色匆匆,汽车飞一般掠过广州街头,我没有来得及看到花园酒店,也就没有机会验证到底整件事情是不是我的错觉……
但是当汽车从天河地区的高架上开过时,我确实觉得,那段路和上海的高架桥极为相似。
当时广州下雨。
“那下大雨的时候呢?”
“下大雨的时候,所有的地方都彼此相似。”
或许如此,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在大雨中都杳无人烟。
睡美人的城堡。
雨水中荒凉的城。
这样的城市或许存在,如同一个标识,一次休息,是一个隐藏危机和能量的转折点。
也有可能,只是你的错觉。
仅此而已。
关于失忆症(1)
老实说,我对失忆症这个字眼一直有着各种不解,举例来说的话,就连最简单的问题我都心存疑窦,即,到底什么样的症状算是失忆症呢?
其他的疑问包括:一个得了失忆症的人是否对自己的过去有一片空白而焦躁不安?一个失去了一部分记忆的人如果意识到自己少了某段时刻的记忆,是否就不算失忆?失去了部分记忆,这个人还能算得上是一般意义上原来的自己吗?
如果说,只是失去了部分的记忆,一个人还可以勉强称得上完整,那么,要是一下子失去了在某个标识物之前的全部记忆,这个人会如何呢?
我几乎无法想象一个人丧失了在某天之前的全部记忆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会——不安?恐惧?痛苦?苦苦探询过去,还是重新开始生活?
无法想象。
我只知道,如果我处在这种情况下,大概会貌似正常地生活着,同时绞尽脑汁在暗地里探究自己的过去。我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或者说,我极为害怕自己的过去里有什么未知的东西,哪怕这玩意隐藏在失忆症的阴影里,哪怕它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像风干的标本,哪怕不具有任何危险性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也不行。
像我这样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在现代都市中并不少见。
这类人的共同点在于,无论是进饭馆还是在哪里,总喜欢挑一个角落,背靠墙面冲大家坐着;勇于付帐,羞于谈论自己。
1
我来到那个处于湖南西部小城的时候,正是金秋10月。准确地说,是10月14日。
这是南方真正的黄金季节,天气温暖,雨水适量,万物都在成熟,汁水饱满色泽金黄,凉薯和橘子便宜得出奇,满街是豆豉辣椒的香味……水牛、鸭子,还有一草一木都带上了丰饶富足的表情。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全因为我的主编异想天开的一个选题,说是要在报纸上每个月做一期关于什么各地民间绝活的专题。这个小城极为接近贵州,属于苗族自治区,乡民一向以勇武好斗著称。别看地方小,它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却赫赫有名,大概是因为出过几个著名的文人、画家的缘故……同时,它的美丽在那些名人的回忆录里也很是被宣扬了一通。
我选定这里,不光是因为这里有名,或者说是此地的蜡染和扎染确实有独到之处……还有一个原因,让我在丽江、周庄等一堆侯选者中挑中了它。
事后我意识到,就是它的名字使我砰然心动,那是一种隐约的召唤,一个遥远的期待……当时,我就是因为这种奇特的熟识感挑中了我此行的目的地。
我住在一家临江的客栈里,是一个船家开的家庭旅馆,面对着此地最著名的一条大桥。那桥是廊桥,上面有建筑物,黄桐木飞檐的形状异常优美。河两岸时不时有人从窗户里吊出一条几米长的绳索,把拖布放到江水里去洗个干净,让我忍俊不禁。
小镇始终保持着旧时的风貌,看得出来,当地人对此是经心的。新建的建筑也延续了当地吊角楼的风格,每隔几米就有木头钉成的果皮箱,样子不失古朴。连街灯都不是那种直杠杠的大灯泡,而是古色古香颇有意趣。我住的地方对面不到一米就是一个小小的土地祠,香火极盛,年纪大的老人路过还不时停下来膜拜致意,古风蔚然。
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上四处散布着三三两两的艺术院校学生,他们在用铅笔、水彩和油画画具写生,口音各地都有,另外至少还有两个摄制组也在这里忙活。各种杂志社图片社的人更是多如牛毛。和我住在同一家旅店的一个邻居就是云南省一个什么杂志社的,天天背着相机出去采风,早出晚归,我和他只有见面点个头的份儿。老实说,此人勤奋工作的精神颇使我惭愧。
我和他完全不同,白天我只工作半天,出去找人聊聊,再拍几张照片就收工,剩下的时间,我全花在泡饭馆喝酒上了。我的理论是,反正报纸也没有催稿,我对自己要求又不高。如此美好的时节,干吗要工作呢?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那个导演,他是拍专题片的,已经在此地逗留了2个月。
2
我通常在一家临街的店子里喝酒,那里的桌子矮矮的,放着几条长条板凳,地上老是油腻腻的,一不小心能滑一个跟头。店里拿旧得发黄的报纸糊墙,连天花板都已经被熏黑了。我喜欢那里的酸汤鱼,那是用当地河里产的小鲇鱼做的,极为鲜美,拿来下酒最好不过。
那天去店子里的时候,正好遇见那个摄制组收队。地方不够,一群人就挤在一起坐。期间还有几个家伙在地上滑了一跤,打碎了碗碟,闹哄哄的,总之弄得我头痛不已,只好埋头一声不吭地喝酒。导演也是北京人,看见我在大口喝贵州茅台酒厂生产的廉价白酒,颇为惊讶,于是两个人就交谈起来。
他问我有否喝过本地的包谷烧,我说第一次来就要的是那个,可是那酒一股工业酒精的味道,极冲,实在很难入口。
导演笑了笑:“这里大部分店里的包谷烧是那样的,因为他们大都统一从小酒厂里买酒嘛。不过当地人有自己酿酒的,确实不错。”
“是吗?”我来了兴趣:“什么时候带我去试试?”
他沉吟片刻:“明天好了,明天中午。”
关于失忆症(2)
本地的包谷烧苦涩难当,勾兑得极为难喝,但是正如导演所说,那家位于小巷深处的小店的自家陈酿还颇有点意趣,那店子在一条小街尽头,没有招牌,如果他不带我去,我势必找不到。
但是我的心思并没有停留在包谷烧上,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个人,彻底打乱了我在此地的停留计划。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到了那家小店,是中午11点半,坐下后,导演和我开喝,点了几个小菜。说起来,我们好象还有几个共同的熟人,不由得感叹世界真是太小了。正在兴头上,大概12点钟左右,一群群初中生样子的孩子们开始成群结队地走过我们的面前。
“附近有所学校吧?”我问。
“呵,是,”导演回答:“一个中学。就在街那边的拐角上。”
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追逐着,给这条寂寞的小巷子带来了些许生气。大概是到了吃饭时间,有几个老师样子的男男女女也踱进了店里。他是不是和他们一起进来的,我不知道。但是当我注意到有这样一个人存在的时候,他已经坐在最里面的一个小桌前面了。
他的面前放着一个盛酒的塑料壶,顺便说一下,此地盛酒用的是那种当年大家盛油的塑料壶,这是在大城市里几乎已经绝迹了的东西。我们喝酒是一杯一杯向老板买的,而此人却直接把壶拿到跟前去,可见酒量可以,也是这里的常客。
我看见此人的时候,他正闷头一个人坐着喝酒,面前只有花生和一碟小菜。他喝酒的速度简直和喝水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吸引我注意的不是他的酒量,而是某种特殊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确切地说,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种熟识的气味几乎是弥漫在他的四周,充满了整个小店,盖过了人声鼎沸和浓重的辣椒味道……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我发誓,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不会吧?”导演对我的话半信半疑:“大概……你来过这里?”
“平生第一次。”
“那你们怎么可能见过,我倒是隔三差五地看见过他,只要是这个点来吃饭,他总是在这里的。大概,你们在镇子上见过。”
“不是吧?”我摇摇头:“我好象不是在这里见过他,而是……而是在北京的时候,在很久以前……”
“完全不可能,”导演说:“他是本地人。”
是吗?我自言自语……也许……
就像心灵感应一样,此人忽然放下酒杯,看了我们一眼。我尚未出口的话立刻噎在了嗓子眼里。说来好笑,我虽然对他有着某种莫名其妙的熟识感,却直到这时才得以看清他的长相。此人的样子倒是十分平常,只是有点憔悴,穿着一件本地人常见的夹克。他看了我们5秒钟,如同注视桌子上的玻璃杯一般茫然,然后又开始闷头喝酒。
看到他的脸,那股似曾相识的感觉反而淡漠了些。毕竟,眼定定地瞪着一个人并不礼貌,我低下头去看自己的酒杯。
我们离开这家店的时候是下午1点,此人在12点45分离开。看他的速度,至少已经喝了快半斤白酒,但是脚步绝无虚飘之感,脸色如常,甚是了得。我注意到他没有结帐,只是跟店家点了点头。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我挪开椅子给他让了点地方,他低下头来,我们的目光交汇了一瞬间。他像看地上横七竖八的板凳一样面无表情。
“你看,他根本就不认得你嘛。”导演说。
“也许,”我喃喃道。其实就在刚才那一刹那,我的感觉强烈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那个场景,那种光线和气氛,无一不让我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仿佛回到了过去。
结帐的时候,我问伙计,这人到底是不是本地人?
伙计回答的挺简单,就算是吧。
怎么叫就算是呢?
因为他来这里2年多,看起来是要常住了,因为他现在在边上的中学教书。
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
教什么?
谁知道教什么?反正每天到这里来喝酒就是了。所以都挂帐的,一个星期结一次吧。
是这样……
伙计补充说:“不过酒量真是好,人也很不错的。就是不太说话。”
他是什么口音?
不好说啊,总之不是本地人。伙计搔搔后脑勺笑了,我也笑了,在这里问对方是什么口音,简直和用黑色的眼睛在黑夜里寻找光明这样的诗句一样莫名其妙,我老是觉得,这诗说的是猫头鹰。
导演非常诧异:“你还真的把这事当事儿了?”
那是。
为什么?
不知道。
3
之后的每天中午,我都在这个小酒馆中喝酒。说是喝酒,其实无非是找个理由观察一下他而已。
这件事情实在是异常古怪。连我自己也诧异不已——我的采访有时候需要到这个小城附近的镇子上去,但是即便是这样,每到中午11点左右,我仍旧会赶到这个酒馆里坐下。
他毫无例外,总是在11点半以后踱进来,叫的东西千篇一律,无非是花生米和一个炒菜之类,酒也是总用塑料桶盛着放在桌子上的。我算了一下,如果说我们用的纸杯子能盛2两到3两左右酒的话,此人一中午总是喝掉4杯,快1斤多的白酒。
关于失忆症(3)
期间,无论这个店子里进来什么样的人,即使看起来像他的同事,也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即使他们主动和他打招呼,此人也绝少和别人交谈。
他的表情让我想起死火山下内湖的水面,一切惊涛骇浪已经在外面高高耸立的岩石上撞得粉碎,在内湖,只剩下凝固成各种形状的黑色火山熔岩,水深不见底……棕榈不再摇曳,没有寄生物,没有大大小小的鱼类和寄居蟹,一切都停止了生长……
我越是看他,就越是肯定,不管是不是认识,我和此人在以前的什么时候见过,接触过……那种熟悉的味道简直像大街上辣椒青蒜豆豉的炒菜香一样扑鼻而来,汹涌澎湃,甚至能把人从睡眠中唤醒。
但是我的感觉也只到此为止。
接下来该做什么呢?我越是那样肯定我和此人的某种联系,就越难开口和他说话。
和陌生人交谈,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简直不算什么。如果我的同事听说我在这个小城花了4天的时间,也没能鼓足勇气和一个人交谈上,一定会当成天方夜谭,一笑了之。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每当我试图和他说话的时候,那股熟悉的气味就会立刻消散,变质……我的疑惑和恐惧呈几何级数的速度上升,脑子里一片空白。内存不足,传送中断,Ctrl+Alt+Del……一片空白……
所有的人都会心有不甘,大声对我叫喊:“就这么完了?再说两句,再说两句……”但是,我就是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这样,我被钉在原地,每天看他来去。
倒是导演无意中帮了我的忙。他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在河边碰到了我,我正要坐着小船到江的上游去。
“你最近老是去那里吧?”
“是啊,你倒是一直没有来。”
“我昨天晚上去来着……这几天阳光太好了,趁天气好赶紧去邻镇拍点东西,有人告诉我明天要变天了。你是不是要离开了?”
我跳上那竹子做成的小船:“明天走。你呢?”
“我也快了。那么,北京见吧……”
“北京见。”
就在船家把船撑离码头的一瞬间,他仿佛想起了什么:“对了,你说你认识的那人……”
我一阵紧张,赶紧让船停下:“什么?”
“有可能你是对的,他是北京人。”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昨晚聊了几句,他在这里教初中的历史。他没有告诉我是从哪里来的……”
“那……”
“但是他的口音错不了。对了,他的同事我也见过。他们对他也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两年前来的,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当上老师了……你也知道,小城嘛,师资力量实在有限,当然不象北京……”
“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导演做了个一无所知的表情。
河中水草异常茂盛,从很低的角度上看过去,水草顺着水势飘荡,给人一种小船在水面上滑动如飞的感觉。下午的太阳十分温暖,照射脸上,我在眼皮下看到了红色和金色。
他开口说话会是怎样一种感觉呢?声音是否低沉?语调是否平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