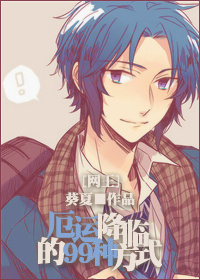高峰体验-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许,也许,也许他是在用另外一种方法谈论所谓的历史感,或者说,权力欲。
双城故事(5)
关键问题在于,一个人将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一个人是否认为自己的一生中将高潮迭起,永远幸运?一个人是否意识到了所有的事情,都只在追求的过程中美妙无比,在追求到的那一刹那就会从高峰跌落,变得平淡无奇索然无味?一个人是否要一辈子执着于一件事情呢?
你可以说,那些一辈子执着的人是中了魔力的毒,或许魔力能持续一生。不过这是幸运
者,包括那些执着于一件事情无所得的人。只要他们觉得快活就行。倒霉的是那些中途试图归零,但是又无法抛弃已有基础——就是要减灾的家伙们,折腾了半天,却到底意难平。
但是其实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
五
所有的海滨城市都会有这样一条热闹的街道,那里会有许多卖海产品的小店铺,里面挂满贝壳做成的项链、苍白的珊瑚、军用望远镜、廉价的泳衣和花哨的泳镜。那会是这个城市里最主要的街道,上面有许多的饭馆,海鲜被放在红色的塑料盆里在大街上一字排开,地面因为撒了水变得湿漉漉的。在这样的饭馆里,尽管旅游季节已经快过去了,但是他们仍然会把便宜的蛏子卖得比鱼还要贵,做成咸渍渍、汤水淋漓的一大盘,扔到外地人的面前。
我和他穿过大街,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找到一家饭馆,里面坐满了本地人,喝着冰镇啤酒,大声喧哗。我们吃了一顿用本地方法烹调得十分地道的海鲜:切得飞薄的大蒜和青辣椒爆炒蛏子、油淋扇贝、肥美的螃蟹、空心菜……饺子有虾仁和鲅鱼馅两种选择,还有刚刚炸好金黄微温的辣椒油,海鲜新鲜得仿佛刚刚离开海面,缩成紧张而有质量的一团,带着海水的咸味,让吃的人浑然忘忧,哑口无言。
我们在大快朵颐之后不约而同地点了根烟,陶醉地靠在椅子上。
“人生最大乐事无过于此。”他闭着眼睛说。
我同意。
我想我们最终之所以能够这样其乐融融地坐到一起,无非缘于最简单的东西,不再是魔力,魔力在第一晚已经消退掉了大半——而是和谐。关于胃肠,关于性生活,这些甚至不用太好,太惊人地和谐,只要彼此都还合适,这种关系就能够延续下去。
和谐在魔力消退之时有助于保持关系,懒惰也是如此。说到底,这是因为它在寻常的生活之外,是第三个城市,是广州和上海之外的城市。还因为我们都已经到了这里,而且决定在这里呆上4天。即便此时觉得没有想象中的和谐,也回不去了。
这就是在现实之外的好处。
而我们是否还能在明年回到这里来,那就很难说了。在这个城里,一年只有3个月色彩缤纷人声鼎沸。当然了,还有大海,大海也只在一年中的这3、4个月中存在。在平常的日子里,大海只是人们不可或缺而又完全漠视的一分子,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一个被人遗忘的布景,亘古不变。
当你真的到达某处,当你真的得到那个人的时候,魔力便开始消退,我说的是真的。不骗你。
关于魔力的消失,还有很多的佐证和案例。
“为什么?”
问这话的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和女友的关系刚刚破裂。这两人本来各自有一段婚姻,在第一次遇到之后,分别费尽千辛万苦离婚,最后终于生活在了一起。在离婚过程中,他成了朋友圈子里关于爱情的象征。
然而就是这对 “象征”,在生活在一起不到一年的时候出了问题。女方提出分手,并且搬了出去。“象征”极度惊愕,然后继以极度的心理紧张和焦虑。他暂时停止了工作,呆在自己家里抽烟喝酒熬夜,对所有试图安慰他的朋友问“为什么”。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们的事情?”
“为什么?”
我叹了口气:“你吃饭了么?”
“到底为什么呢?”
……
“拜托,你能不能问点推陈出新的问题?”
……
我环顾四周,这个地方因为男人熬夜而变得乌烟瘴气,四处乱放着衣服和影碟。当然他们的家以前也是影碟、书和衣服乱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女主人不在似乎影响到了这个屋子中的某种表象,到底是什么呢?
注视了半晌,我忽然意识到少了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屋子里,所有属于她的物品全部不在了,书架上的书少了一半,CD架子空了一半……所有摆设上的一些原来标识女主人存在的小东西统统不见了,比如花瓶下的手工编织垫子,拖鞋架子上的罩子等等,消失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这一切比她不在场这一事实本身还要让人体验到双方关系已经结束,结束得干干净净,那是逼真如同冰冷的玻璃墙面般的结束,雨水、光线、空气和愿望都无法穿透的玻璃墙面。
一切都已经结束,和为什么无关,和如何开始无关,和人的愿望无关。
“为什么?”我问他。
“不知道。”
“人们为之痛苦,究竟是因为爱情消失,还是因为爱情存在呢?”
“消失。”
“真的么?”
他颔首:“你看看我,我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不愿意相信,曾经属于我的这个东西居然不再属于我了。”
“还有更糟糕的,也许一开始就是个误会,它根本不曾属于你,或者说,它根本就不存在。”
双城故事(6)
“喂,你别雪上加霜行不行?”
……
所有的谚语,所有智者和死去人们的智慧都在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过犹不及,过犹不及。无论你缺少什么,你首先会厌烦你不缺少的,既而渴望你缺少的,然后,一旦你得到了
,就会像以前那样厌烦,最后,只有厌烦留在这个世界上,和你相守到老,到死。
“象征”不赞成我的这个看法,他认为人是可以保持高峰体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前提取决于他遇到了自己百分之百的那一半,他的情人,他爱的人。我看见过他和别人在一起的样子。大家喜欢一样菜,很快把它吃了个干干净净,他是个好主人,渴望让他人得到满足,于是又点了一份。这回,除去少数几个人,其余的人根本没有动筷子。那盘菜就这样失色了,冰冷了,凝结着油花,他摇头叹息:过犹不及过犹不及。
只有温柔的,对生活毫无餍足,贪婪的和敏感的人会这样做,只有渴望给予他人什么,并且奢望一次性满足对方,希望“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生活”的人会这样做。
但是,我了解我们这个族类,了解他,了解我自己,了解所有的人。我知道我们是在怎样地因为某种缺失而辗转反侧,四处寻觅,我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渴望,怎样折磨人,怎样迫切地希望有某种灵丹妙药一劳永逸地来帮助人摆脱困境,“从此幸福地生活”。我也知道这种缺失是怎样危险的海市蜃楼,它大张着黑洞洞的嘴巴吞噬一切,总是饥肠辘辘,总是无法满足。所有一开始被视为良药的东西最终都将被这种饥饿和厌倦毁灭。这个族类永远无法停止抱怨和寻觅,因为那就是他们本身。
这个古老的咒语很快将降临,最终有一天,我们将厌倦我们自己,这一切缺失的根源。
六
第四夜,也就是最后一夜的时候,海上又起了雾。大海近在咫尺,但是我只能听到它永恒低沉的波浪声,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
“雾真大。”
“恩。”
我们在露台上坐到很晚。海雾很重,带着咸味,我的头发因为湿润的空气而变得卷曲,椅子上金属的部分上渗着水珠,触手冰凉。
“这几天,你快活吗?”
我思考半晌:“不错,你呢?”
他颔首:“是的,不错。”
对于已经过去的一切,我们有些伤感。
下了结论之后,又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即全都如释重负。
我说过,魔力是存在的,这是常理,而魔力行将结束,这是结论。
后来我才意识到,网络时代的美梦在他问我“快活吗?”的时候便已经趋于破灭。那时候,各个风光一时的网站第一批融资已挥霍告罄,盈利遥不可及,后续资金杳无音讯。投资人开始撤退,花钱的人开始做噩梦。
据同行们反映,按名片夹中换过名片的人留下的座机来找对方,开始变得困难起来。后来发展到这种程度,即如果当时彼此不留下手机,根本就别想知道此人现在在哪里了。这就是说,我认识的人在快速地变换工作,有时是一个公司消失了,有时是一个公司成立了。
那阵子,我有种幻觉,就是我的熟人们像秋天的叶子一样在漫天飞舞,我虽然知道他们终将尘埃落定,却很难确定时间。
消失的公司越来越多。
那年秋天,我常常在一个酒吧喝啤酒,那里本来是个徒步旅行者聚会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些从网络公司中离职的中层职员们的集散地。我被这些人弄得有些无名惆怅起来,酒吧里一直在放着些4、50年代的老歌,平克劳斯比和他的甜嗓子把这里的空气搅出一片涟漪……
这种时候,我老是回忆起在海边眼睁睁地盯着雨看的感觉。
那东西是什么呢?说到底,这种感觉恐怕过于个人化。但是当时我确实察觉到有种东西开始越来越多地掺和到了我身边的空气里,如同粉尘般弥漫在四周,甚至使空气的折射率都为之改变。
我当时只是懵懂地觉得,它类似一种伤感,一种年华已逝,永不复回的东西,像月亮背后的阴影,像雨中的太湖或者大海……
和他,从海边回来之后,我们又约会过几次。
整个关系轻松愉快,但是无疑少了些什么。
或者说,有某种让光线折射率为之改变的物质,如同玻璃幕墙般慢慢树在了我们之间。这东西生长得如此巧妙和顺理成章,如同攀爬在水泥墙上的爬山虎,绿叶蒙尘,在微风中发出沙拉拉的声响,工程浩大,令人叹为观止。
这就是魔力的减退和消失的过程吗?
不知道,这无疑是种过于个人化的感受。
但是确实有什么东西,已经被封存在了那个北方不甚出名的临海小镇,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市。
时光荏苒,那东西或许还能够被找回来,比如再次的逃离,和这个人。
也许,是和其他人。
直到后来很久以后,一次在市场上买盗版光盘,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在那个网络泡沫行将破灭的秋天所体会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那些盗版的片子是由一个据说是电影学院的家伙批量生产的,做得极为精致,让购买者对此人的敬业精神立时三刻肃然起敬。那些片子全部是精品,装在牛皮纸袋里,上面印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一句话,大意是生活不断继续,人如逆水行舟,只好不断向前云云……
双城故事(7)
直到那时候,我忽然发现,盖茨比眼中的世界和我们在那个秋天眼中的现实颇有些重合之处。那是菲茨杰尔拉德笔下荷兰水手眼中充满机会的新大陆,那是人一瞬间发财致富,下一个瞬间一文不名的地方。重要的是,那是唯一一块可能让平常人实现梦想的土地。
美国梦,互联网,梦幻之地……所有这些在1998到1999年间萦绕我们的气氛和欲望具有一种魔力,热烈而直白,动人心弦。如同孩童眼中的世界,新奇稚气,那是一种异常美好的
憧憬,只能存在于新大陆,因为尚未遭受挫折而显得格外幼稚,也格外美妙。
奇妙的是,只有在它一去不复返时,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一点,既而感到伤感。
伤感是魔力消失的标志,是清醒的前兆。
一旦感到伤感,魔力就像盖茨比的梦想一样,永远消逝了。
在我明白这一点之前,我的那批朋友就已经全部开始了降职减薪或者是找工作的历程。归零的人和继续的人都在不断前行,当然,他们还会在酒酣胆热之际对我说起他们和几百万擦肩而过的事情……这一切在一些写字为生的人笔下已经变成了回忆和过去。
或者说,历史。
一些人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历史,更多的人被人遗忘了。
结尾
我和他的约会渐渐结束了。
这是必然的——即便两个人之间的那种东西确乎存在,也会如同一件行李,被存放到了那个小镇上。回去取需要时间,两个人一忙,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另外,还有许许多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更何况,魔力已经消失。
“了不起的盖兹比”中不是说了么,生活飞逝,于是,人如逆水行舟,只好不断向前……
后来,连这个生活以外的约会本身都已经被我逐渐淡忘……直到有一天,我和一个广东朋友说起上海和广州的相似之处。
“上海有一些地方很像广州,这听起来有点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吧?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在上海静安寺波特曼酒店的附近,有一段路和广州花园酒店附近的街景相似得惊人:一样建在露天的风味餐馆,竹子做成的桌椅板凳。树上挂满了写有“避风塘”字样的小灯笼,一到晚上8点就会点亮,发出红色温暖的光。一样的马路和过街天桥,到了夏日,在上海闷热到极点的时候,连飘荡着水汽的灰色天空都完全一样,人们会带着同样厌倦和懊热的表情在马路上穿行……”
“你说广州的哪里?”
“花园酒店旁边。”
“你搞错了,花园酒店旁边没有避风塘。”
“真的吗?”
“真的,要说泰国菜馆倒是有一家,叫蕉叶。”
……
“你说的那个地段,听起来倒像是在远洋饭店附近。”
……
是真的吗?
朋友走后,我注视着面前的水,有点迷惘。
我是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湖边别墅,来的时候就是阴天,结果到了傍晚下起雨来。雨点不停地落在灰蓝色的水面上,然后,连涟漪都没有来得及泛起,就消失于无形。看久了这种情形,人会产生一种奇怪的置身事外的感觉,而且有些伤感。
我匪夷所思地想起太湖,那个巨大的湖泊,很像大海。
真是这样么?是我从一开始就记错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两个城市的相似之处,究竟是因何而起呢?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之间存在的那种东西,难道只是个美丽的错误?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魔力究竟来源于什么呢?
究竟是我的错觉,还是其他人的错觉?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