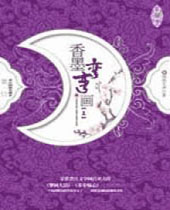心路弯弯-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森孔的妈妈看大妯娌孤独的日子难熬,便对我姑姑说,姐姐,我三个痴儿中,你愿意要谁就让谁去你的膝下承欢吧。当时森孔的两个哥哥都己结婚生子,我姑姑无论要了哪一个都只要坐在家里带孙子承欢膝下的。可她却偏偏要了这个最小的侄子到身边,并要承担繁重而又忙碌的教养义务。这样从他承继过我姑家后,由于表兄弟的关系,就开始了我们之间太多的接触。
自从七六年大哥陈小毛和我还有森孔一同迈进了芗溪中学的校门,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以至于一年后磕头结义,成了亲蜜无间的兄弟了。
在学校,二哥的学习成绩其实是挺不错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全年级大哥的成绩在全校一直名列前茅,我和二哥的成绩比大哥稍逊一筹,在我与二哥之间他的成绩又略胜我一些。两年后,也就是时间到了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我们三人一同迈进了中考的试场。
报考时,我们三个都想报考大学,老师们、特别是班主任张世昌老师坚持要我们报考大学,说我们的成绩一直稳定,没有大起大落。可那时,我们十六、七岁没主见,便都回家问父母。那时我们三家的境况都差不多,在农村并不富裕,为了早日寻到个饭碗,有个固定的工作,大人们认为还是报考中专稳当些,于是我们便齐齐的报考了中专。
不知老天有意捉弄人还是天道不公,我们兄弟三人一同走进试场,成绩也差距不大,可到最后,我和大哥双双被九江师范都昌分校录取了。只有森孔名落榜外了。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下午,我跑步到了大哥家把录取的消息告诉他时,他也在前一刻接到了通知书,并录取了同一所学校,我俩双双沉浸在了欢乐之中。欢乐过后,大哥说,不知森孔考上了没有。于是我俩又一起往森孔家里走去,待来到我姑姑家里,森孔一付无助的表情站在屋前的空地上,脸上淌满了难过的泪水。
此情此景,还有什么值得庆幸的?我们兄弟三人无言以对。静默中我们三个来到了鄱阳湖边,看着青青的水草,静静的湖水,飞翔的鸥鹭,三个人不由同时大声的吼叫了起来:“啊……啊”……
后来,我和大哥便走进了校门,开始了新的学习。在我们临毕业的那年,森孔结了婚,我和大哥参加了他的婚礼。
再后来,我和大哥便被分配在了不同的地方参加了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三兄弟在一起相聚的时候就慢慢的少了,只有在年头月尾过春节的时候在一块聚聚了。
一个阴雨的日子里,我那表嫂用独轮车推着我细姑来到了我家。她们告诉我二哥患肝癌住进了医院,己是时日无多了。这无异于一个霹雳在我头脑中炸响,我在第二天便约齐了大哥去医院看望二哥。
来到医院,见二哥己憔悴得只剩下了一身皮包骨头。怎么说呢?我们三双六只手重叠在一起什么也没说,有的只是心里那一份的酸楚和无奈。有的只有虔诚的祷告上天保佑二哥了。
再再后来,待我们再去看望他时,嫂子告诉我他撇下她和两个儿子享福去了,留下她母子三人在这尘世上受苦受难了……
二哥走了,走得那么匆忙,你可知我和大哥的心里是怎样的凄凉?二哥,你在那边可安好?是不是真的有天堂?如果有,愿你在天堂快乐安祥!
谨以此文纪念逝去的二哥森孔,并寄托我们心中永远的怅惘。
怀念达范
达范,是我在师范学习时的同班同学,姓江。是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以一个社会青年的姿态重新返校补习,并与我同年参加中考且同时被同一所学校录取,又分在同一个班级读书的。
说起达范,他一米六五的个子,长着一付小圆脸,细细的眼晴常常是眯缝着,两排稍稍外凸的牙齿泛着淡黄的颜色。腿长腰身短,走起路过稍显不协调。平时说起话来声音倒是尖脆,与他是个成熟的男人气概有点不相符的带点娘娘腔。
虽然我在中学读书时他亦在校补习,因为他是社会青年返校学习,在年龄上与我们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他在校补习的一年时间里,虽然我们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我也从没与他接触过,所以我们彼此并不相识且完全是陌生的。只是在参加招生录取体检时才认识他的。
自从认识了他以后,我和他便有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一起了。且不说中学同学一年,因为那时没有接触,互不熟识。进入新学校后的两年学习时光,便让我对他有了很深的了解啦。
达范的身世很悲苦,幼年便失去了双亲,是在村人们的百家饭里慢慢熬出来的。他虽然有个叔叔,可也是身单力薄。在一个劳动日才七分钱的年代里,有着三个小孩的叔叔自顾都不暇,哪里还能顾得上他哟。
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春天般的温暖。在孤儿的生命世界给予了阳光雨露,依靠政府的抚养,一个孤儿上了学,成了材、成了人。最后靠自己的艰苦努力,为自己在社会上立足争得了一席之地。他的成功较常人又何止付出了不知是多少倍的努力。
毕业后,我们被分配在同一所中学,当上了少年时特别崇拜的人民教师。由于它的身世和阅历的原因,在单位上他得到了普遍的关心和爱护。他亦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上刻苦努力,学习上从不放弃,他的那种认真的劲头谁也不能比。记得他连续几年都是优秀教师代表出席县上的表彰会。
只是他的脾气有时就是太倔。他如是认定了的事,任九头牛也拉不回。我们有时也故意逗他,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并大家在一起同声附和,他便和我们抗辩,非要辩出个是非曲直来才罢手。
这样我们在一起从教了六年。一九八八年,达范因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原因,调离了原单位,到他妻子工作地方的那一所中学任教,从此我们就分开了。后来听人说达范得胃癌了,我们不信。便约了其它的几个同学骑自行车去几十公里外的他家里去看他,那时他正好从县医院出院回来在家疗养。
见到他时,整个人只剩下个人形了,我们同学几个都不由倍感凄凉。本来是多么壮实的一个人,如今成了这个样,怎不叫人心为之酸、心为之痛呢?同学间本就是无私、清纯的友谊,有不得半点缺撼的。他的病痛牵着我们这些昔日的同学们的心。
达范自己的表现倒还平和。他告诉我们胃全部被切除了,有病灶的全拿掉了,医生说没有问题了。听了他告诉的话,我们全都为他欣喜。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还有时在适当的机会碰面,表面上也见他确实恢复得蛮好。我们便只要见了面就高兴地祝福他并要他多注意休息,保养自己。
可能是好人命不长。达范在手术后仅仅只过了三个春秋便黯然地撒手西去了。出殡的那天,我们二十几位同学都去送他上路了。想到他的过早的离去,我们大家亦不免有了兔死狐悲的哀叹。哀叹人世的无常、哀怜生命的脆弱。
达范就这样走了,那红红的薄皮棺材装进了他一生的艰辛、一路的风雨、一世的期盼,去找寻那只管生他而又不养他的父母理论去了……
万语千言说不完同学情谊,砚田墨海书不尽对学友的怀念。谨以此文告慰达范:你安息吧,你的名字无时不在同学们的唏嘘声里打转,你的治学治人生的态度无时不在后人的口碑声中流传!
永远的烛火
三尺讲坛度人生,燃尽心血启后人。天地国亲师,牌位上占了末位一个位置的职业。别看它占了个位置,这还全托了孔老夫子的福。话说得好听点,叫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说得不好听,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更有个响亮的名字:“臭老九。”
可是好听也好,响亮也罢。这世上可偏偏就有那么一种人,他只要爱上了某一种职业,就甘愿去为这个职业,去奋斗,去献身。
这里我要提到的是我在芗溪中学上初中、高中时期的化学老师冯克正以及关于他的一些轶事。
冯克正,江苏扬州人。永远留着小分头的冯老师,头发总是乱乱的,上课时,那稍带扬州音的普通话有时让我们听得莫名其妙;不修边幅的穿着在身上倒给人一种洒脱、飘逸的感觉。
他是我初、高中学习时,带了我四年的化学老师。冯老师的化学课上得生动,形象。七十年代,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仪器缺乏,要上好一堂化学课较之现在的直观教学不知要难上多少倍,可冯老师却总能用尽心力,想尽办法让课上得直观、易懂。
记得上初二时,他给我们讲分解反应。他说:“生石灰和水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反应,放出什么气体?”同学们便抢着答道:“氮气。”他则笑眯眯的说:“我就知道你们在放氮气。这句话是一定要说清楚的,是分解出二氧化碳气体,不是氮气。此碳非彼氮也”。
还有一次是晚上下自习后,同学们都去寝室休息了,我由于有一道化学题不管怎样冥思苦想,就是想不出解题的方法,在教室一直思考到了半夜十一点多,还是不能解答。于是,我便来到了冯老师的窗下寻求指导。我敲了冯老师的窗户,冯老师己经睡下了。我抱着释惑的强烈愿望用力的敲击窗棂并大声的叫着:“冯老师,冯老师”。
冯老师被我吵醒了,捻亮油灯问:“谁呀?”我说:“冯老师,是我呀,有个题目做不出来,求你指导。”他说:“我睡着了。”我说:“你在跟我说话,怎么是睡着了?”他接应着道:“上了床,我就是睡着了。”嘴里说着话,他己披衣起床了,并很快的开了门把我让进了房间,揉了揉睡意朦胧的眼晴接过题目认真的看了起来,并耐心的向我指出解题的原理所在,使我茅塞顿开,终于释疑了。之后并叮嘱我要注意休息,说会休息的人便是会学习的人,两者都有个度的问题,二者一定要掌握好。我记下了老师的话。
七九年,我走出了芗溪中学的校门,继续踏上了求学之路。三年后,待我再回到母校去拜望当年的师长们时,独独不见了冯老师。后经问询其它的老师们,有老师告诉我,冯老师调动了,进城了,去了百多公里外的景德镇了。听了过后,我心里有种酸酸的离愁。
时间又过了几年,我听同学告诉我,冯老师走了,他是站在讲台上走的,走的时候是用手按着腹部倒在讲台上的。正在上课的学生走上讲台喊老师时,冯老师己安详的合上了眼晴,脸上的表情虽稍带痛苦,可痛苦的表情后面透着幸福的笑容。
原来冯老师身患肝癌,他早知自己时日无多,便隐瞒自己的病情坚持上课。因为他离不开三尺讲台,离不开学生。讲台是他的天地,学生是他的朋友,教学是他一生不变的追求!
烛火不灭,点亮满天繁星。师魂永存,精神永励后人。你安歇吧!冯克正老师:满天下的桃李给您增光,满园的鲜花送您芬芳。慰藉您在天上的守望!
单骑走江湖
一九八五年的夏天,被灸热的太阳烤得枯黄的野草无精打彩的低垂着高傲的头,路边树上的知了在有气无力地叫着:知…了、知…了,知了。这天是星期五,上午十点四十五分,宜初上完了自己的课程,便匆匆动手做午饭,十一时三十分宜初吃过午饭,便拿来毛巾顺手擦了把脸,认真的检查起自己那辆己经骑了三、四年的永久牌51型自行车来。
早在上个星期天宜初就开始准备今天的远行了。上星期六他己经用公费医疗在定点的医院请熟悉的医生开出了两瓶氯化钠盐水,这是预备上路后解渴时用的,免得在路上要买水喝。这次的目的地是鄂南的黄梅小池,全程有一百三十多公里。宜初在八三年与妻子结婚后不到半年,妻子便患上了人听人怕的大病――鼻咽癌,这在当时可是震惊十里八乡的大事情。
宜初今年二十三岁。为了给妻子治病,家里己是债台高筑,欠上了超过万元的债务。为了还清债款,宜初不得不铤而走险去贩运在当时控制特别严格的卷烟。无论是在陆路还是在水道上,设立的层层关卡森严,为了躲避检查,宜初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单骑去进货。这样既节约了来回柒块多钱的路费,又可于关卡管理疲惫时迅速过关而一举两得。
宜初是一个小学老师。人长得可是身材高大、体格魁梧,高鼻梁、丹凤眼,国字型的脸上五官端正,清澈的眼睛里透着精明和干练的气质。叫人一看便知是一个有胆识,有气魄的男人。贩卖香烟:这在那个年代来说是属于严重的投机倒把行为,作为一名老师,宜初心里也很明白这个道理,可家里的困境时时困扰着他,尚在后续治疗中的妻子要继续治疗,嗷嗷待哺的幼女要哺养,亲戚朋友处的借款要尽快还上,这对于一个月工资只有四十一元的宜初来说无疑比三座大山还要沉重。他就是二十年一家人不吃不喝也还不上债款哪!所以他便在无奈之下加入到了在当时称作投机倒把的行列了。
十二时多一点,夏日正午的日头似火。宜初把两瓶氯化钠盐水和一条旧毛巾放在自行车前面的篮子里,在后车架上绑好修车的工具袋和一只小型汽筒,戴着一顶破草帽上路了。由芗溪到中馆的二十几公里沙石公路上厚厚的尘土被车碾过时黄尘漫天,宜初不时腾出左手捂着口鼻躲避那呛人的黄尘。宜初边骑车边想:总计一百三十多公里的路程,我得保持体力要匀速前进呢,不然到最后怕骑不动了,争取在天黑以前到达浔阳就好了。因为小池就在浔阳的对岸,两地隔江而望。这样想着宜初真的就这样做了,待到中馆时宜初己几乎成了个土人,灰头土脸,汗水和着黄尘一道一道写在脸上,活象古装戏中的大花脸滑稽极了。
终于松口气了。因为由中馆至浔阳的公路相对要好走些了,整个路程是简易的柏油公路。宜初在路边的水塘里用毛巾洗了把脸,又喝了两口塘水便再次骑上了单车向浔阳而去。一路经北炎、五里、马影、文桥、均桥、三里,于下午五时左右来到了鄱阳湖口的重镇:石钟镇。在这里要乘坐渡轮过江,宜初在渡口待汽车上船后立即赶着自行车也上了船。二十分钟后渡船靠岸,宜初一看日头己是西斜了,还有二十几公里的路要赶呢,便迅即拿起盐水咕咚、咕咚猛灌了一气,顺手把空瓶丢在路旁,此时两瓶盐水己喝光殆尽了,用手一摸身上,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