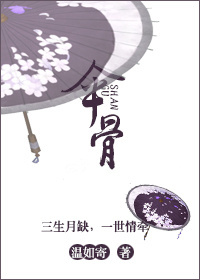红纸伞-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第一回的交战,她就输了,因为他的胡笳。
今天算是第二回的交战了,她扮演了他曾爱过的白薇,这一切注定了她往后的沉陷,竟然觉得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冷傲,他一定也是一个很好的男人;这种男人令人心慌意乱,令人顿生绝望的幻想与孤绝的无力感,但他是女人最想要的那种男人,他会是女人心目中的英雄和保护神。她好庆幸就这样被他牵引着,由死去的素苹变做不堪死去的白薇,再做回秋晓,做回那个被他用胡笳撩拨着的那个不安分的女人——噢,望尘,为什么会是这样?噢,望尘,告诉我,牵着我走来的这个男人,他……到底是谁?
他们三个人就这样默默地对望着,静静地对视着,钟望尘,古居,秋晓。
各自心中都有着很奇特的感觉,好像他们都是走了很远的路才得以相见,好像他们生来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狭路相逢,让他记住了她,再让她记住了他。
钟望尘只觉得心里有一种惊叹,一种在平淡闲散的注视中突然令瞳孔放大了的惊叹。他在秋晓的表演中感知着那份陌生的游魂一般的白薇的气息,那些冗长的琐碎的戏剧铺垫,那些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生命终结之前是和了殷红殷红的血,汨汨地从不忍不堪的隐痛中往下流淌,浸染在阴丹士林的胸襟上,让她再也做不回昔日那个清纯的被他在墓园里发现的忧郁孤独的女孩——此刻她的灵魂正离开躯体,在湖畔的哀歌和风声雨声之中饮恨啜泣。他以为她是早在好多年前就告别了那片墓园的,他以为她只存在于他的世界和他的爱情中,只会在属于他们的一方天空中像鸽子一样地飞,一如飞在幼年的回忆里,飞在那把红纸伞的一张一合之中,一片片灰云,一片片白云,那些鸽哨声声的翔影,直冲云霄。云中漫步的日子多浪漫呀!他一挥手,她就紧跟而来,他牵着她的,她牵着他的,他们就这样走过一生再走过一世,生生世世不弃不离——是这样吗?秋晓?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秋晓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让钟望尘觉得陌生的光芒,不似胆怯的,没有焦虑的,蕴涵着浓浓深深的莫测和浅浅淡淡的哀怨。更有一种乖觉,一种楚楚可怜,一种寻求保护的神色,甚至有一种精灵般的狡黠和聪慧。这样的感觉在钟望尘的心里像流星一般地闪烁,划下一道长长的轨迹和一条令他感到眩晕的慧尾,他不禁又想起十二岁时做的那个红云笼罩的梦,那只小小鹦鹉绿唇儿是那么急切地飞来,闯进他的梦——它是从哪里来的?最后又飞向了哪里?钟望尘早在与它双眸交汇的刹那就认定了它是从灵魂深处走来的朋友,但他却从没想到,事隔多年之后他又从秋晓的眼睛里捕捉到了这种令人柔怜无比疼痛无比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当秋晓和古居并肩从台子上走下来的时候,钟望尘竟然迷梦般的再次看到红云闪过,看到那只他们都认识的绿唇儿再次从记忆的星空里扑张着翅膀直飞而来——不是错觉!钟望尘看见它落在了古居的手上。
“绿唇儿?!”
“绿唇儿?!”
秋晓和钟望尘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还是那通身的碧绿,羽毛油油亮亮,绿唇似凝玉。
还是那样轻盈矫健地翔飞着,久久地,一动不动的安详神色,乖巧警觉的表情,抑郁黯然的眼神,纯纯净净,欲语还休。
事隔多年,它还是那只他们用心认得的精灵吗?
——哦,绿唇儿,是你吗?还记得那扇红云飞过的窗口吗?还记得那片槐树林和那片开满铜铃花的绿草地吗?那座养蜂人的白帐篷,那只牧羊犬,那些随风逝飞的风筝……
那时候,绿唇儿总是像老朋友一样的跟随着他们——年少的钟望尘,美丽的少女秋晓,它看他们时,表情里尽是凄迷若梦,乱了他们的眼睛也乱了他们的心。它常常会扑张着忧心似焚的翅膀,从他的手臂跳到她的手臂,那样来回跳跃着,很快乐——它好像完全读懂了他们的心。
事隔多年,它竟然还……活着?!
多少的爱情老去了,多少的岁月老去了,它竟然还有着这么美丽的容颜,这么纯真的、诚挚如初的眼睛,它竟然是记得的,它竟然不用想起——哦,绿唇儿,绿唇儿!
好像只是为了验证多年前的那个梦境,又好像只是为了重温旧梦,又……或者……只是……为了再续另一个好梦。
钟望尘看见那只绿唇儿,从古居的手中跳了出来,那样急切地,来不及在半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就直直地向他这边飞来,落在他的手上。它是那样快乐无比,前后左右地跳跃着,顾盼着,美丽的姿态,柔顺无比的羽毛,不住地婆娑着他的手指,后来它又跳到他的肩膀上,再次婆娑他的耳朵——就像那些有风的日子里,夹裹着爱情和比爱情还要娇艳的花雨,就像那些不断在耳边拂掠而过的悄声细语,凭直觉,竟然是像极了秋晓——哦,绿唇儿,你和秋晓,到底谁是谁?
终于,它向秋晓飞去。
秋晓张开双手迎接它,它就扑愣愣地飞落下来,在她的手指间舞蹈,轻轻巧巧,似是抚琴,似是拨弦,似是揉歌,和着彼此心头骤然奏鸣的音律,淡淡的伤和淡淡的悲情,知心,知性,知音,知情,知己——哦,绿唇儿,再次回来,为了谁?
是那样专注的神情,是那样迷离、倾心、幽怨的问候。
既是精灵,又怎会不知为了谁?
既是精灵,又怎会不知她究竟是谁?
既是精灵,又怎会不懂得她的心?
既是精灵,请一定告知,还要等待多久,才能让他们互相认出,既没有痛苦,也不会有……仇恨?
精灵原本是在天上飞的呀!
它在天上看着他们。天上人间本没有距离,有距离的只是爱人的眼睛和寻找爱人的心。
就像秋晓,就像古居,谁能比他们更辛苦?谁又能比他们爱得更凄迷?更专注?更忧怨?但他们偏偏是痛苦的。他们的眼睛里因为只有对方而再也看不到对方,他们的心里因为只有爱而从此找不到爱。这世界啊,多的是被辜负的心和没有结果的绝爱!
如果精灵回来,它一定是感知了什么。
但是那些爱,那些被爱困着的人,谁能在意这一份感知?谁能真正超越了传说里故事中那些神秘之外的精神力量,谁能真正挣脱掉不为人知的命运之手的操纵?
而现在的事实是,这只精灵,它回来了。
古居说:“这是我的鹦鹉。多年前我来大连寻找父亲,一下火车就赶上了一场大雨,我在站前的一个破亭子里避雨,一眼就看见了它,蜷缩在一个又小又旧的笼子里,像是被人弃置在这里的……”
钟望尘说:“……然后你就看见它也正在隔着笼子看着你,眼神无辜得像个孩子,浑身的羽毛都是湿的,鸟笼敞开着门,但外面是风大雨急,你不知道它究竟是无处可去还是……还是刻意……在这里……等着你……”
秋晓说:“……当你轻抚着它的羽毛,那么湿,一滴一滴地往下跌水,它瑟瑟发抖着,你心疼它就把它揣在怀里温暖它,它终于暖和了,羽毛蓬松,跃跃欲飞,你这才看清楚它原来是一只鹦鹉啊,它有润玉般的唇和迷一样的黑眼睛……”
“可是它不会说话。”古居说:“当它在我的怀里扑棱着翅膀,伸展抖动它的羽毛,当它一遍又一遍地用它的绿嘴唇轻啄我的胸口,我们互相温暖着却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钟望尘说:“……你一定找不到你要找的人了……”
古居说:“……因为我在第二天早上就丢失了它,因为我后来的找寻已不仅仅只是为了父亲……”
秋晓说:“……那段日子你好像只是为了这只鹦鹉而活着,你在这座城市的边缘徘徊着,在每一个角落找寻着,突然有一个晚上,你也梦见了……好大的……一片……红云啊……”
古居说:“……那是怎样壮观的景致啊,怎样的一片红云啊!汹汹的,像是从人的心里燃起,后来我发现原来红云升起的地方就是鹦鹉的归处……”
钟望尘说:“……先是一个梦,梦与现实之间隔着红玻璃,红云只是心里铺张着的一个愿望,梦醒之后就是那么美丽的一个早晨……”
秋晓说:“……一缕晨光,一只鹦鹉,一个故事结束了,另一个故事却刚刚开始……”
钟望尘说:“……我听见鹦鹉在喊秋晓,我听见秋晓在喊望尘……”
秋晓说:“……然后它就扑张着翅膀飞走了……”
古居说:“它变做精灵,我们谁也没有再见过它,但它一直是存在的。”
是的,它是一直存在的。
它也许已经存在了十年,百年,千年,万年……无论是否被人看见,它是一直存在的。
它是精灵呀!
而钟望尘却从这个精灵的眼睛里找到了一种熟稔,他从这种熟稔之中看到了秋晓,古居,还有哑叔。突然发现他们竟然有着相同的眼睛,他们是否也是精灵呢?为什么,他会从他们的眼神里读出红云飞渡时迷离在梦和现实之间的那种眩惑?好像他所面对的只是另外的情境里另外的心动,他甚至能从秋晓和古居相携而来的身影里看出他们的前生后世,那种不为人知隐约闪现在他心痛处的命中注定的生命痕迹,竟然使他怦然心动,竟然使他感动在这一对人儿相似到极致的那种无暇的和谐中去——这样的一对儿,生来就是要做夫妻的,如果天不凑美难做夫妻,那也必是一生一世的兄妹。这样的奇思怪想令钟望尘心灰意冷,细究起来竟是蚕食桑叶一般,渐渐咀嚼到一片虚空,咀嚼到最绝望的最疼痛的地方。
爱是什么?爱也许只是一种感知,长长久久的感知。
知道你在爱她,知道她在哪里,知道有一天心碎了但碎片跌落在哪里。
知道爱的每一种可能,知道每一种可能的缘由和结果,以及为了结果而时时感知着的那份心动。
有爱的人都是精灵啊!
第二十一章 水月梦花 2家园
古居在恍惚之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评委身份。
台上的复试一直在进行着,而他,竟然是忘情而专注——忘情为秋晓,专注为自己的心。惟有忘情才能专注啊,专注到“玩忽职守”。
错在精灵。
仅仅只是……错在精灵?!
掌声铺天盖地,是为一个名叫兰馨的女孩子。
初试时她的表现就不俗,只念了一手勃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弹了一首肖邦的钢琴曲,气质生就的高贵典雅,若演话剧她一定最适合古典主义流派的剧目,或者演绎莫里哀笔下的某个贵妇,在单纯抽象的布景前,穿着华丽繁琐的宫廷服装,每一个动作都局限在剧本和古典流派的严谨结构中,看起来极到位,但实际上没滋没味。古居曾在初试时看过她的表演,古居甚至无法想像,若演中国话剧,干脆就找不到适合她演的角色。这样的女孩,一定属于那种内心寂寞而外表有冷傲无比的人,她的钢琴弹得确实不错,她似乎更适合于做一个音乐家。复试这会儿她选了契珂夫笔下的《蠢货》中的寡妇,那个虚伪、做作、一方面把自己关在四堵墙里替亡夫守节,另一方面又时刻期待着有风雅的男人在她窗下唱小夜曲的假殉情者。她竟然博得满堂喝彩。
接下来的女孩很朴实,模样长得有点像《家》中的大嫂瑞钰,初试时她果真就念了一大段瑞钰的台词,这会儿复试她却选定了春妮,是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角色。解放军的一个连队进驻繁华的上海滩,在南京路上与暗藏的敌人做斗争,但是连长陈喜却被“冒险家乐园”的香风毒草、糖衣炮弹弄晕了头,冷落了来连队探亲的妻子春妮。春妮的这场戏没有大段的台词和内心独白,但是这个小女孩却把春妮给演活了。隔着长长的剧场甬道和一排排座椅看她给丈夫钉纽扣,不长不短的线,在针缝之间进出,进出的是长线,出来时线就短了些;那时的军服扣子都是四个眼,她的针线穿梭着就总是在四个眼之间,网眼上的线结一定也是四瓣的梅心一样的;然后就低了头用牙齿去咬断线头,只听细微的“噗”的一声就吐出了线头,露出雪白的碎玉似的牙齿一笑,羞红了脸。是一场真正的无实物表演,却有着极丰富的人物内心展示,眉宇间的贤淑与端庄让人感觉她一定会是个好妻子。她的名字就叫如霞。
兰馨和如霞。
竟让剧场后座的这三个人,古居,秋晓,钟望尘,都记住了她们的名字。
而钟望尘,其实早就认识兰馨了。他的父亲和她的父亲都是将军级的人物,酒桌上曾经玩过“指腹为婚”结为儿女亲家的把戏,只是后来钟望尘的父亲死了,兰馨的父亲却活得更好。钟望尘还记得小时候被父亲拉着手去兰馨家串门子的情景,一进门就听到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兰馨穿着白色的公主裙出来见他:“你会弹钢琴吗?”她问。“不会。”钟望尘老实回答:“我会吹笛子。”那个小公主瞪圆了她的大眼睛:“吹笛子?!”她说:“那是放牛娃才会玩的乐器!”钟望尘不说话了。父亲领他来本想让他与她吹弹合奏一曲的,钟望尘却再也没勇气拿出那把……笛。
可是刚才,就是兰馨在台子上扮演孀居怨妇。她提拽着黑色的金丝绒长裙,高声大骂上门讨债的“蠢货”,她要与他决斗,可是最终却爱上那个粗野之人,只因他揭穿了她,只因她在被揭穿之后渐渐显露出真实可爱的天性。契珂夫的戏总是有着最丰富的人物个性展示,大段的对白和潜台词,自然环境和人物心理的呼应,象征手段的广泛运用,并善于在生活常态之中挖掘戏剧性,用最平常的动作、行为举止表现复杂多变的深刻内涵。春暖花开的季节,下人们都去户外采摘鲜花和野果子去了,身着丧服的寡妇却把自己关在四堵墙里,听见门外有男士求见,她一方面拒绝见客,另一方面赶紧给脸上扑粉,终于赶在客人进来之前把自己装扮一新。这出《蠢货》是契珂夫的早期作品,三十年代传入中国,曾经在延安“鲁艺”的舞台上公演过,中国话剧的许多老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