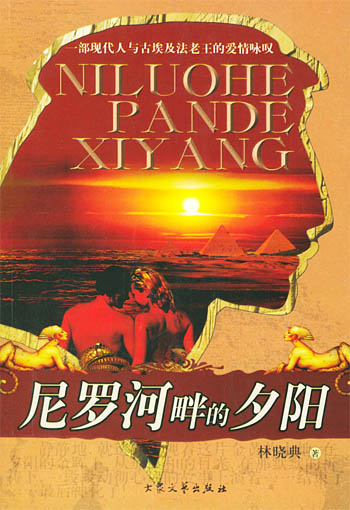鹤阳河畔-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妈妈说:“现在天冷了,好多人买羊毛线找不到会织毛线衣的人,这手艺你是懂的,何不以此来谋生?”
当学生的时候,符荣华家对面的一幢小楼房里,住着一个年轻的太太,这年轻太太的丈夫是个军人,长期驰骋于沙场,她个人在家没事干,常常坐在一张藤椅上,用几支修长的银箸自由自在地像变魔术般似的编织毛线衣。以此来打发时光。荣华十分欣赏这位年轻太太编织毛线衣时的那份闲适和安详。看她那灵活的手指,借助跳动的银箸,将毛线编织成各式各样图案的毛线衣来,她觉得这是一种艺术创作,看这种创作,是一种享受。
时间长了,符荣华也学会编织毛线衣了。不过,那时编织毛线衣,仅仅是为了猎奇,为了学时髦罢了。
自从不准符荣华用肩膀挑重挑来维持生计以后,荣华一直呆在家守穷,经她妈妈这一启发,为了生活,她就替人编织起毛线衣来。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猎奇”,现在却能用来作为混饭吃的手段!
一天早饭过后,符荣华正在门前洗涤小孩的尿布。一个理平头的塌鼻子的男子走了进来。手中拎着个鼓鼓的绿色旅行袋,见了荣华,他就自我介绍说:“我在镇委工作,听说你编织毛线衣手艺不错,我想请你织条毛线衣……”荣华听说是镇委的人,马上放下手中的活,热情地请客人到屋里坐,客人犹豫了一下,进了屋,打开旅行袋,拿出羊毛线说:“这是百分之百的纯羊毛,请你织的时候精心一些,价钱多少都无所谓”。
当荣华拿出软尺跟他量度臂长、身长及胸围的宽度时,这个平头塌鼻子目不转睛地在看着她,好像能从她的脸上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
量好身后,平头又说要先付工钱,当他听荣华说织好毛衣后才付工钱时,他就转头走了。
自从符荣华靠编织毛线衣谋生以来,这是第一个来她家的政府干部,这一来,荣华的心中又起了波浪。她想,他是干部,他不顾阶级界线,走进地主家,是否阶级斗争这支弦放松了?土改时说,地主安分守法,过了三年、五年,地主成份就可改变。土改至今已过三年多了,也许我家的成份就要改变了……她又想,这男子说话、动作都总不够自然,是否也借雇我编织毛衣之名,来此另有打算?醉翁之意不在酒……
符荣华夜夜伴着一盏微弱的煤油灯,坐在孩子的摇篮旁边,向睡眠讨借时光,编织毛衣挣钱养家。有时累了,就伏在摇篮边睡着。到摇篮里的孩子醒来呱呱哭时,她才醒来给孩子喂奶,孩子睡了,她又继续着她手中的编织生计。当年那个年轻太太玩弄手中的银箸那么悠然自得,她是在打发时光。现在她以此为生,全家的吃穿就靠这双手了,实在体味不到那份悠然。
穿呀,织呀,穿呀!灯里的油干了,雄鸡的鸣唱声响了,符荣华又得拖着疲倦的身躯到厨房去生火煮饭……
由于家务繁多,睡眠不够,心情不好,荣华渐渐地消瘦了。
那个自称是镇委干部的男子又来到荣华的家。这次,他一进门,荣华就叫二娘,抱着小孩呆在门边。那塌鼻子男子好像要对荣华说计么,但见一个老太婆抱个小孩坐在那里,又把话吞了下去。
荣华说:“羊毛衫已经织好,请穿起来看看是否合适,要是不不合穿,可以修改!”
第十五章(3) '本章字数:1473 最新更新时间:2011…09…25 09:41:52。0'
那平头男子马上脱下他穿的那条列宁装,将羊毛衫套上,左瞧瞧,右看看,衣袖的长短,衣领的大小,衣身的宽狭全都适合。他看了看荣华一下,咧开嘴巴,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笑一笑,又高兴地脱下羊毛衫,穿上列宁装,打开旅行袋拿出一包东西,顺手将羊毛衫装进袋去。
塌鼻子又从口袋里拿出两张伍元钱,并把那包东西送到荣华面前说:“这是工钱,这是奶粉,是我另外送你的。”
荣华说:“我做工仅收工钱,不收什么礼品,奶粉你带回去,我不能收,工钱是八元,这里找回你两元。”
当荣华将两元和那包奶粉交回那男子时,那男子又把钱和奶粉塞过来,就这样一推一送,一送一推,男汉的手接触到了荣华的手。他紧紧地将的她手抓住,向前跨一步,像是要动手动脚似的,但又碍于那个老太婆抱着孙子坐在那里。荣华早已警觉到这个男子的不正经。她马上将手收了回来,后退几步,严肃地说:“我们人穷志不穷。我丈夫是大学生,有知识,有文化,我们心里很充实。我们……”“好吧,好吧,别说那么多了。做了工收了钱可以了!”二娘怕荣华说话失了分寸,挫伤了这位干部的面子,就从中打岔着。
塌鼻子男汉还想再缠,但见对方不是那样的女人。态度严肃,说话又是那样的有板有眼,只得将那两元钱和那包奶粉塞回旅行袋中,悻悻地退了出去。
这位塌鼻子男汉,满以为自已是政府干部,越过阶级界线,潜进这少人搭理的冷清人家,投以诱饵,一定会钓到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然而,他扑空了。他想不到会遇到个泼辣的硬女子……十分懊恼,堂堂一个干部却被一个地主仔侮辱,实在是江河倒流了。但他又不敢把这事情张扬出去,只好把这事埋在心底。以便他日再作盘算。
纵横交错的阡陌,将稻田分割得像棋盘一般。这些稻田,一直向海边延伸。再过去就是浩瀚无边的大海。淡淡的远山,在稻田的西边尽头一动也不动。高山和大海润泽着这片肥沃的稻田,陶家庄和周围几个村庄的农民,世世代代就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地劳动着。
小暑已经过了,稻田里的秧苗绿茵茵的连成一片。从海上吹来的清风,掠过稻田,荡起了粼粼的绿色波浪……
在鹤阳山脚下的夹谷里有两块稻田还未犁耕,这两块待耕的瘠田,就是符荣华家的田地,农会已多次派人来催促备耕,不过,实在是没有办法,家里现在五口人,真正能劳动的仅是荣华一人,她家没有牛,她自己也不会犁田,雇人来犁也不行,谁人肯来帮地主家耕地犁田?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已拿锄头到田里去挖了。这么热的天气,要是她一个人拿锄头去挖这两块地,恐怕周围的稻田已经收割了,她家的田还未能插秧。这怎么办?
正在发愁的时候,陶家家族中一个按辈份排,荣华要称为她为婶婶的中年女人走了进来。她开门见山地对荣华说:“听说你家在鹤阳山脚下的那两块田地还没有犁过。我家也有一亩多地也没犁。你叔叔是会赶牛犁田的,不过,我家没牛,听说你娘家叔叔有头公牛闲在家,你能否将牛借来两天,头天你叔叔先犁你家那两块地,第二天才犁我家的。这样,我你两家都得方便……”
听了这位堂婶的话后,荣华觉得这样还是可以。马上赶回娘家去找叔叔借牛。这叔叔是个吝啬鬼。听侄女说要借牛,心中就不舒服。但要是不借,又怕村人议论。结果,牛还是借了,不过,他要荣华保证两条:一、驾牛犁田的必须是老手。二、两天过后马上还牛。荣华答应了两条要求以后,立即用肩膀杠着犁具,牵着那头膘肥体壮公牛的回到陶家庄。
这位心计狡诈的堂叔,下午他就杠着木犁,牵着水牛,一跛一拐地来对荣华说,他的脚板被玻璃片刺伤了,不能再犁了,将牛还回人家……荣华说:“我那块旱地已泡上水了。还牛时间还有一天,明早你跟我犁耙好后才还牛……”“不,我的脚刺伤了,很痛,不能犁了……”说完他就将牛拴在木桩上
转身就走了。
第十五章(4) '本章字数:1523 最新更新时间:2011…09…26 09:26:09。0'
荣华借来了牛,原说要犁耕两家田地。现在堂叔的田犁耙好了,而荣华的田却借故不犁。这实在太缺德了。不过,如此缺德的事,谁来判理?本来这堂叔当过保长是历史反革命,他们是同病相怜,应该互不嫌厌,互不欺压,但是,世间什么样的人都有,被虐待的仆人,有机会也要欺侮奴婢。娼妓也咒骂邻女不贞洁。荣华没有办法,只好流着眼泪,又扛着木犁、牵着牛,回娘家还牛去。回来后,她带着小弟天予荷着锄头,硬着头皮在自家的田地上,挥汗运锄。在烈日下,汗水和着泪水,淌滴在这块瘠瘠的土地上……。
挖地刚回来,荣华累得四肢酸软,水也不想喝,饭也不想吃,坐在墙根下的矮凳上,一句话也不想说。
这时,邻居大婶交来一封信。一看信封,就知道是天赐寄来的。荣华提起精神,高兴地拆信来看。
看到那工整稳健的笔迹,她就像是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夫君,脸上马上浮出了丝丝笑影。看到信中写到在学校里的学习生活情况时,她高兴得笑出声来。
抱着孙子在灶边煮饭的二娘、听到了荣华的笑声就说:“是天赐来信吗?说些什么了啊?”荣华没答话,继续看下去,渐渐地眼眶里含满着眼泪。
“……口袋里分文没有,坐在教室里聆听老教授讲课还可以,但是一走到街上,心里总是不舒服。百货商店玻璃框里的白色衬衫,新华书店书架上装订别致的文学名著,街头饮食摊上冒着香气的油炸面饼,好像它们都在合谋向我鄙笑。街道两旁铺店的门扉、窗口好像也在对我白眼。
“下课回宿舍来,动手洗泡在铁桶里已有两天时间的脏衬衣,揭开肥皂盒,盒里空空的,肥皂早已用完,我只好用水揉一下脏衣就拿去晾晒了。在晾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衬衫背上有一尺把长的口子……。
“前天,给一位曾是患难之交的朋友写了封信。在投邮之前,我站在邮局门前,搜遍全身的口袋,找不出八分钱来买邮票。在朝的贰臣,不知道眨居于儋州古屋里苏子的心绪,得势的清王不可能理解在伦敦蒙难的孙中山的宏愿;纨绔子弟,怎能理解一个穷学生连买邮票八分钱都没有的潦倒窘境?
“不过,我个人这些生活上的困难,跟你在家扶老携幼的那些艰难日子比较起来,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荣华,困难可以磨炼我们的意志,困难更会增强我们的信念。”
荣华看完了信,泪珠串串地从眼中涌了出来。她想,在家里,再贫穷再寒酸她都能咬紧牙根低头走过。一个农民穿破衣服劳动,穿补衣服上街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学校,在大学里,在那文雅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圣地,太寒酸了,人们是瞧不起的。怎能设想,一个大学生没有八分钱买邮票寄信呢?天啊,为什么我们这么苦?为什么我们这么穷?
织毛线衣得八元钱,昨天又得六元,共十四元,她再跟二娘要回要买菜的六元,一共整整二十元,第二天一早,她就到邮局去,将这二十元寄给远在省城读书的丈夫。
夜里,村里的狗吠得十分厉害。有时,荣华半夜醒来给孩子尿尿,除听夜狗狂吠外,好像门外、窗下有走动的脚步声。她心里十分害怕。男人不在家,家里除老的老,幼的幼以外,只有她一个少妇。要是有歹徒破门进来施暴,实在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天天吃晚饭时,荣华对二娘说,近来夜里狗吠得凶,有时似又听有人在门外走动……,二娘说:“不要怕,有贼也不会潜入我们家。谁不知道我们是寅吃卯粮,有什么给他偷?”“荣华听二娘这么说后,心中想,偷东西的贼不可怕,可怕的是偷人的贼。不过她没说出来。二娘又说:“恐怕是民兵巡逻的。”荣华说:“反正夜里听到狗吠,要注意听听……”
自从宗贤被枪毙以后,其妻凤姬就另嫁别人走了。家中只有宗贤的母亲钱氏一人。钱氏年青的时候,是个风流人物,嫁来陶家以后,还常约男人到鹤阳山上,到鹤阳河畔或到她家来幽会**。钱氏爱打扮,喜打牌。有时外出打牌输了,几天几夜不回家。生宗贤后,人们常在背后说这孩子像谁像谁,是她输钱了后,用她身上的那四两丑肉给人抵债。后来怀了宗贤……
第十五章(5) '本章字数:1581 最新更新时间:2011…09…27 09:44:46。0'
儿子死了,儿媳妇走了,钱氏一人又好吃懒做,家中存的一些值钱的东西,能够卖的都卖了,田地也都卖光了。到土地改革时,看在她孤老婆子一个的份上被评为贫农。
近一两个月来,这里悄悄地有人说着这样的话:说荣华家近来常有男人半夜光临。她家五、六个人,仅她一人干活,她家都未断过炊烟,可能是靠干那种事……,这话经钱氏加油添醋后,一直传到了镇里。镇里分管治安的就是那个曾经叫荣华编织羊毛衫的那个平头塌鼻子男子。他想,这假装正经的女人,原来是这样的年轻,白白嫩嫩的,生活那么困难,老公又不在身边,能忍得住?想到这里他兴奋地自言自语着:你不肯就我,以后你会来我面前跪着求我……那时候,吃白的吃赤的,那就由我了。
从那以后,这个管治安的平头塌鼻子男人,每天掌灯以后,就以治安巡逻为名,佩着短枪,到陶家庄去,在荣华家周围转转。要是真的发现有半夜君子潜进陶家,他就抓住把柄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平头夜夜扑了空。但又不甘心罢休。他想叫陶家庄一个可靠的人替他监视。想来想去,就想到了陶宗贤的母亲钱氏。
钱氏家庭成份是贫农,政治可靠。钱氏家跟荣华家毗邻,饭前、饭后、夜里可以窥探,十分方便。另一方面,她们两家是死对头,叫她当此差使,她一定乐意接受……再有,她儿子宗贤当过日本狗腿,又贩卖鸦片,被日本人打死。这一窝囊历史,土改时曾有人提过。不过,考虑到她是个孤寡妇人,又是贫农,人们也就不再管了。镇里交给她这一差使,是瞧得起她,她能不从命?
钱氏领命回来后,高兴得饭都不想吃了。她想,镇里把这件事交给她,说明他们对她的信任,说明她儿子的那段历史,他们真的既往不咎了……要是她在新屋抓到了奸,不但立了功,还可以发泄她多年积郁的冤恨,而且远在省城里读书的天赐,也可叫人勒令他回来跟他老婆一起背黑锅。
每夜,荣华都要二、三次的点起灯来给孩子尿尿,屋里每次灯亮,都牵动着屋外执行任务的钱氏的心。都给钱氏带来立功的希望。但是,无情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使她的希望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