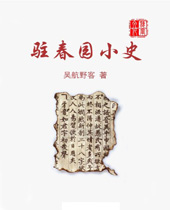爱的罗曼史-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一种既使在无助时也要把心捧出来,把话说清楚简白的诗人——从不因为无助而呻呤。在别人呻呤的地方,她哑然(因为用尽了力量),而这是真正的无助……
我们愈来愈靠近,甚至肌肤相亲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在这之前,我们俩全部都被交织着幸福憧憬和未来颤栗的泪水模糊了眼睛。我们像双眼被布蒙着的人一样摸索着前行,让各种身边事情牵着走。我们正在享受恋爱之初懵懵懂懂的激情幻想。我们每次见面都含含糊糊地相处——我指的是在人多的公众场合,在课堂,学校内。装着若无其事,甚至眼皮都不敢朝对方多抬一下,而每次一起上完课,一起集体出游之后,都弄一身紧张、热乎乎的热汗。在和学生们聚坐在一起时,我有时会大声哗笑,忽然间人群的头顶上有时掠过一道女性近乎于哀鸣的目光——我会突然笑声顿失,心里感到无端的惆怅。那种感觉在随时告诉我她在哪里,她此刻的位置,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第六感官是伴随着她的,仿佛生长在她那里。那个时刻心系着她的第六感日夜煎熬着我,就好像一名被关进了狭小囚室的人,被迫每一夜亮着灯睡觉。这种初恋的疾痛和痴情导致的身体感应过份的灵敏。在人的一生中持续的时间和阶段并不太长久,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耗费人体内的精力。它可以在极短的几周几天里,使坠落情网者失去理智、憔悴不已——它仿佛是在用暗哑无声的苦楚酿制最终的爱的醇美甜蜜。它是很厚实,密不透风的那一圈酒窖酒瓮口子上的封泥。隔着大肚的瓮坛,我能感觉到内部酿制中的酒汁的微妙变化,它的温度正和种种看不见的酵母相链接。一种冉冉上升的香气,正在更迅速地日夜到达我欣喜若狂的唇际……
第三部分两把吉他(2)
她在走廊,和她在一起的女伴是谁。现在她来了。她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一言不发。她的叹气鼻息是火热的。她用左手撑着脑袋,右手在本子上胡乱地写着、画着什么。她在我背后肩膀上方,趴在那些看热闹的同学身后(我正在弹奏吉他)。她像孩子般顽皮灿烂地笑,试图博取我的注意。我连头也没抬一抬,我那被爱情烧炽着的颈脖仿佛化作了无生命的石膏。我暗自羞愧,而她一声不响背转过身去(我能看见)生气了,她生了气,至少要在半堂课左右长的时间里不理睬,而且是决意不会往我这边看一眼。正如我有时候看见同学中也有成绩优秀的学员,尤其男生,课间休息时主动坐到她位置上和她交谈(他们大概在相互赞许对方的诗)时,我心里有一种类似妒嫉的情绪默默噬咬着……当我走过空无一人的楼梯,我闻到了她身体的体香,一种汗浸润了发丝的女孩子的健壮顽皮。那香气跟世上别的东西都不一样,那香气年轻而幽暗,宛如黑暗中振翅高飞的云雀。它会在我的心上啼啭逗留告诉我一个个并不确切的有关爱情的消息……自从上一次在火车巷里甜蜜地邂逅(并没有身体接触,只是俩人第一次私底下安静相处。恋爱的钟表上开始有了第一下秒针颤栗的向前移动……)我俩仿佛都已确信,向对方发出的讯息已被证明(从眼睛里)是明确有效的。眼前的天地已豁然开朗,只是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往前跨第一步(即使手拉着手)。我注意到,后来,她身上的香气更壮严专注起来,更令我激动了。在我眼里,她像是一下子又大了几岁。变得像个懂事的大人了(她会用类似妈妈或姐姐一样的眼光耽忧地从远处看着我),但是,在人多的场合,我一时无法分开心,无法面对,朝她爱理不理时,她又突然憔悴得像个泄了气的卑怯的小学生。因此,她在两节课之间有很多种样子和表情。她又是那种死不愿说,死不开口的倔强脾性……直到来年的一月,我们有走到一起的机会。在这之前俩人真是吃足了互相思念、猜疑的苦头。
那年县城的东门大街正在扩建。老护城河段上的桥梁拆除后,在新桥落成前夕临时搭建了一座木制的简易桥。桥的东西两岸,到处都是脚手林立、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班上有一名学生,他的妹妹结婚,家里置办喜酒。他就热情相邀全体师生去他家。那是一个星期一的傍晚。1990年1月的隆冬季节。风刮得乡野耕地一片灰白,我们把原定那一晚的课程挪到了下午。两节课罢正好是吃晚饭时间,大家都热情高涨,一付窃窃私语惟恐天下不乱的表情。同学的家在距城十五里路的乡下。五点半,那名乡下同学带头,二十多辆脚踏车开始往预定的目标开拨。
这之前,整个写作班期间,我们也曾有过几次集体出游,大家在一起玩得热闹,但这次的意义不同,一是去这么远的乡下,大家都有点好奇;二是我们的学期很快就要毕业了,这可以说是毕业之前最后的一次集体联欢。二十多辆脚踏车的队列足足拉长了有一里路的距离。我落在最后面。我在锁上教室门的最后一刻突然有了个激动人心的主意。“我的车胎坏了……”我说:“我骑谁的车子,带一个人……”
两个男的骑一辆车,毕竟太可笑。剩下的肯定是女生。而那天参加的女生,总共只有四名,推了各自的车乱哄哄聚在校门口的学生们一齐嚷嚷:“老师带英子——”大家全心照不宣,我所谓“带一个人”指的是谁。
我又看到那辆轻巧的紫色女脚踏车,看见那辆车,我就像看见了久违的亲人,眼睛都不舍得从车身车把手上移开。冯建英正站在车龙头左边,微低着头,显得顺从而大方。没有特别逗人注意的异样表情。“走吧许老师。”
她答应了一句,声音轻得只有两三人听得见。
先头部队往大街上一哄而散。不知不觉中,她那辆香气的脚踏车已经到了我手上。我往前推了几步(她跟在后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又停下车,低头用手故意摸摸轮胎“气足不足?”
“足的。”她说。
我在她温柔的嗓音中上了车,她坐上来。我感到了她身子的小巧和轻盈。我又故意晃悠龙头:“哎哟,第一次骑,龙头真活。”我笑了,她也笑了。我感到一件重大的事情正在降临。“路总蛮远的,半路上摔下来可别叫我陪……”
换了别的女孩,也许会说:“你敢!”“那不行,找你算帐!”在冯建英这儿,我只听见同样温柔的轻轻一句:“不会的”。
仿佛在说给路上的晚风听——而隆冬旷野上的寒风也变成了暖洋洋的春风。
我至所以提到或记得东门那座简易临时的木桥,是因为俩人上桥时,她早早就从车后座那边溜下身来,同时一只手还推着脚踏车,一路小跑,跟我上了车。我记得她在身后“哎哟哎哟”的欢情。她的情绪高涨。当我们推车上桥时一轮残月挂上湛蓝的夜空。天很快就要暗下来。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年冬天的那个晚上,那个暮晚,那一幕星月高悬的深寒夜空。我的身体内升腾起无限的青春热情。我们过桥时仿佛在展翅飞翔。那样一座简陋杂乱的窄木桥,想不到却容纳下了我一生最初的幸福。轮胎和脚步声在木头板上“隆隆”作响。咯隆咯隆,整个底下的河床都感到了震动。这人世间刹那之际的幸福容不得人们多加逗留、思考。转眼之间,我们已经来到河的东岸。她已无声而熨贴地坐在我的身后。“坐好啦”,“嗯!”。桥的下边是一段长长的陡坡,两旁堆满建筑用的木料,砂石,水泥预制件。橡胶的车轮胎很容易打滑。当我环视左右,我发现过桥时落在后面的学生们全都远远地骑到了前面,仿佛在进行一场全体脚踏车越野赛似的,连刚才陪着冯建英的一名女生也快快地往前追赶——仿佛急于要把尽可能多的大路和旷野留给我和她……
旷野无声。
第三部分两把吉他(3)
高悬的月亮在我俩头顶“沙沙”作响,远处传来村庄上的狗吠声。农耕小路上的拖拉机由近至远的声音以及在我们身后,新建城区一下又一下的打桩机声。广阔的田野几乎尚没露出冬麦的嫩青色。土地还是褐黄色的、黝黑的,是一年中最深沉苍凉的色泽。枯瑟杂树、苇草的小河边,尚能窥见一蓬蓬横阵,不久前积融着的白雪。夜空充满了针砭人肌肤的霜寒的白光……
“后头冷吗?”我问她。
“不冷。”
“手好,好抱着我的……”
顿了顿,我见她没反应,又说:
“手好抱着我的……“
“不要……”
“好热点,还有一长段路呢。”
“我屁股也坐疼了。”
“再坚持坚持……”
我右手脱掉车把手,默默伸到后面,搜索她的手。我把她的手拉近过来,搁在我腰里面。她的那双小手可爱、委屈、畏葸不前。手上弄出些胆怯的响声。乡间土路“嚓嚓”地从车轮胎下飞过。我俩都戴着手套。她忽然一把扯掉我右手上那只纱手套(动作恼怒),在我的右手食指根和中指根上亲了一下,又亲一口手心。
……
她轻轻一口,含住我的心。柔嫩发烫的嘴唇像铬铁般印上我记忆的肌肤。
忽然,我的手被移近了她的脸庞,摸到两行无声的热泪……
那一晚的记忆,出现大段的空白和寂静,突然有凛洌的旷野黑压压一片,朝头顶压下,旷野上生长着大片忍耐着缄默无声的庄稼。天边的村舍轮廓已经有星星点点的灯光闪烁。一条宽宽的河流出现在我眼前,远看,是天上的星空带,辽远的银河系;近看,是一条运河支流,叫“白屈港”。我们的双手脸颊都被彼此的泪水弄湿了。我不知道其余学生去了哪里。我好一阵子思索,才弄明白俩人何以置身于这片旷野。一条阔大的土路静静,泛着冬夜的月色。大路前方空无一人。除了她,大路,我自己之外,其余的一切仿佛都已远离,都恍若隔世……课堂、单位、家、童年。一切都在旷野黑黝黝的耕地中深埋着,千年沉睡着的样子。在人世上我仿佛从未醒来过。是一缕女性的发丝将我轻轻拂醒。我感到她呼吸的气息在我脸庞的周围留下莹洁澄澈的印痕。我看到我的一生在旷野上隐隐现身,是凝然不动的风暴中的一个漩流形状。它已经过去了,结束了,被凝固在遥远的黑夜深处,凝固在这块离长江不远的乡间土路上……一个人在月光下喊我们,站在桥上,推一辆脚踏车,他的脸完全被一双惊诧莫名的眼睛所占据。“许老师,前头快到了……”我们看见一座黑黢黢的青山。山脚下,有几座散乱的村落。“快点骑,在等我们——”身后冯建英用手捅我,使我吃了一惊。怎么?村前,有露天的婚礼场面,散乱的鞭炮屑,临时搭建的塑料棚棚,录音机响着音量最高的流行歌曲。灯光一亮,我们到了。满屋子学生的眼睛都静静地看我。那名乡下学生年老的家长出面接待,大家陆续就座。我昏昏沉沉。注意到冯建英又坐到几位女同学席上,这一带村子的供电似乎不足,灯光昏暗,所有的菜肴碗盏都冷冰冷……
同学们早就到了。在桥上,在大路口,每一次都是乡下的学生一个人来给我和冯建英引路,生怕我们在旷野上迷了路。可是,在到达此地的一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曾停下车来,相拥相依在一起吗?
空气里是瓮装黄酒的滞重。忽然间我被一碗酒的滋味冲醒过来,恢复了平时的知觉。我闻见厨房间的油烟味,仿佛空气中猛地爆开了一整个厨房间的菜肴案板,其余人咪咪笑着,我们正在伸筷子品尝一盘红烧鱼块。各人开始敬酒。称兄道弟,开各种玩笑。我的感觉是,在和你心爱的女人初吻之后吃一桌丰盛的酒宴,真是可怕!
那亲吻仍逗留在我脑际,留下异常悲愤、快乐、执拗的印迹。留下一个阔大的完全新的世界。那世界之门的开启,沉重的门轴“吱咯”转动的声音,沿着我背后的脊柱骨开始上升,一种相爱过后孤零零的感觉朝身体的左右弥漫。在爱情中,人生原有一种孤单留下来,供恋爱双方独自品尝,而无以言表,无法排遣世界的……
那晚的其余节目包括歌唱表演、诗朗诵。引得许多前来参加婚礼的村民们围观。学生们全都吆喝我这个老师务必露一露脸。我微笑着表示可以唱一曲。
“我把这首歌献给——”我停下来,声音有些不自然,有些颤抖,“献给今晚的新郎和新娘,献给大家……”
我大声唱了起来,我感到我很努力,结果声音仍旧很弱小。你一定不会相信——我唱的那首歌曲。那是一首生僻的爱尔兰民歌:《伦敦德里小调》——那就仿佛是进一步的亲吻和搂抱,进一步的公开表白,相互怜惜。我以前在课堂上唱过,我唱时看到大多数学生的眼睛都泪光闪烁。所有能够唱几段,会唱的人都跟着我唱起来(我本该选择一首更通俗的中国歌曲)。不一会儿,人群中有人递给我一把吉他,在这样的乡野村落里居然也有玩吉他的人家!我就着乐器,又唱一遍,把那间屋子变得像一群疯子在聚会。唱完,才发觉吉他至少有两根弦的音,完全走了调。
哦但愿我是骄柔的苹果花
从弯曲的树枝上面落下
飘落在你那温柔的怀抱
把它当作我的家……
——
第三部分两把吉他(4)
那一夜我们是怎样回县城里,我弄不清楚。这里面可以有很多种表述。比方说:那晚上我们是走着回去的,走路回去,推一辆脚踏车,有时也在路上骑行一段。有段时间,她还要用她那辆稚嫩的小脚踏车带我,让我坐在她后面,摇摇晃晃几下。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推着车走路。另一方面,我像是从未从那样一长段旷野的夜路上回来过。我的心被留在那里,在像那样年轻寒冷的夜色中,那样热烈的交谈里。那片临江的乡村旷野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这一生。我后来的一切的所作所为都跟这片冬夜的乡间土路相关,我们俩就像是手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