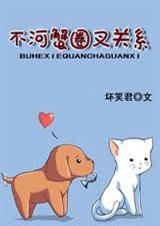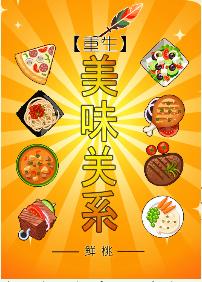关系-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真的说不出这里诱惑着我的是什么,有一种诱发初恋的感觉,到高潮的时候,和第一次做爱也有点儿相似。非常迷醉!心中有些憧憬什么,期待什么,又想进入什么。什么都有一点。有一种精神欲望传遍全身,最后把生理欲望也调动起来了。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叶挺认真地说:“至少我再到风雅颂去,我会要求自己在原来的品位上,再加上一点,透明和优雅。他必须是有激情的,同时又是很高贵的,是那种很纯净的高贵。我也说不好。应该像《青春之歌》里的卢大川吧,同时把自己变成林道静,是那个从香河去北京的火车上,穿白衣白裙的林道静。当然,也可以是一个余永泽,不过只是偶尔为之。”
区惠琴的私生活相对保守一点,有了固定男友麦地,又在杜林这位老夫子麾下,她生活得比较理性。对苏叶伊然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她又十分感兴趣。她对此有一种学究的意味,她总想寻找追问现代女性心底的东西。
在白云山上唱歌的人,大部分是女性,40岁以上的又占了大多数,她们是最积极最忘情的一群。生活对于她们而言,似乎就只剩下唱歌,唱她们青少年时代的歌。李可凡说得很对,她们都怀着各自的目的来寻找一种东西。唱歌只是一个方式,不是目的,而这个方式却又被幻变为一个目的。李可凡其实是所有来白云山唱歌的人中,最理性同时也最孤独的人。她的孤独是因为她明白自己心中的欠缺,知道自己到白云山上寻找什么。
“当生活的全部内容或主要内容,就只剩下唱歌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幸呢还是不幸?”区惠琴总是有问题,而且她的问题通常都很犀利,这点很像她的老师杜林。“她们都还只是四五十岁。”
“苏叶,到了这个年龄,你会这样吗?”区惠琴直指思想最解放最无忌讳的苏叶。苏叶甚至可以向女友描状她与男友一夜情的每一个细节而不脸红。她认为这是人的精神与肉体行为的盛宴,有什么不可以细细描状的呢?人类是需要这方面的交流的。
“我真不知道。如果会,应该有一位男友陪着,像高塬那样的男友。我会追随他,为他做任何事,不问历史,不问未来,只问现在。”
听了苏叶这些话,李可凡有一种剜割血肉的疼痛。
苏叶的人生是明确的,她的爱恨是明确的,她的欲望也是具体的。李可凡自叹不如。也许是年长10岁的缘故,也许是因为还有一个并未了断的刘兴桐的缘故。她想做一个坏女人,但还是不能彻底地坏起来。她想起和胡杨在风雅颂的那个最后的夜晚。这是她走得最远的一步。在高塬和胡杨之间,她还是经受不了胡杨的诱惑。他太强大,强大到你无法拒绝。他简直就是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佐罗,在风驰电掣之间,他就已经把你裹挟到了天堂之门。你还来不及挣扎,就已经成了他的俘虏。
他的强大是以并不强大为诱饵的。他在无限的顺从中一步步拉紧了他早已撒出的罗网,那罗网轻软同时柔韧,无声无形无迹。他以千年不死的韧劲令你自投罗网。
她们几个说到半山亭去,却因为谈论问题一直站在人群外面。这时,合唱变成了小提琴独奏,白夫人与几位女士为独奏曲啍着和声。李可凡听出这是一首俄罗斯歌曲,是俄罗斯彼得堡“强力集团”的作曲家鲍罗廷的作品《在中亚细亚的草原上》。
她们挤进人群,李可凡毫不犹豫地挤到最前列,她非常真切地看到了高塬。她离高塬就只有两三米的距离,高塬也看到了她,她看到高塬的眼睛投过来山羊似的温情的一瞥。这一瞥令李可凡羞愧难当,惊心动魄。
高塬面色苍白。他坐在椅子上拉琴,他已经拉了六七个小时,他完全沉浸在极度亢奋之中。在小提琴高音区弱奏的背景上,白夫人她们哼唱出一段浓郁的俄罗斯旋律,它描写一支骆驼商旅正迈着沉重的步子,由远而近地行进在亚细亚的草原上。高塬灵巧手指的跳动,形象地拉出骆驼和马的蹄声,最后,提琴的音量越来越弱,这支骆驼商旅已消失在无尽的远方,辽阔的草原又陷入一片寂静。随着这首作于1880年的歌曲的终结,人们见到这样的情景:
高塬脑袋一歪,他托着提琴的手慢慢低垂,提琴“咣”的一声摔在地上,高塬瘦弱的身体也随着提琴落地轰然倒下。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人们还没有从《在中亚细亚的草原上》的优美旋律中回过神来,就目睹了这惊人的一幕。有过很寂静的一刻,这一刻是提琴终了,余音却还在夕阳下的林中空地飘飏之时。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这一刻,等待着生命终结时无穷的寂静。
高塬死于自己创造的寂静之中。也许这正是他梦寐已求的人生时刻。他和1880年鲍罗廷旋律中孤寂的驼队一起,走向茫茫草原,沉没在寂静的草原深处。
几位退休的医生,首先冲到高塬身边,有一位年纪很老的女大夫,抱起高塬的头,将他枕在自己的腿上,像母亲抱着婴儿一样。她自己不堪重负,一屁股坐在冬天的泥地上。她翻开高塬依然睁着的眼睛的眼睑。瞳孔放大,高塬死了。
李可凡难忘高塬的最后一瞥,就是在那一瞥之后,琴声渐弱渐远,高塬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步。
除了李可凡她们几个,没有人知道高塬的名字。白云山唱歌有一个约定,谁都不过问别人的名字、职业以及现状。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问它干嘛。来唱歌本来是为了开心,问起来就不开心了。何以解忧,唯有唱歌。
人们喜欢同时需要这个拉琴的人。喜欢就是他的名字。人们把喜欢藏在心里。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没有再提起他,这个在30岁上和他的提琴一起夭折的年轻人。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李可凡甚至没能挤进人群,去与高塬告别。他被蒙上白布,绑在担架上,4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抬着担架,把高塬从林中空地抬出,送上停在路边的救护车。人群自觉地分成两排,目送着这个刚才还在以无穷的生命力量拉琴的人。高塬就这样走了。
刚才高塬拉琴的地方上空,那一片黄栌树枝上孤零零的红叶,终于飘落下来,和地面上无数早已飘落的红叶,静静地躺在一起。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李可凡怎么也没有想到,高塬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人间。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林中空地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夕阳收起了它最后的光芒,暮色包围了山林土地。
一切依旧。尾声
一切还回到它原来的轨道·绝望的勇气·扑朔迷离·手稿也许将永远沉睡·难以名状的迷惘和凄苦·风雅颂最后的夜晚·苦艾的滋味·我们来唱歌吧
尾声这部小说,如果依照它在生活中的情节,它本应该无穷无尽地发展下去,它没有结束的理由。好人还没有完美的句号,坏人也不一定会有恶报的时候,不好不坏的人也就不存在什么极端的报应。人本来就没有绝对好坏之分,只看我们如何去评判了。
但世界上任何事情,总有个告一段落的时候。
高塬的死,使李可凡顿感无法结束的生活,暂时也应该结束了。也许一切都应该重来,也许一切还回到它原来的轨道。人,在还没有走到生命终极的时候,实在是无法知道最初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李可凡曾经被高塬吸引,想走近高塬。在还没有走近他时,却又在另一个地方,走进了胡杨。是胡杨给了她坚决走进的力量。可是,她刚刚走进去时,胡杨却又独自走了。他还会回来吗?胡杨还没有回来,高塬却真真实实地走了,他死了。他死得那样平常,又那样壮烈,让每一个活着的人惭愧,又同时庆幸,庆幸避免高塬那样的命运。
回家后第二天,李可凡正式提出和刘兴桐离婚。尽管再有一天,女儿就要出国
留学了。但在李可凡看来,离婚是一个不容改变的事实,不管是谁,包括女儿李小凡,都必须正视这个事实。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不能无视降临于命运的每一次厄运。女儿也不例外。她毕竟就要成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她要负责任地面对一切,包括面对她的父亲、母亲将要发生的一切。
女儿默认了李可凡的逻辑,刘兴桐无奈地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他最后小声地问:“能把手稿还给我吗?”
“那不是你的手稿,所以不能。”李可凡斩钉截铁的回答,给刘兴桐以一种绝望的勇气,他终于知道应该怎样去保留一个男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尊严。当他放弃了乞求的时候,他的选择就有了方向。
老枪终于给许楠生来了电话,让大浪鸟陪着去见她。她是在中国大酒店最豪华的咖啡厅接见许楠生的。就老枪和他两人。
老枪在注视许楠生时,又再一次想起那个新兵连的小兵。她用眼睛在许楠生身上,重温了20多年前,当她还是一个18岁的女卫生兵时,给一个死去的同龄小兵清洗身体时的感觉。
老枪递给许楠生一张支票,支票上金额一栏,赫然写着人民币贰拾伍万元。
“我已经为你办妥了你想办的事,一半一半。你拿着它回东北去,再也不要回来。记住,永远不要回来!好吧,你可以走了。”老枪说着,她戴着宽大墨镜的眼睛,似乎闪动了一下。
两天以后的一个午夜,在火车站的公共场厕所,许楠生倒毙在最里面的一个卫生间里。经警方披露,他是被注射了过量的毒品致死。暂时定为他杀。因为正常人是不会给自己注射如此过量的毒品的。他的口袋里,有一张25万元的存折,存折是以死者姓名在两天前以现金存入的。故排除了谋财害命的可能,凶手并不为钱财,也不知道死者身上藏有巨款。这个案子更显得扑朔迷离。
许楠生因属于盲流,他的死亡也没有上报纸的理由,故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死讯。
据警方的现场调查,有目击者描述,死者这两天曾与一操海南话口音的中年人在这一带出没。事发当天,他们还一起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大排档吃晚饭。
麦地自从那天和许楠生通电话,约在天河城见面未果之后,一直没法与他联系上。他相信许楠生有一天会和他联系。许楠生还有一个手提包放在他这儿。那天他把手提包带往广州,放在区惠琴处,学校放假了,区惠琴又把手提包放到杜林那儿。至今没有人打开过那个手提包。手提包里有许楠生父亲许达文1972年的下放日记,里面记载着关于《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手稿的事情。
这个手提包至今仍放在杜林的储藏间,手提包覆盖着厚厚的灰尘。它也许将永远地沉睡在那里。
刘兴桐遭遇火车
车祸去世后,正中大学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学界纷纷撰文,悼念这位在新时期填补了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空白,卓有建树的学术巨匠。他的葬礼电视台还做了专题报道。只是,在追悼会和葬礼现场,没有出现刘兴桐的夫人李可凡和刘兴桐的任何亲属。李可凡已在刘兴桐车祸之前与他协议离婚,她不愿意参加追悼会和葬礼。
那天天气很冷,苏叶在追悼会现场,见到包着黑色头巾的洪笑。洪笑站在一个角落,追悼会还没有结束,她就走了。
一个星期之后,刘兴桐的老父亲刘伯带着一个农村妇女,到正中大学来,带走了刘兴桐的骨灰盒和他的一些遗物。这个中年农村妇女,是刘兴桐已经离婚多年却还在刘家尽孝的结发妻子。
刘伯在刘兴桐的灵堂前老泪横流。灵堂上刘兴桐颇具学者风度的遗像两边是一副挽联:“一代学术巨匠;两袖清风学人”。
在新校长未任命前,丁新仪暂时代理校长。他特意为刘兴桐办了一个“刘兴桐学术纪念室”,设在
图书馆。待新馆落成之后,再行迁往。纪念室内陈列着刘兴桐的所有著作、手稿和各种报告、讲稿等等,供广大师生参观学习,每个系至少都要组织参观一次。
杜林例行公事地去了一回,他在陈列标志着刘兴桐学术成就的巨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的玻璃柜前,久久地凝视着这本书,凝视着封面上“刘兴桐著”几个大字。他的心中,弥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迷惘和凄苦。他脑海里翻动着岁月的书页,一页一页迅速掀过,像拉洋片似的,嘎然而止,停留在1972年12月31日这一天。这一天的黑暗燃烧了光明,也孳生了罪恶。
杜林悲愤得难以自持。他迅速走出纪念室,撞上了正要进门的金毛骆见秋。
骆见秋诧异杜林为何如此失魂落魄。杜林回头一笑,他的表情很古怪。杜林的脑海里叠印着《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和铁轨上刘兴桐血肉横飞的惨象。
苏叶、伊然、冯雅和区惠琴相约来到风雅颂。她们早就约了李可凡,但李可凡迟迟未到。
苏叶明天将去西班牙留学。
风雅颂的每一个夜晚,都上演着同样的戏剧,不同的只是演员。
今夜她们没有去内场。
已经深冬,圣诞节很快就到了。外场太冷,客人很少。苏叶记起那次在这里给胡杨打电话,而胡杨就在不远处静观她们,任凭手机在桌子上闪着蓝灯打转。她下意识地往那棵棕榈树下的酒台望去,此刻那儿也有一个男人,背对着她们,孤独地坐在那里。但不是胡杨。苏叶翻出胡杨的手机号码,给胡杨打电话,不在服务区。
李可凡答应来的,但一直没来。
她们谁都没有心情去内场,大家默默地喝酒。酒是那种很苦很烈的丹麦伏特加,没有加苏打水,也没有加冰,喝起来有一种苦艾的滋味。
苏叶感到有些惆怅与迷茫。
伊然把手轻按在她的大腿根上,苏叶有一种很异样的冲动的感觉。她抓住伊然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揉搓着它说:“很冷,是吗?”透过幽暗的灯光,苏叶闪亮的眼睛看着她。伊然哭了,哭得很伤心。
“去西班牙,什么时候回来?”
苏叶黯然:“不知道。”
冯雅见状说:“我们来唱歌吧。好吗?”
区惠琴说:“唱老歌吧!可惜不会唱那首《在中亚细亚的草原上》。”
“那就唱《三套车》。”苏叶笑着说。
初稿「后记」
后记一本书出版了,它就掉进了时间的河流里,任由时间去处置。时间就成了它最好的朋友。有些书,迅速地沉到时间的河底;有些书,它与时间之河一起前进,令人欣慰。
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