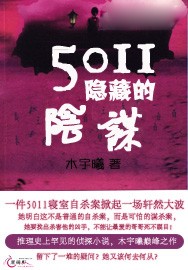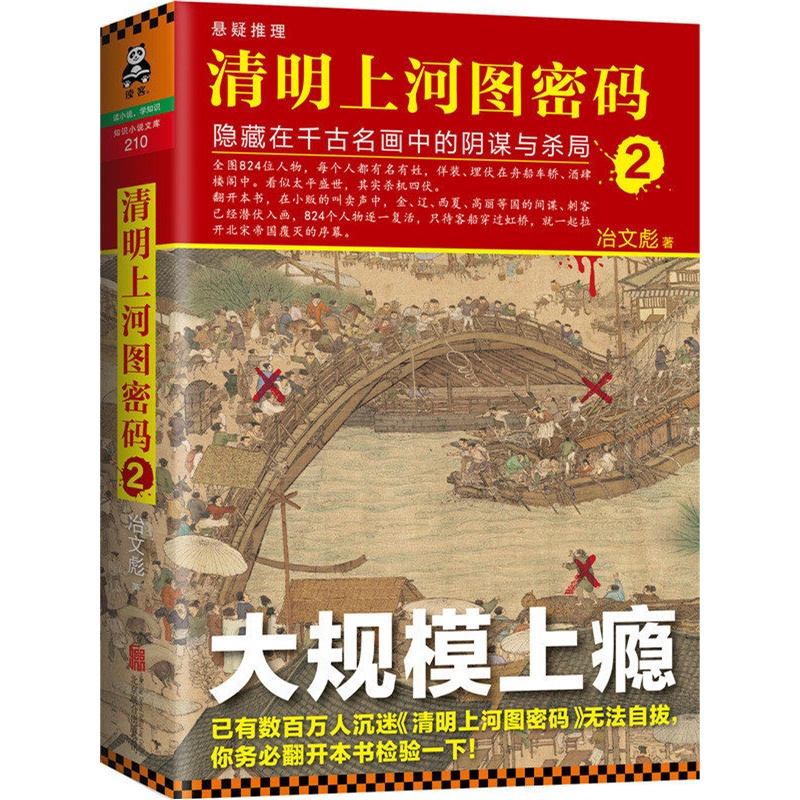母爱的阴影 作者:无敌-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更新时间:2005…9…4 10:20:00 本章字数:12368)
母爱的阴影
作者 常无敌
(五月精华版)
人之子宣言
我,向世上为母亲和将为母亲的人宣告:
你应当是人之母,而不仅是生灵之母。
你应当爱人之子,而不仅是爱己之子。
你应当给人子以人性,只要你的母爱有人性。
否则,你将不为人母。
而且,你将不得人子。
——人之子
引子
非洲,庞大的角马群在荒原上游弋。
一只小角马蹒跚地跑来跑去,它不幸和它的母亲走失了,可每当它靠近一只母角马时,都遭到粗暴的拒绝,因为那不是它的母亲;母角马凭借气味识别无情地将它踢开。幸好它的生母及时赶来,可怜的小角马才有了归宿。另一只失母的小角马就没有那么幸运,在屡遭拒绝体力耗尽后绝望地躺在地上,等待死亡的降临,而它身边的角马群对此无动于衷。
这是电视里播放的野生动物的生活场景,它似乎告诉我们,动物的母爱是自私的,排它的;这是自然法则。
其实并不尽然。
人工饲养的动物自不必说,因为已有许多“狗奶妈与虎宝宝”之类的报道,这或多或少有人为的干涉在里面;野生动物也有不少的例外:狮群中的幼狮就由成年母狮共同照顾,印度“狼孩”的故事表明哺乳期的母狼能接受人类的婴儿。以狼机敏的视觉和嗅觉当然不会人狼不分;那么,母狼能抚养异类为“养子”,这种“母爱无类”是自然法则的背反,还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我们人类母爱的法则是什么?是高于野生动物,还是如同角马,不如母狼?
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拷问人类的母爱。“母爱”——这个包含人性与兽性的词让我心向神往,又使我备受伤害。
第一章 一个人的旅程
一. 妈妈
爸爸说:“这是妈妈,叫啊!”
那是一九五三年的秋天,九岁的我一个人从南京坐火车到北京,由爸爸接到一个陌生的家,带到一个陌生的女人面前;那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正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
我从未叫过妈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单词。我努力想张嘴,但叫不出来。
我从小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奶奶告诉过我,在北京有我的父母,但我不太认识他们。爸爸回过南京几次,很快就走了;而妈妈却一点印象也没有。
“叫啊!”爸爸催促着。
“妈——”我终于叫了一声,妈妈答应着,笑了。
“叫婆婆(外婆)!”爸爸说。
我又叫了外婆,那是一个瘦瘦的女人,模样有些厉害。
两岁多的妹妹跑了过来,爸爸对她说:
“叫哥哥!”
“叫什么哥哥,叫无敌!” 外婆大声说。
妹妹有点糊涂了,外婆又重复了一遍:
“叫无敌!”——无敌是我的名字。
爸爸妈妈没有再说话。
没有当成哥哥,我当时并不在意。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另外一些事。
就是那“到家”的第一天,外婆在尿盆小解,还没有站起来就叫我端走,我走过去弯下腰伸手拿尿盆,大概是不习惯那种气味,我扬了扬头,外婆大叫:
“看!看什么看!你这个坏坯子!” 把我吓了一跳。
随后大人们就争执了起来。我听见有说我坏的,有说我还不懂事不必大惊小怪的。我听不懂他们的话,端了尿盆默默地走出去倒掉。对我来说,他们都是陌生人。
晚上,我睡在墙角的一个小床上。夜里,我被尿憋醒。睁开眼睛,四面是一片黑暗,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心里十分恐惧;我不敢动,不敢喊,不敢哭;我拼命想憋住尿,但最后还是尿了一床。
早上,外婆催我起床,见我不动,过来掀开了被子,然后惊叫:
“哎呀呀,这么大了还尿床!真没出息哟!”
然后就絮叨给她添了多少麻烦之类,我没有辩解,满面羞愧。
我今年已六十岁,五十年多前的这一幕幕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恍如昨天。
注:在南京,老人们习惯说虚岁。来北京那年九岁,我印象极深;但从出生的1945年算,53年实为八周岁。以后本文中再出现的年龄,均按周岁算。
二. 爷爷奶奶
从我记事起,我就仅知道爷爷奶奶。而疼爱我的,只有奶奶一个人。
奶奶跟我说,她是从六个月把我带大的。
“喂你吃饭像唱大戏哟!”奶奶用浓重的南京腔说。“吃一口就要用勺子敲呀打呀哄你,你哭哟闹哟,唉呀呀——。”
“唱大戏”时我吃的是藕粉,四十年代的南京大概还买不到奶粉吧。我一定是小时吃藕粉吃伤了,长大后闻到藕粉的味儿都难受。
可以想见当时奶奶抱着六个月的乳孙,用小勺喂食;一边是又哭又闹,一边是又敲又唱的场景。那是一幅令人心酸的弄孙图。
我印象中的爷爷很严厉,从来没有对我笑过。而奶奶非常和善,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离开南京的前一晚,奶奶哭了,我抱住奶奶,祖孙俩哭成一团。我不想离开奶奶,不想去哪个陌生的北京;但我除了哭,没有办法。
第二天爷爷送我上火车,把我交给一个列车员。爷爷临走时给我买了好多零食,还嘱咐了我许多话,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过的和蔼。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听奶奶说,是爷爷多次给父母写信,执意要送我去北京的。
我的名字叫常无敌,这个名字就是爷爷给起的。
我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出生,然后就发生了许多大事:苏联出兵,日本鬼子投降,抗战胜利。爷爷高兴的不得了,于是赐名无敌,意为从此中国不再有外敌。我五岁多时就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学写自己的名字,无敌两个字的繁体(無敵)笔画奇多,结构复杂,难为了我很长时间。
这个名字立意不错,但也有过于张扬之嫌,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包含如此重大的爱国主义典故。到北京后父亲曾要给我改名,我不同意;后来又有人误认为“无敌”是“文革”中赶革命时髦改的名字。常无敌——这名字确实是有点个别,甚至有几分可笑;但我不想改。
我出生后不久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父母的离异。父亲和他的表妹自由结合,去了北方,我的生母带着姐姐回了老家重庆。年幼的我成了多余的人,留在南京,与奶奶相依为命。
听奶奶说我几个月大时得了可怕的肺炎,高烧至昏迷,几乎没有了呼吸,把玻璃片放在口鼻前才能查看到一丝热气。那时肺炎的死亡率很高,都说没希望了。或许因为是男孩吧,家里人不言放弃;也多亏那时有了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很贵,花了十几块现大洋,总算把这条小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父亲后来多次向我诉说当时的情景:
“大夫说扔了吧,这孩子不行了。我说不能,这孩子还有救,你一定要救救他!大夫让我给你擦身上降温,我几天几夜没合眼。后来,你哇的一声哭出来了…。”
父亲当时好像还很在意我,但后来就把我淡忘了。八年后重新生活在一起时,一切都从头开始。
三. 我不是老大
没有人告诉我妈妈是继母,但他们也不想隐瞒这一点。其实许多事都在不断地向我提示,只是当时我太小,我是在太多的困惑之后才明了的。
有一个周末,我听见父母商议:
“明天带老大去公园玩。”
当我盼望的第二天到来时,他们带着妹妹高高兴兴地出去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妹妹是老大,我不是老大。
但我明白了,他们说老大时指的就是妹妹。
我转入“西单区第一中心小学”上二年级,我的南方口音让我十分自卑,不敢在同学中讲话。有一次课堂上老师让我念生字,我把“熟”念成“书”的音,引得全班哈哈大笑。幸运的是我遇上了一个好老师,她很和气,鼓励我在课堂上发言,还时常给我回答问题的机会,使我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学会了普通话。起初我在课堂上还老低着头,害怕老师注意到我;后来上她的课时我始终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每当她微笑的眼神注视到我时,我由心底感到一股暖意。
我至今还记得她在成绩册上秀气的签字——李清香。
在家时自然要做家务,外婆说不能只吃饭不干活。
我不怕干活。早晨被外婆叫起,先要扭着头屏住气一路小跑去倒尿盆,再拎铁壶到院子里打水给大人们洗脸,等他们洗完了自己再洗。天渐冷了时,脸盆里要兑暖壶的热水,妈妈洗完了我刚要拿去倒,妈妈说:
“别倒!就着这水洗,省点热水嘛!”
我在南京没这么洗过,看着脸盆里泛着肥皂沫的水直犹豫,可又不能违抗,只好拿自己的毛巾沾湿了在脸上擦两下。当我端着脸盆出去倒时,听见妈妈在后面说:
“哎哟哟,还嫌脏呢,真是的!”
可外婆和爸爸他们都换新的水洗,妹妹有外婆伺候着洗,也是用换过的水。
一个冬天妈妈都让我用她洗过的“剩水”。
放学后便是打酱油买醋之类,后来还学会了生火和劈劈柴。到北京的第一年冬天,我端着一大盆脏水摇摇晃晃地去倒,在污水池边滑倒,头磕在地上,一下子摔昏过去,是院子里的邻居把我扶回家。我额头上起了一个大紫包,我想哭,但没有哭。
每天躺在床上,我都想念南京,想念和奶奶在一起的日子,后悔到北京来;心想当初要是赖着不走就好了,奶奶一定不会强迫我。
我家那时住在西城一个叫“四棵槐”的地方,是一个大杂院。院子里的孩子们经常在一起打打闹闹地玩。邻居大妈有时把我叫到家里,给我一块糖或一点零食,叹息道:
“这孩子真可怜!”
我则高兴地跳回院子里继续玩。那是一个还不懂得忧愁,不懂得怨恨的年龄。
随后一起刻骨铭心的“冤案”使我懂得了怨恨。
我每天上下学要路过北海公园,碧绿的湖水,飘荡的小船让我想起了南方,那高高的白塔,又带着几分神秘;不少小孩子被父母领着高高兴兴地进去,兴高采烈地出来,很是让人羡慕。公园的门票是五分钱,五分钱在当时可不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我也没有一分零花钱。
一天下午放学,北海公园门前有许多解放军战士,他们穿军装的样子吸引了我,我跟在他们周围转来转去。
一个解放军叔叔问我:
“小朋友,想进公园玩吗,跟我们一块儿进去吧!”
我当然喜出望外,那天和解放军叔叔一起玩得很开心。
回家后自然要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我如实说了;父母还没有说什么,这时外婆又说话了:
“你们别信他编的瞎话!一定是让你买东西时扣的钱,谁会花钱请你玩,全是瞎说八道!”
父母顿时大怒,不容我再辩解。父亲拿了个板子,开始打我,我挨不过,只好哭着承认是贪污了家里的钱,外婆则像破了案的福尔摩斯一样得意。
我开始恨他们,为了报复,我真的试图偷拿家里的钱。有一天,趁他们不注意时,我从抽屉里拿出五毛钱藏到一个角落里;结果很快被他们发现,又挨了一顿打。
孩子们盼望的春节到了,来串门的客人有的给我压岁钱,那是快乐的时刻;我五角钱,一元钱的积攒,好不容易攒到三块多钱,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大数目。我还没来得及考虑怎么花,外婆就跟我说:
“小孩子拿那么多钱干嘛,不小心该丢了。把钱放我这儿,我替你存着,用的时候再一点点从我这儿拿,好不好啊?”
我听她说的在理,样子又从来没有过的和气,就把钱给她了。没想到过些日子再找她要时,她脸色一变:
“人家给你钱是人情,我们是要还人情的,哪还有什么钱!”
我听不懂她的人情理论,只知道大人骗了小孩子的钱;我又气又急,可是跟她要了好几次也是分文不给;父母在一旁冷眼旁观,不帮我说一句话。
我在心里骂外婆:
“骗子!骗子!”
有了这次痛心的教训,后来过春节拿到压岁钱我就迅速地把它花光。二踢脚,黄烟炮虽然贵,也要买一些过过瘾;为了能尽情享受,我还有“少花钱多办事”的办法,就是用一块钱买十挂小鞭,然后拆散了一个一个的放,能玩好几天。
四.外公
外公从南京来了,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喜欢外公。外公戴着眼镜,样子非常有学问。他在南京当过小学校长,会讲很多故事。
他对我很和气,也很严格。比如洗手,我通常是把手在脸盆里划两下就算完;外公把我拉回去,先用肥皂把一只小黑手洗白,然后要我把另一只手洗得和这只一样。刷牙我也是敷衍了事,外公要求我刷牙时要心里数一百下。还有许多吃饭时的规矩:筷子不能在菜里来回拨动,夹了的菜不能再放下;眼睛要看自己的碗里,不能老盯着菜看,等等。
我觉得很麻烦,但还是乐意听他的。
最开心的是和外公一起洗澡。澡堂子真大,一排排的床,热腾腾的水池子,外公教我把毛巾卷起来给他搓背,然后他也给我搓;他给我搓得生疼,但很舒服。我给他搓时他老说:“使劲!使劲!”我奇怪怎么用力他也不疼。洗完澡躺在床上,会有人给你递上滚烫的毛巾,用它擦一把脸,哪个舒服劲儿就别提了。
爸爸就从来没有带我洗过澡,他好像总很忙。
外婆比外公厉害,外婆发脾气时,外公就不做声。
外公后来在北京的一所中学教语文,直到“文革”时退休。
南京打来电报,说爷爷突发脑溢血死了。
我脱口而出:
“活该!”
“不许瞎说!”这次先斥责我的是外公。
父亲去南京办丧事,然后奶奶也到了北京。
五.南京回忆
我记恨爷爷是因为他打奶奶。我小时看见他打奶奶,奶奶掉泪,我跟在旁边嚎啕大哭。
爷爷性格古怪。他一个人住在小楼上,那间屋不许我进。我曾在奶奶整理房间时偷偷进去过,知道房间里有一台能说话唱戏的收音机,我猜想那里面一定藏着小人儿,想到收音机后面看看,被奶奶慌忙制止了。
南京的家是位于“文昌巷”的一栋二层小楼,还有一个我记得非常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一棵石榴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