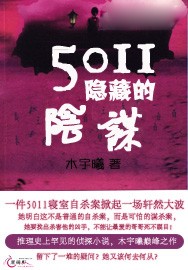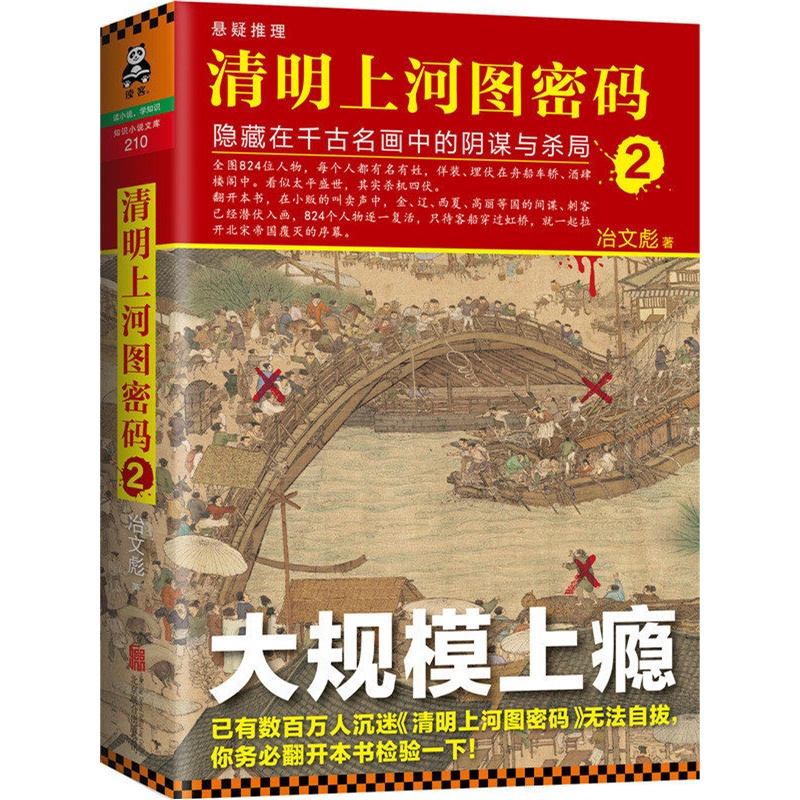母爱的阴影 作者:无敌-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在绝对错误的“革命”之中,绝对没有人道主义的容身之地。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对敌人的慈悲,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外公在文革中退休。他珍藏的《四库全书》也在“破四旧”时被迫交公。
本来是没什么事的,我们家也不是什么“封、资、修”的名门旺族,红卫兵本无暇光顾。但爸爸是不愿意在政治运动中犯错误的人,天天和外公吵闹,让他把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处理掉,否则他就要叫红卫兵。外公只好屈服,叫了一辆三轮车,把书拉到了他原来所在中学的图书馆,管图书的人直埋怨:“这时候谁还要你这些东西!”外公好说歹说,那人才答应将这些书堆放在墙角,算是交了公。
“没办法…,你爸爸天天的闹,说是红卫兵来了,别说是书,连大衣柜都保不住…”
视书如命的外公痛苦地摇着头,那表情,也如同下了一次地狱。
有失必有得,外公失去了藏书,爸爸得到了他想要的一点政治资本:他可以向组织汇报是如何坚决地敦促思想顽固的老岳父革了自己的命。
外公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些书,后来“复课闹革命”时,他到学校想“借”两本回来看,
结果一本也找不到,动乱中全部遗失。
外公退休了也闲不住,每天义务清扫楼道和院子(六六年我家搬到了朝阳区水碓子的居民楼),结果被小孩们误认为是劳改的“黑帮分子”,朝他身上扔石子。外公一气之下也不扫了,整天在家闷着,后来脑中风瘫痪在床。
由于爸爸交了南京的房子,奶奶没有了房租的收入,老住在大伯家终于引发伯母的不满,文革中改为两家轮流住。我们家是九口人两间房子,二十多平米,平时就拥挤,我回家就要打地铺。外婆管奶奶叫姐姐,她们是堂姐妹,妈妈管奶奶叫“姨妈”。可我看得出来,外婆和妈妈对奶奶充满了敌意。奶奶善良而软弱,根本摆不起长者的架子,但她温和而宽容,对咄咄逼人的外婆母女礼让三分,所以表面上还相安无事。
奶奶私下里问我交没交“女娃儿”,我说没有。
奶奶认真地说:
“交女娃儿要小心哦,不要很亲热了,把人家肚子弄大了不得了,女娃儿家不答应的。”
我埋怨奶奶:
“你说这些干什么嘛!”
奶奶笑了:
“你听我的,这是好话嘛!你要是交了女娃儿,带回来让我看看。”
也就是奶奶才会和我说这样的好话。爸爸妈妈除了让我按月寄钱,其它一概不问。
(注)马雅可夫斯基一九三○年因患“绝症”而自杀,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这是我六十年代从一本书里看到的,书名已记不清了,惟独“自杀”还能得到“批准”一事记得非常清楚。但现在的许多有关马雅可夫斯基的资料,对他的自杀或不提或简单带过,我的记忆也就缺少了佐证;我手头的资料有限,还望有识之士教之。
六.忏悔和反思
“群众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有的现象。关系较近,比较谈得上来的人组织起来,起个“兵团”,“战斗队”之类的名字,便可宣布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革命派”之间若观点不一,也会相互攻讦;这在当时叫做“派性”,一个并不难听的名词。“派性”据说会被敌人所利用,但更多的是被“自己人”在用。指导运动的军宣队、工宣队会有意透露一些档案材料,让各派别之间相互批判,制造阶级斗争的大好形势。
一九六八年秋,“清理阶级队伍”后期,老的“名牌”的阶级敌人已经批得差不多了。
一天晚上,工宣队的人找了我们这派的骨干,我当时已是本派的“笔杆子”。他们拿出一份材料,是一位姓汤的老师大学时的日记,好像是作为思想汇报交给组织的。这位汤老师是师范学院政教系毕业,参加工作比我们早几年,理论上一套一套的,曾嘲笑我们是“左派幼稚病”,所以加入我们这一派不久就退出另组织了一派,与我们有些不大不小的矛盾。
那日记的内容反映了他大学时期思想的苦闷,诉说心中“理想王国”的破灭和对“现实世界”的失落感。没有具体的所指,文字深奥,像是哲学论文。
工宣队的人说,由于他的反动日记,他一直是组织“内控”的对象,让我们写批判文章,揭露这个心怀叵测的“阶级异己分子”。
有工宣队的支持和信任,我们当然没的说,也乐于借此给他一点教训。由我起草,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上纲上线,把汤老师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世界”不满,妄图实现资本主义“理想王国”的“阶级异己分子”。
大字报一贴,全校震动。当天开了他的批判会,会上汤老师一句话也不说。
当夜,汤老师离校出走,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至今日,仍没有他的下落。
二十多年后,我们对他的日记才有所理解。 应当说,汤老师的思想水平远在我们之上,他是较早能独立思考,较早对“极左”思潮有所批判的人。
他跑到了哪里?有人推测跑到了国外,当时中越中缅边境很容易出去。即便如此,他现在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他应当回来看一看;如果死了,也应当有身边的人给他家里带个消息,为什么信息杳然?
前不久和老朋友李老师聊天,聊到文革;我们当时是一派的;谈到汤老师时都心里感到内疚。对他的出走,我们负有责任。
汤老师的下落成了压在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
是可以有许多理由为自己解脱:工宣队要整你,我们不写文章批你,也会有别人写。工宣队也没有责任:以当时的形势,不抓阶级斗争行吗?
没有人需要忏悔,有一句冠冕堂皇的话:“一切向前看。”
但是,如果汤老师活着,站在面前,我和李老师都愿意真诚地说:“对不起!”并请求他的原谅。
如果他已魂留异乡,愿我们的诚意上达天国,告慰他的英灵。
不是一个普通人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负责,而是作为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后来,工宣队又发动另一派来批判我,抓住我文革中说过“革委会代行党支部职权”的一句话不放,上纲到反对党的领导。我知道只要一认错,便是没完没了的批判和检讨,所以在针对我的“学习会”上引经据典,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到《人民日报》“革委会领导一切”的论述,夸夸而谈;总之是铁嘴钢牙的一番狡辩。所幸我资历短,让他们抓不到什么别的把柄,才让我逃过了一“批”。
学校里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七○年工宣队大换班,换了另一个厂的,队长姓何,人称何师傅,很有表演天才;张口闭口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
早晨,他敞着上衣在院子里抡一把大笤帚扫地,一位女老师过来和他打招呼:
“哎哟,何师傅,您身上怎么了,贴着膏药?”
何师傅立刻把上衣扣好,表情庄重:
“怎么让你看见了。”
然后正色道:
“我们工人阶级,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是不怕任何困难的。”
“工人阶级”的大批判也是一针见血,势不可挡;对一位学俄语的教师说:
“你学俄语想干什么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就是等苏修打过来好给他们当翻译!”
一天清晨,还没有到起床的时间,突然铃声大作,广播喇叭也响了,通知全体教职工开紧急会议,不得缺席。人人不敢怠慢,匆忙赶到会议室。
何师傅严肃地宣布:
“今天早上,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大家屏住气,紧张地等着下文。
“有人,竟然用印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的报纸,擦屁股!”
没有人敢笑。
“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我们革命的工人阶级,绝不答应!”
会议室前面的桌子上,作为物证的几张沾有排泄物的报纸残片已经被展开,有几个人正凑在一起认真地分析,也没有人怕臭。
“我们的政策是一贯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揭发有功!” 何师傅继续说。
“凡是订报纸的教研组和个人,马上把报纸收集上交,一份也不能缺,我们要做全面的调查!只要有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敬的行为,我们都要追究!”
有报纸的人都着了急,不知道自己的报还能不能找齐,否则还说不清。
案情有重大进展,那边分析结果出来了,是某月某日的《光明日报》。
有《光明日报》的老师都慌了手脚。
散会了,老师们都紧张地找报纸。在政策的强力感召下,作案人“自首”了。但那位老师是革干子弟,根红苗正,连检查都不愿意写,谁也奈何他不得,结果这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不了了之。何师傅想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捞取政治资本的小算盘也落了空。
没多久,这位何师傅从学校里消失了;打听他的去向,工宣队的人也吱吱唔唔。后来有内部消息传出来,何师傅在北京站购票时顺便掏了一个妇女的钱包,在厕所点钱时,被盯上的便衣一脚踹倒,人赃俱获。听有的师傅讲,他在厂子里原本就是个耍嘴皮子不干活的混混。
越是这样的人倒是越需要点政治资本。
二战中的巴顿将军有一股挥师作战的狂热,他的同僚说:“我们是生于战争,而他是为战争而生。”
“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生于运动,另一种人却是为运动而生。何师傅之流应属于后者。
“为战争而生”的巴顿将军何其壮,“为运动而生”的何师傅之流又何其劣也!
“复课闹革命”,学生回来了,课不好上也要上。“农业基础”课取消了,我便成了“机动”人员,缺什么教什么,我教过语文,教过历史,教过生物,后来教化学。农校的化学底子还不错,教起来还比较顺手,学校也缺化学老师,于是从那时起到退休,化学成了我的专业。
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老大(妹妹)到江苏插队,老二分配到农场。七一年,老三也插队,分到密云,离我的学校只有十几里地。
老三在密云插队时,我尽到了当哥哥的责任。我到村里看过他,村里有我的学生,不少村里人知道那是“常老师的弟弟”。
有一回妈妈不知想起了什么,对我说:
“听老三讲,他插队时到你们学校改善伙食,你们两个人就能吃一只鸡呀!”
我还真记不起来吃鸡的事。不过我记得老三让我给他买一双橡胶雨靴,我给他买了,我工作十几年也没舍得买。转正后我的月工资是四十块零五,每月给家里二十,剩下的钱除了吃也没有多少富余。
文革中,我让爸爸给我买一只箱子,因为我的东西没个箱子放不方便。在转了几个信托商店之后,爸爸给我买了一只旧皮箱,说是花了十五块钱。我不在乎新旧,能用就行。
从那以后每次回家,爸爸都跟我要买箱子的钱。开始我还不理他,心想拖延两次也就算了;没想到他还鍥而不舍,把我给要急了。
我拍案而起,用力过猛,把手震得发麻;我冲着爸爸大喊,也是让里屋的妈妈听:
“钱!你们就知道钱!再跟我要钱我跟你们脱离关系!我每个月给家里钱,你们还要,我哪儿那么多钱!买个破箱子还跟我要钱,你们给我买过什么,我跟你们要过什么?”
我把肚子里的怨气全发泄出来。
爸爸看着我,似乎也觉得理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妈妈在里屋听着,也不应声。
七. 四川探亲
:
一九七五年春,我收到一封由密云县教育局转来的信,发信的地点是四川省武隆县。我感到奇怪,信一打开,我惊呆了。
是我亲生母亲的来信!
信中的大意是:无敌,我是你的母亲,我和你姐姐在四川,你姐姐在武隆县邮电局工作。我们一直很想你,但无法和你联系。在南京的姐夫通过常家的亲戚打听到你在北京密云县教书,如果你能看到这封信,尽快和我们联系。落款是徐素,是我母亲的名字。还附有姐姐的信。
我看着看着,禁不住泪如雨下!
我的亲妈妈!多少年了,魂牵梦绕,已然是想苦想断想绝了的思念,已然是无望的祈望,已然是不敢奢求的亲情,今日得以如愿,今日终于如愿!
我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激动不已,哭了一回又一回。
等我冷静下来,我又有些茫然;我与母亲和姐姐从未谋面,她们长什么样,她们是什么样的人,我都一无所知。至疏而又至亲,真让人一时转不过弯来。
我马上回了信,急切地等待他们的回音。
母亲和姐姐回信了,还附上了她们全家的照片。照片中母亲的脸型很像我,准确地说应当是我的脸型和母亲很相像。母亲看起来有五十多岁的样子,很面善。姐姐姐夫身旁还有我的外甥女,一两岁。
我也把照片寄给了她们,不知她们看到我这个陌生的儿子(弟弟)时作何感想。
这件事告诉不告诉北京的爸爸妈妈?我考虑再三,决定告诉他们,不论他们怎么想。
我回北京和他们讲了此事,爸爸很冲动:
“我过去不和你讲,是你还小。你妈是反动地主出身,你不要只讲血缘关系,对人要阶级分析,别一点立场没有。”
听爸爸的意思,他和母亲的离异简直就是一种阶级觉悟。
我说:
“你说话注意点,她们是人民,不是敌人。”
妈妈倒温和:
“我们和你生活也二十多年了,和你还是有感情的。你总不能认她们不认我们吧。”
是否有感情我心里最清楚。不过我明白表示,我不会忘了他们的“养育之恩”。
奶奶又住到了大伯家,我看望奶奶时把母亲和姐姐的消息和她说了,奶奶很觉意外,说:
“你妈现在怎么样啦,又嫁人了没有?”
我说不知道。
奶奶叹口气:
“你姐姐叫胜男,比你大一岁。你六个月大的时候,你妈抱着你姐姐回的四川娘家。这么多年了,也不晓得她们怎么过的…”
我问当年母亲为什么要走,奶奶摇摇头,似答非答:
“我说你妈不要走,不要走,她就是不听嘛!”
奶奶叹息着:
“唉… ,作孽哟!作孽哟!”她不想再说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