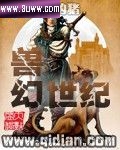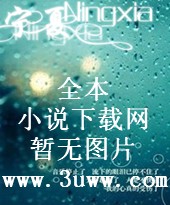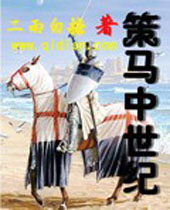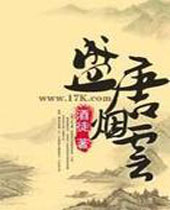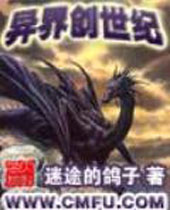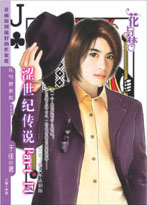世纪烟云-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低呢!
这正是天无绝人之路。易凌胜听了,真是喜笑颜开。这些年来,由于粮食紧张再加上生产队里有做无钱,农人们要生活,大部分把从地主那里分到的稍为值钱东西都已卖掉。村子里凡是土改时分的地主的屋子和家具,差不多都已是十室九空。他自己住着地主周伯年的龙凤大厦,什么眠床衣柜,沙发凳台,或是细软衣物,时钟手表的,都早就没有了。但是,地上的虽然都没有,房顶上的却是依然完好。那里每一条树桁,每一块木板,每一根瓦桷和每一片青瓦,都神秘的隐藏着财富,隐藏着钞票,在无声地向穷人们招手。他想,自己有几间屋子的房梁棚瓦,少也能卖它五七百元钱哩,吃用便再不用发愁罗!可怜穷人们总是脸朝黄土,他们的眼睛还没有往上面去看,还没有发现头顶上的这笔财富呢,得趁机先卖得个好价钱!他既佩服黄寡妇的灵醒,又感激她的关爱。这一晚便把她当作天上降下来的娘娘,加倍的殷勤,直服侍得她通体舒服,飘飘欲仙。
第二天一早,他便叫了几个泥水师傅,在自己屋里乒乒乓乓的干了起来。地主的房屋结构都很讲究。除了雕龙画凤之外,房顶瓦厚梁密,楼棚的木板树桁也全是杉树,是做家具的好材料。易凌胜吩咐师傅三梁抽一五抽二,每间房只剩下二、三条桁梁支撑住两边的墙壁就可以了,二楼的棚板也统统的拆下来;同时,又把房顶上的厚瓦也删减五分之二。正是拆屋容易建屋难,如此足足的忙了两天,三间屋子的桁梁棚瓦就都十去五六了。第三天刚好是圩日。他把拆下来的建筑材料锁好,雇了两个人工,扛了一条树桁,一担青瓦,自己挑了半担木板,便在墟尾空地上选了个位置摆卖起来。
不久便有几个山民模样的人来问价钱。
“青瓦十五块钱一担,杉木棚板十二块钱一方,大树桁二十块钱一条!”易凌胜高声出价。
“老哥,你这货比人家的贵啊!”有个山民道。
“物有所值嘛。老实对你说,咱这是旧社会大地主的房梁屋瓦,坚久耐用,豪气大方。用来建屋,保你富丽堂皇!”易凌胜说。
“你们平原的人好世界,砖瓦梁木,遍地金银,到处可以变钱!”另一个山民羡慕地说。
“这还得多谢地主老财哩。要不是他们留下的东西可以变卖来救命,这些年来早就饿死几多穷人罗!”旁边有个老人道。
“你的货太少了,便宜一点吧。”有个人想买。
“我家里还有,够你建两间屋的料。”易凌胜小声告诉他。
于是,讨价还价,最后以每百瓦十二块钱,每方杉树木板十块钱,每条6乘90(直径6寸,长9尺)的杉木桁十五块钱成交。摆在地上的先给钱,并约定下午再到货主家里去验货交易。
正在算钱的时候,忽听有人高声呼喊:
“市管会的来啦!”
于是,有几个人便扛起要卖的树桁木板飞快的逃开去了。
“这条树桁是你的么?”有俩个戴着红袖章的市管会人员走前来问易凌胜。
“这是我住的屋里拆下来的。”易凌胜道。
“对不起,政府有规定,木材交易必须有证明!”市管会的说。
“后生哥,我拆自己的屋梁是卖来买米救命的!救命也要证明么?”易凌胜说。
“没有证明的木材要没收!”一个后生哥说完便要去扛树。
“你没收那树桁我就跟你拼命!”易凌胜大声喊吼。
“你是哪个大队的?”另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喝问道。
“我是岭塘村住翻身屋的,叔父易天华是大队书记!”易凌胜高声回答。
“什么家庭成分?”
“本人三代贫农!”
一喊一吼,很快便有许多人围上来看热闹。人们都声声同情卖树桁的。市管会的俩个同志眼见不能强来,只得退让一步道:
“这一次就算了,下不为例!”说完,便大摇大摆的走开去了。
“告诉你,今天再休想欺负我,老子是贫农队长,卵棍敲得凳板响!”。易凌胜望着他们的背影悻悻地说道。
市管会的两个同志走了,围观的群众发出了喜悦的吁吁。易凌胜也开心的笑了。打从卖粮票开始,他就在市场里“揾食”,虽未成精,却也已得道,积累了许多经验。他知道市管会的同志欺软怕硬,尤其害怕“三代贫农”这四个字。只要打出这个牌子,他们便知道没有多大油水,而且纠缠起来留在市管会里还得管饭吃。有人传经,狗饿不怕狼,人穷不怕官。当今是穷的世界,穷凶则极恶。打出“三代贫农”这金牌子,到处响当当,县长也要让你三分的。
一堆青瓦房梁,棚板木桁,终于卖出了好价钱。从此,易贝车衣兜里的碎银散钱又袋得胀胀的,香烟装得鼓鼓的。他把从圩上买回来的谷子辗成上白的大米,煮成两头尖尖的硬饭,又不时到供销社去买它一两条窄尾翅的咸鱼来,再打半斤八两的烧酒,便在自己厨房里翘起二郎腿来慢慢的品尝斟酌。乌丁咸鱼加硬丁饭,他重又过起了有吃有喝的日子。
社员们瞪大眼睛见到雷公队长梁瓦换大米,个个效法,立刻就家家户户都动起来了。乒乒乒、乓乓乓,不到十天的功夫,翻身楼的,人民大厦的,解放楼的,幸福楼的,所有原来是地主们的屋子,都三下五除二,拆下了许多建筑材料。也有的索性把房梁一条不剩都拆下来,统统换上大麻竹的。于是,许多山里的朋友和有钱的人都到村里来看货议价。买的,卖的,一时甚是热闹。
岭塘村住新屋的穷人们都笑了。他们有钱买粮食了!
穷人们住的那些土改翻身分到的新屋子都空了,破了。它们被凿得百孔千疮,变得断壁颓墙,面目全非了!
第十七回 大小队各显神通;有情人终成眷属
却说易凌胜带头凿屋卖梁,虽然把住的屋子都破坏得残破不堪,但却使许多社员免受了饥荒之苦,所以,公共食堂散了后,岭塘村的水肿病人便好得快一些。但见这些原来是地主的屋子,有的梁瓦卖四留六,有的卖六留四,下雨天便不免这里穿那里漏,要用盆儿罐儿去盛那滴雨;有的一不做,二不休,把房梁瓦桷统统的卖个干净,换上用竹子搭的稻草茅棚。看是难看了一点,像秀才戴了顶烂草帽似的。但不管春夏秋冬,一家大小吃饱了肚子,把门关起来,照样不怕刮风下雨,自是福在其中。
光阴荏苒,日月如轮。不觉大饭堂散伙后,新年就又到了。新年一过,春节就近。靠了房上的梁瓦,这一个春节大家都能吃上一餐酿豆腐和几餐干饭,算是欢欢喜喜过了个年。但是,春节过后,春荒又要开始。虽然大家的米缸里都还有些粮米,却不敢多吃,仍需勒紧裤带。人人都心里知道,家有千两金,不如朝进一。生产队里分的粮不多,自家有再多的钱去买粮也只是担坭填沟渠。而生产队的禾田有限,人均就那么几分地,又还要交公余粮和超产粮供应城里人吃的粮食。所以,农人们要想过好日子就是件不容易的事。
一九六二年的体制改革后,公社由一大二公变为“队为基础”的半公不公了,公共食堂解散,大小队和个人都要拿出过日子的本事来。可各户人家已没有家底,添置家当都要从买煮饭的陶罐煲钵开始;大小队也没有基础,一穷二白,大队夜晚开会点灯的煤油还得靠公家的厕所卖尿钱去买。正是千头万绪,百废俱兴。
百业食为先。各家各户有稻谷,生产队又种了花生,各大队便都办起了榨油厂、辗米厂和米粉厂。但毕竟各个大队的人口有个限数,干这些营生赚的钱便只够供大队干部们出入开会的使用和几个工人的饭食开支。后来有的大队就又办起了织布厂,还有的又办起了竹器编织厂,更有的办起了大队综合加工厂,大队三鸟养殖场和大队鱼苗场等等,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岭塘村接近县城,历来织布业发达,许多农妇会织布,有的工商业者的家里还有一些布机。于是,大队干部开会研究,要办一间织布厂。
说干就干,征用织布机的事很容易解决。老书记出面,那些工商业者们的家庭不敢说半个不字。只一夜的功夫就无偿征到了五十多架布机。但是,工厂的场地却是个难题。全大队的地主的屋子经过土改复查已全部分尽,再也找不到办厂的好地盘。
“搭个简易厂房吧。”有人建议。
“不行,工厂的线纱布匹,被人偷走谁负责?”有人道。
“用翻身楼的公共食堂吧,上厅加中厅,少也能放四十架机。”有人说。
“更不行罗,你不见翻身楼但凡公共地方就被凿挖得七穿八漏么?”有人反对。
“华侨地主林番客有许多房舍,可不可以借来用?”有人提议。
“公家征用就是啦!现在讲一大二公,用得着向地主借吗?”有人赞成。
“不行,有华侨政策保护,这林番客一告,谁也顶不住。”治保主任张道迁说。
“去年公社想征用他的房屋做粮仓,派我去商量,这林番客都一口回绝呢!”财经主任有点信心不足的道。
原来,这林番客在泰国做生意发了财,解放前回来家乡买田做新屋。这屋子名叫凤阳楼,座西向东,红砖绿瓦,回字形结构,四个角还有炮楼,挺有派气。土改那阵,林番客被划为华侨地主,只是被分了一些田地,却没有动他的屋子。他一家人都在泰国,只有老番客和一个孙女儿在家,爷孙俩守着空荡荡的一座大厦,故早就有人想打这座屋子的主意了。不过,政府对华侨有保护政策,谁也奈何不得。这林番客虽然年过七十,但体魄还很健壮,在县社的侨联会也有些名望。去年春节,他的儿子从泰国回来探亲的时候,还请许多大干部吃饭呢。所以,干部社员都还得看重他。
“我的意见,张道迁织布有经验,由他任厂长;林番客的屋子要借来做厂房,这事就张厂长想办法吧!”老书记下结论般的道。
“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张道迁拍拍胸脯说。听书记命他做厂长,他即便心中有数。
不几天,凤阳楼的北边有一间屋子夜里忽然起火。林番客吓得敲起锣来大声呼救。幸得大队民兵和许多社员邻居及时赶到,可好就近就有池塘,大家舀水泼火,人多力量大,很快就灭了火势,免了一场火灾。事后查看,烧坏了一间屋子的瓦面。原来北面的屋边正是农田,这农田里堆放着许多晒干的禾杆,农田又近大路。治保主任张道迁分析,可能是夜晚时候有人在这路上走过,抽烟不小心,把烟头掉到晒干了的禾杆堆上面引得着火了。这霜风天气,气候干燥,又吹着北风,火顺风气,风趁火威,一下子便吹向北边屋子的窗户和瓦面。若不及时抢救,恐怕最少也得烧坏二三间屋子哩。
林老番客认为这个分析在理,又觉得烦劳了众人,心里过意不去,便叫孙女拿香烟茶水来慰劳大家。烟过半支,众人告辞。张道迁表示,大队有责任保护华侨房屋的安全。为了保护好华侨的房子,避免类此事情的发生,他建议凤阳楼北边的屋子最好借用给大队做织布厂。布厂开张后,就有人专门看管布厂和这屋子了,这是一举两得。林番客惊怕再有失火,又想有了个公家的什么厂,人气也旺一些,便也点头同意。不过,凡事先小人后君子,必须签个租借合同,还要计算租金。张道迁代表大队都一一答应了。于是,不久,布厂择日开张,治保主任住进凤阳楼,他兼任大队布厂的厂长。
有了几间工场和工厂,大队兴旺起来了。每天上工的梆声响过,便有几十个娘们从各自的屋子里走出来到布厂去上班。一会儿,几十架机儿便“的咔的咔”的叫响起来。又一会儿,那辗米机也“哒哒哒”的开动了。隆隆的机声和有节奏的织布声,交织成强劲的一曲欢歌,从早晨唱到太阳落山,使村里变得热闹极了。
干部们的工作更加忙碌了。不久,几个大队干部都戴上手表,并且,出入都骑上单车,令不少人好生羡慕。不过,这两样会转的东西都是公家出钱买的,这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干部说,比如,你一会儿要去公社开会,一会儿又要去跑生意,一会儿还得回来处理大队里的一些事情,假如你没有单车手表,怎能做好这么多的工作呢?
但就只易天华老书记一人还没有这两样会转的东西。不过,他也照样能做好工作。他每天开会做事不需看时钟,只看日头,一天之中最少也有三次准确的;他出入不会骑单车,特会走路,到公社和县里开会却不会迟到。由于他没有兼职,只是做个书记,所以他不能像那些做生意搞交易的厂长场长那样有机会大吃大喝,最多只能三天两晚的到米粉厂或小食店去沾边儿吃点宵夜;或有时候到综合厂去观察工作,顺便喝点儿豆浆或吃点儿豆干、豆腐;又或有时侯带上级来的干部同志一齐到三鸟养殖场去捉几只鸡鸭来检查质量。但只他一人吃四方,家里却还是免不了有柴无油的过日子。老婆眼见个个大队干部都比他风光,他们的老婆孩子人人都脸色油亮,心里便不免有嘀咕,常常骂他是死田螺不会过田丘。但他心里清楚,自己虽是书记,却从土改开始一直就是上面官封的。无奈没有这做官的本事,肚里没有墨水,写字难过驶牛,又不会那样算加减乘除,也就管不了生意出入,自是觉得晦气。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忽一日,公社开大队书记会议,会后去黄岭大队参观。只见黄岭大队满岭种的都是烟草,已长得有半人多高。社员们正在小心的剪摘。公社抓财贸的领导说,现在国家烟叶缺乏,种烟草能卖出好价钱。他号召各大队尽量利用山岭坡地去种烟草,早种早发,迟种迟收,还可以自办烧烤房。但烤烟必须有技术,可以参照黄岭大队的烤烟房,他们烤出来的烟叶都是一级水平的。
照黄岭的经验,一亩地的烟叶少也能赚到七八百元。
易天华抽了半辈子的烟,时常也要拿家里老母鸡下的蛋去供销社换那烟丝,他对烟叶便有特殊的感情。开会回来之后,他就有了主意。
这天夜晚,他叫自己的大孩子来商量道:
“我打算办个耕岭队。把岭坡地全部种上烟叶,再办个烤烟房。你说好不好?”
“这敢情好哩,有眼光,种烟叶准发财!”孩子易得发不禁欣喜地说道。
“我任你做耕岭队长,负责管好这件事,行吗?”父亲问。
“我保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