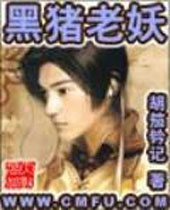推倒千年老妖-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矶元拼命的点头,她才重新将目光落在姜怜心身上,渐渐平复下情绪道:“看在你是家主,又曾经帮过小矶的份儿上,我就信你一次。”
姜怜心的唇角又抽搐了两下,俨然眼前这对男女是一家人,正勉强接纳她这个外人到家里做客。
好你个矶元,竟然暗地里金屋藏娇,藏得还是个有来头的娇。
也不知他是不是为了情爱,连修仙大业也搁到一旁去了。
姜怜心正忖度着,矶元却已挠着头对她解释道:“小璃也是有仙缘的,我瞅着一人孤独,倒不若两人结成连理,来日一同飞升,做一对神仙眷侣也好。”
听到素来只对银钱满怀兴趣的矶元说出这样一番肉麻话,姜怜心只觉得头皮发麻,于是抖了抖臂上的鸡皮疙瘩道:“甚好,甚好……”
面对眼下情形,她实在有些词穷。
毕竟一只灵兽和一个向来以捉妖为己任的道士,这样的组合,多少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然而对于她随口应来的言语,矶元却显得过于激动:“家主的意思是,不反对?!”
眼见他一双眸子都晶亮起来,姜怜心只得顺着说下去:“当然不,我只顾铺子的收益,至于你与谁私定终身,我也管不着?”
她说着,做了个摊手的动作,表示事不关己。
矶元却甚是动情的握住阿离的手,继而说道:“你毕竟是家主,而今我师父不在身边,便想着好歹得了你的应允……不管怎样,家主不反对就好。”
说到后来,他话中竟带了些感激的意味。
对于矶元将自己的辈分一下子上升到和他师父一般这件事上,姜怜心有些别扭,但也不置可否,只是看向正柔情蜜意的二人道:“我只有一桩事为你们忧心,不知当讲不当讲。”
她虽深知自己一个外人不该在此时泼冷水,可这件事也是困扰了她许久的一件事,于是先征求意见,再考虑是否问下去。
“家主请讲。”矶元答应得毫不犹豫。
见小璃只是倚在矶元怀中沉溺不语,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姜怜心便硬着头皮相问:“世人都说人妖殊途,小璃虽是灵兽,可是与凡人终归不同,寿命也长上许多,我只怕……”
后面的话她没有再说下去,其实多年后回想起这一刻,她之所以会不合时宜的问出这样唐突的问题,也全是因为念及人妖殊途四个字时,她满脑子都是画末的身影。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刻才不过温顺了片刻的小璃,听了姜怜心的话,立马就从矶元的怀里跳脱出来,一副大义凛然的表情道:“我不嫌弃小矶是凡人,小矶不嫌弃我是灵兽就够了,管他殊途不殊途的。”
对于她大胆的回答,姜怜心甚为诧异,却又听她继续嚷道:“至于寿命,即便小矶这一世未能修成仙身,我就等他下一世轮回,如此一世又一世的渡他,终有一日我们做得了神仙眷侣。再说了若是喜欢一个人,就要一心一意的喜欢,不相干的东西想那么多做什么,这不就是你们凡人所说的情爱吗?”
小璃突如其来的反问直把姜怜心问得发愣,说来在爱这件事上,小璃她一个才修成人形不久的灵兽,竟比她这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理解得透彻得多。
姜怜心于是颇为惭愧的摸了摸鼻梁,想也未想便由衷道:“在追求爱这件事上,小璃姑娘好胆魄,实在让怜心佩服。”
就矶元那个只认得银钱和妖怪的木头疙瘩,小璃定然是十分大胆,才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令这位道士不顾凡俗眼光,决定与她相守永生。
想来这故事当是比那折子戏里演的更精彩。
姜怜心这样想着,却又听小璃说道:“那是自然,若是喜欢一个人,却又不说出来,自己在心里憋闷的要死,那人却还不知道,多憋屈。”
“可要是那人心里没有你呢?”姜怜心看着小璃满目情思,下意识的便问出了这一句。
“怎么会?”小璃抬眼与矶元对望了片刻,蹙了眉答道:“就算是这样,我喜欢他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爱便是爱了,问心无愧就好。”
问心无愧就好,姜怜心一路念着这几个字自卜算铺子里出来,回了姜府。
这一日算卦的念想终究还是没有完成,然而自小璃那里,她却体悟出不少新的感触,只是尚且需要些时间来消化咀嚼。
是故,姜怜心回到姜府后只处理过堆积的公务过后,便慌忙钻进寝屋里去辗转反侧去了。
这一日她都尽量避着画末,只恐见到他后本就十分混乱思绪愈发纠缠到一起。
这样又过去一夜,该理清的思绪却还是没有起色,姜怜心无奈的从床榻上爬起来,在画末遣人来催促了好几遭之后才揣着一颗凌乱的心出了门去。
随着天气愈渐寒凉,姜怜心在水牢中落下的病根终于显露出来,身上的筋骨总是隐隐作痛,厉害的时候,全身的骨头架子都好似被人拆过一遍再重新拼装的那般。
所以自打入冬以来,她就变得十分畏寒,而这一点也被画末细致的安排进她的起居之中。
便连这晴日里时常在院子里廊下用的早膳也给挪到了厅堂里,只是这样一来,没有了院落里那些诸如风吹树梢或是鹰飞鸟啼的声音相伴,他们二人默然对坐于桌前,则成了更加令人尴尬的一件事。
作者有话要说:至此,在家主之外,矶元童鞋又多了一个三界内最怕的人,小矶乃个万年总受。
第十二章 :君心与花雕(一)
其实画末可以不必与她一道用早膳的;只是不知从何时起,他们两人就像形成了一种习惯;除非有事外出,一日三餐的膳食总是要一起用的。
多半是画末看着她用膳,自己则端着盏雪梅泡的清茶;只坐在桌旁,也不动筷。
起初姜怜心还觉得别扭,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可是到了如今却又莫名的别扭起来。
过于安静的氛围中连杯盏不经意碰撞的声音都显得格外突兀。
她指尖捻着银箸;小心翼翼的夹着糕点送到嘴里;又忍不住抬眼瞥过正饮茶的画末。
今日的阳光依然馥郁,自门口撒进厅堂中,给一袭白裳笼上柔和光晕。
跳动的光斑悬挂于他低垂的纤长睫羽;又在眼睑落下阴影,坠饰眼角的泪痣便被掩藏其中。
这样的面容格外安详,看得人不觉心驰神往。
姜怜心忘了嘴里还未溶解开来的糕点,痴然相望。
画末正以白瓷盏盖撇着漂浮的梅瓣,阳光下剔透的指几乎与玉色融为一体。
他似乎有所察觉,顿住手上动作,将目光挪到她的身上。
姜怜心却忙移开了眼,心虚的假装埋头饮粥,心下则早已乱作一团。
她忽然想起小璃的话。
“喜欢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只要问心无愧就好。”
只是,自己而今这般心慌意乱的感觉,真的就是恋慕了吗?
她盘桓着、犹豫着、纠结着,终于还是鼓起勇气抬起头来。
这一瞬间,她却对上了画末宛若无波的瞳眸,还未来得及开口,便听他说道:“再过半个月就是玉琼宴了,家主可要出席?”
对于画末所提及的玉琼宴,姜怜心自小便有所耳闻。
所谓玉琼宴,是江南酒业最大的盛会,每三年举行一次,由江南一带的商会承办。
试想飞雪漫天之际,寒风凛冽之时,邀一壶美酒,品于梅树之下,该是何等惬意之事。
故而玉琼宴多安排在年关前。
届时江南一带有名的酒行和商号都会参加,也时常有远处的商人不远千里来赴宴的。
各家都拿出自己最得意的佳酿到大会上展示,由数位酒业行当中德高望重的大师品评,选出个魁首,再以商会的名义昭告天下。
接下来的三年中,被选中之酒的赚头也必定是魁首。
如此重要的盛事,身为家主,怎可不亲自赴宴,更何况上两届玉琼宴上,姜家的酒可都拔了头筹,眼下落在她身上的担子自然也就重了。
所以当画末问她是否要出席时,姜怜心立马收起心里那些千回百转的心思,忙振奋了精神点头道:“自然要去。”
说罢她又与他详细探讨了此番成行的具体事宜,以及届时准备拿去展示的酒品,不知不觉间,竟将这个话题贯穿了整个早膳。
待到丫鬟们前来收拾盘碗时,画末却侧过头来看姜怜心,忽然问道:“你刚刚欲言又止,是否有话要说?”
没有想到自己那样小的表情变化竟被他捕捉到,姜怜心甚是尴尬的缩了缩脑袋,再想起早前欲说的话,却没了方才一时冲动的勇气。
她于是躲闪着他的目光,随口搪塞道:“也没什么,不过是件小事,我直接吩咐下人就好,不必劳烦你。”
听她这样说来,画末便也不再追问,与她辞过后,就撤了身子准备玉琼宴之事,只留下她一人,对着已然空空如也的桌机,如释重负般吁了一口气。
今年的玉琼宴在扬州举行,故而姜家众人提前数日便开始准备。
姜怜心忙着走动于各个商号,叮嘱自己不在这段时间的事宜,画末则着人赶往扬州,在他们抵达之前将一切准备妥当。
万事具备之后,姜怜心和画末,以及几名酒行掌柜才成行,至扬州时,距离玉琼宴还有两日,倒也颇得时机。
只是这短短两日里,她却也不得闲,光忙着奔波于商场上的应酬就有些忙不过来,而画末竟也十分耐心的始终陪伴左右在,这倒也令她在与那些“老江湖”们谈说时少了几分局促。
难得江南有名的经商世家齐聚扬州,那些嗅觉素来敏感的商人们自然不会放过这好机会,而这其中也不乏与姜家有交道的,所以直到玉琼宴开宴的前夕姜怜心还盛情难却的参加了一场饭局,下帖的便是她父亲多年的商道好友,吴记酒行的背后老板吴贵鑫。
说来这吴家也是江南一带的经商世家,多年来只做酒行买卖,虽不及姜家的规模,却也是有些年头的老字号。
听画末说,上一次玉琼宴姜家夺魁的时候,吴记酒行就是榜眼,不过这吴老板甚有胸怀,也不计较与魁首之名失之交臂,还亲自选了贺礼派人送到姜府,以示恭贺。
除此之外,画末又道这吴贵鑫也与赵欢过从甚密,故而还需多加提防,当然这些也不重要,只要姜怜心开口,他可保姜家再得魁首。
此刻的姜怜心终于明白,原来父亲手上,姜家之酒两举夺魁不是巧合。
姜怜心态度决然的与画末约法三章:若非涉及性命,否则不得使用妖法。
结合她惯有的执拗,画末不置可否的明知故问:“你想凭着一己之力夺得魁首。”
姜怜心却笑了笑道:“是,也不全是。”
其实姜家的酒素来远近闻名,入酒的秘方也是祖祖辈辈改了又改的,而她的父亲在去世前也为了今年的玉琼宴再次修改了秘方,意在令人耳目一新,而那秘方就藏在书房里,还是画末翻找出来的,故而要凭借势力三度蝉联魁首也不无可能。
况且与她同来的还有数位在酒行混迹了大半辈子的老掌事,各个都妥帖的很,她虽不甚懂酒,可也算不上凭借一己之力。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画末若在玉琼宴上使用妖法,必然对凡间的秩序产生干扰,那是会损修行的。
这一系列的理由,她没有一一陈列,画末也不追问,只以清冷的语调道了一句:“随你。”
依照契约,她是他的主子,他便照她的吩咐行事,本就无可厚非。
只是当他表现出这种倾向时,姜怜心却有些憋闷,但真要她矫情的同他解释那些话,她却又说不出口,便就任由这般了。
再说那饭局,吴贵鑫等数位姜家的旧交,一见姜怜心就熟络的将她恭维了一通,直说姜家的出了位女家主之事如何被传为美谈,连他们苏州一带都妇孺皆知。
虽说姜怜心深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道理,也明白这市面上关于她的传闻多半不怎么中听,但对于那几位当面的赞赏还是有些飘飘然。
她一面推辞着,一面频频举杯致意。
这就是女儿家在酒桌上的不便之处,若是盛情难却的都受了,自己吃不消,若是百般推拒,则难免损了所谓情谊。
日后风水轮流转,难保不会有相求之时,到时候再要开口就难了。
好在今日有画末同行,每到有人向她敬酒,他就格外仗义的接过酒杯,只道“家主近日身子不适,不能饮酒,这杯我且代了”,接着便举杯一仰而尽。
他既做得如此豪爽,敬酒的人也就不好多说,只有姜怜心知道他是凭借妖法化去了那些酒。
于是原本该姜怜心饮的酒便尽数被他了结。
酒至酣时,吴贵鑫又求了姜怜心一件事,却还得从玉琼宴的规矩说起。
依照往常惯例,参宴的商家需要依照次序将自家的酒呈给在场众人品评,这过程中不仅要闻酒香、观酒色、品酒味,还要介绍酒的来历背景。
往往这段关于酒的介绍在品评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试想同样的一杯酒,背后若是隐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那么人们它就多了一分好奇,品尝的时候再将那故事回味一番,唇舌间的滋味也似浓烈了几分,这就是世人的猎奇心理。
正因为如此,这段酒的背景介绍,各商行的当家通常不肯假以他人之手。
不巧的是吴记商行的酒依照次序被排在第三天展示,而吴贵鑫又道他苏州有急事,需得在第二天就打道回府,故而想求姜怜心,与排在第一天展示的姜家对调顺序。
只要双方都愿意,这在玉琼宴中也是允许的。
姜怜心见这事也不是什么大事,又道自己旅途劳顿,明日推说酒的背景故事时也怕不在状态,于是抬眼看了看画末,见他只是垂眸出神,似乎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就送了吴贵鑫这个顺水人情,豪气道:“好说好说。”
吴贵鑫于是千恩万谢,只道她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又与她连饮了三杯才作罢。
饭局持续到夜深方才结束,自酒楼中出来,姜怜心因饮得不多,神思还十分清醒,然而画末却一路不语。
姜怜心觉得气氛阴沉,只当画末不喜这沾了酒的应酬,故而不悦,所以亦不敢多说话,安静的跟着他的脚步往客栈里行去。
回到客栈里,姜怜心与画末辞道:“天色不早,我回房歇息了。”
画末却兀自推了自己的房门进去,竟连应都不应一声,偏生那阴影遮蔽了他的眉眼,叫人看不清表情。
姜怜心无奈,只得吐了吐舌头,转身往隔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