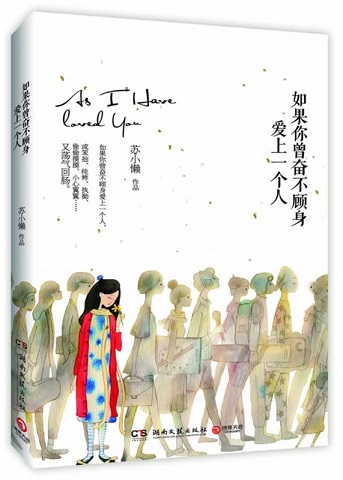如果可以这样爱.续-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已经很久没喝过咖啡了,潜意识里很害怕那种熟悉的味道。可是我连做梦都梦到西雅图的味道,那温暖的浓香,如久别的故人反复出现在梦境中,或近或远,可望而不可即,我贪婪地呼吸着,咖啡的浓香渐渐变成了他的味道,淡雅温暖,熟悉而安详的感觉一下就包围住我,梦里有淡淡的香烟气息,还有隐约的薄荷香气。那正是他的味道!
我常常在梦境中哭泣到天明。
有一次我竟然梦见跟他面对面站立在西雅图的码头边,他的声音遥远而轻微:“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最后的日子里,你还是绝情地离开。”
我鼻子发酸,膝盖发软,胸口痛得连声音都变了调子,一字一句,宛如掏心:“没有办法,墨池,如果我不离开,你一天也得不到安宁!”
“可是你走了,我更加无法安宁!”他看着我,目光哀戚得让人不忍直视,我低垂着头根本就不敢看他,只听到他的声音低沉喑哑,透着无法抑制的惶恐,“我爱你考儿,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爱你。如果你走了,我怕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再将你找回来,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害怕他继续说下去,转身就走。他拉住我的手,我想将手从他手指间抽出来,他不肯放,我就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他力气比我大,我掰不动,就指着他骂,骂的是他,却让自己的心如刀绞般,几乎不能生还。
“耿墨池,拜托你让我自由好不好,被你困了这么多年还不够吗?两个孩子都没了,你还想要我失去什么?我不想死在你的前面,你就不能给我一条生路吗?你给我放手,别再纠缠我,我永远不想再看到你!”
这么说着,我几乎已不能站稳,汹涌的泪水夺眶而出,感觉自己是个刽子手,我用这些话杀了我最爱的男人,他两眼通红,最后终于是绝望,颤抖着松开了冰凉的手指。他其实是不明白,我这样让他难过,是为了让他以后不再背负着痛苦,所有的痛,所有的不幸,我宁愿自己来背。
在转身的一刹那,我感觉心被穿了一个孔,汩汩的鲜血喷涌出来,让我怀疑自己是否能活着离开,我急急地往前走,踉踉跄跄,像个酩酊的醉汉,最后仰倒在一个公园的草地上,失声痛哭。我一直在哭,哭得胃直往上翻,最后干呕,咬着自己的手背,咬得鲜血直流,也不晓得痛。
然后天又亮了,我躺在床上吸气,好半天不能确认自己还活着。如此真实的梦境,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活在今天,却不知道是否还有明天。连忙打电话到美国,还是朱莉娅接的电话。
“先生回来过没有?”
“回来过一次,又出门了。”
“去哪儿了?”
“不知道。”
清晨的阳光透过纱帘照耀进房间,我无力地靠在床头,感觉空前的虚弱,即使沐浴着阳光,还是感觉周身冰凉。
魂不守舍地到公司上班,一进办公室就看见工作台上放着一大捧白玫瑰,满室玫瑰的芬芳,新鲜万分。我看着那捧玫瑰一阵发愣。英珠正好推门进来,夸张地叫嚷着,飞身就扑过去翻花间插的签名:“Kaven?哪个神仙?”
我默不作声地坐下工作。
“哇,荷兰空运过来吧。”英珠好像很识货,嗅着玫瑰哇哇叫:“死丫头,你怎么总是比我走运,老是被优秀的男人垂青。”
“你的骆驼不优秀吗?”
英珠哼了声,咬牙切齿:“这家伙,从认识他到现在,我连狗尾巴花都没收到过,哪像你,一收就收这么名贵的玫瑰,很贵的啊,一支就要二三十呢,如今买这种花大把送人的男人可不多见。”
我打开电脑敷衍着说:“在深圳有钱的男人多了。”
“那你就好好把握啊,谈场恋爱吧,女人是不能没有爱情滋润的,否则就会比这花还要枯萎得快!”
“我已经枯萎了。”
“切!”英珠捧着花爱不释手,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花送你吧,如果你喜欢。”
“真的?”
“不就是一束花嘛,拿去吧。”
英珠扑过来在我脸颊上狠狠地亲了口,“这还差不多,算我没白疼你!”
半个小时后,陈锦森突然出现在会议室,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昨天就听高澎说今天有个很重要的谈判,原来对手就是他!谈判桌上,他气宇轩昂地跟高澎谈合同,游刃有余,运筹帷幄,显然是谈判的高手。自始至终,我没有说过一句话,埋头用笔装作记录着什么。但我感觉得到,他炽热的目光时不时地掠过我的脸庞,让我更加不敢抬头看他。谈判进行到一半,到了用餐时间,高澎做东盛情邀他和随行高层吃饭,他很礼貌地回道:“谢谢,不必了,让白小姐一个人跟我吃饭就可以了,具体的合作事宜就由她来跟我谈吧,OK,就这样!”
高澎的笑容顿时凝固,一边的英珠也很诧异,探究地扫过我的脸。“对不起,业务上的事情我不懂。”我难堪地说。
陈锦森笑了起来,温柔地拍拍我的肩,“没关系,我教你!”
嘘声一片。在场所有的员工都盯着我,尤其英珠,双手抱胸,朝我直耸肩膀,不怀好意地坏笑。
香格里拉的四季厅华丽得让人局促。
“喜欢我送的花吗?”他开口直奔主题。
我低着头没回答。
“怎么,不喜欢跟我一起吃饭?”陈锦森这回没点西餐,而是特意点了湖南菜,微笑着给我倒酒,“其实这单生意我根本不需要跟你们公司合作的,但我还是选择你们,你知道为什么吗?应该知道吧,你那么聪明……”
“我一点也不聪明,聪明的话怎么沦落到陪客户吃饭。”我冷冷地说。
陈锦森一顿,笑容凝住了,脸色一变:“陪我吃饭让你很难堪吗,如果是这样,对不起,我很遗憾。但我是很真诚地想跟你吃顿饭,所以才不辞辛劳地从香港过来,其实这种广告上的合约根本用不着我亲自出面的……”
“谢谢,我很荣幸,但我真的没胃口。”说着我就站起身,抓起手袋头也不回地疾步走出餐厅。陈锦森马上追了出来,在门口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怎么了,我说错话了吗,对不起,我不知道……”
“没有,您怎么会错呢,您这么尊贵的身份是不会错的,”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这单生意做不成都不管了。不知怎么,在他的面前我格外在意自己卑微可怜的自尊,“您还是找别人谈合约吧,我又不懂。”
“我说了我可以教你的嘛,你怎么了,怎么突然……”陈锦森被吓住了,我竟在他面前流起泪来,他顿时慌了手脚,拽着我的胳膊不知所措,“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这么直接。”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突然情绪崩溃,众目睽睽地在香格里拉门口掩面而泣,陈锦森只得把我拉回酒店大堂,扶我在一边的沙发上坐下,掏出手帕极其温柔地给我擦拭眼泪,又堂而皇之地搂着我的肩,轻言细语地哄,温情款款的表情和声音让情绪失控的我周身发软,渐渐停止了哭泣。
“别哭了好吗,你一哭我好难过,我不知道怎么就把你弄哭了。”陈锦森的手越搂越紧,脸也贴得越来越近,呼吸浅而轻,暖暖地拂在我脸上。我的意志莫名地变得模糊,侧脸呆呆地看着他,大理石般雕刻的脸近在咫尺,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歪在他的怀里?我一个激灵站了起来,把正沉浸在温柔抚慰中的陈锦森吓了一跳。
“对不起,我……”我意识到自己出了洋相,拿手挡住脸,无地自容。
陈锦森站起身,也回过了神,又是一副彬彬有礼的绅士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好抱歉,我真没想到会把你弄哭……进去吃饭吧,你还没吃饭的,你比我上次见到时还瘦。”我顺从地跟随他回餐厅。
可是就在我转过身的时候,从大堂的电梯里走出几个穿西装的男人,个个面容冷峻,气度不凡。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走在中间的那个男人,一身藏青色西服,精致的无边眼镜,目不斜视,步履稳重矫健,昂首挺胸地走在最前面,旁边的人应该是他的手下,无论他说什么,都唯唯诺诺地点头。
我惊得要跳起来,祁树礼!
已经无路可逃了,阴谋吗?怎么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见到他?他待在西雅图好好的,跑来这里做什么?收拾我?!太夸张了,完全不可信,根本不是什么见鬼的奇遇,又是命运的故技重演,我的脚跟像粘在了地板上,完全动弹不得。
他也看到了我,停住脚步站在那里,像个冷酷的杀手,目光毫不留情地杀过来,不给我任何生还的余地。
我目瞪口呆,摇摇欲坠,顷刻间手足冰凉……
我是个不祥的人
NO。8我是个不祥的人(1)
“没错,我就是来收拾你的!我先收拾你再收拾耿墨池,你们两个是我这辈子最痛恨的人,别想我会手下留情,做梦!你们毁了我的一切!杀死我的孩子,你难道还想好好地活在这世上吗?他是快死了,不用我费多大的劲,不过听说他买了墓地,准备将来和你同葬,休想!只要有我祁树礼在,你们就别想躺到一起!哭什么,你以为还是当初,你的一滴眼泪就可以粉碎我所有的防备,白考儿,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情分可言,你就是死在我面前,我也不会难过。你这个女人,真的是不祥,只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不幸,想我祁树礼英明一世,竟然栽在你手里……”
他狠狠地说着这些话,表情决绝,如果他手中有把匕首,没准就已经捅过来了。而我没有任何还击的机会,只能怔怔地看着他。
咖啡厅里不断有人进出,音乐声很低,是Timo Tolkki的那首《Are you the one》,歌声凄婉缠绵,虽然动听,却透着深深的哀痛和无奈。
Are you the one? (你是他吗? )
The traveller in time who has e (进入我生命的陌生人。)
To heal my wounds to lead me to the sun(治愈心伤,播撒阳光。)
To walk this path with me until the end of time(结伴走在生命的小路上。)
Are you the one?(你是他吗 ?)
Who sparkles in the night like fireflies(萤火虫般留彩的目光。)
Eternity of evening sky(对视,在永恒的夜空。)
Facing the morning eye to eye(直至晨曦来临。)
Are you the one?(你是他吗 ?)
Whod share this life with me(与我共度此生。)
Whod dive into the sea with me(与我在深海偎依。)
Are you the one?(你是他吗 ?)
Whos had enough of pain(受尽创伤。)
And doesnt wish to feel the shame,anymore(不愿再心伤。)
Are you the one?(你会是他吗?)
……
'=BW('8我是个不祥的人'='泪水忽然涌出眼眶,在这样的时空听到这样的音乐。茶杯里的热气袅袅升起,我别过脸看着窗外,隔着大玻璃窗子,外面是川流不息的车和匆匆赶路的人,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如此心伤,外面明明是烈日,却恍然感觉比冬天还寒冷,我捧着杯子从里到外都在颤抖。
祁树礼根本无视这些,长长地吐出一口烟,语气中难掩霸气:“想知道我怎么收拾你吗?想知道吗?”
我没回答,低下头用吸管搅着杯中的玫瑰花茶,像是自言自语:“我,我原本是想把那个孩子生下来的,我知道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是吗?那你怀孕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你明明知道那个孩子是我的!”他用手指激动地敲着桌子,引得周围的人纷纷侧目。
“我怕他……受不了……”
“哦,原来如此,说到底都是因为他!”
“Frank,你怎么收拾我,我都没话说,可……他是个病人,没几天的日子了,只要你放过他,你想要怎么收拾我都可以。”
他哼了声,更加怒不可遏:“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为他求情,真是感天动地啊,你只要有一分这样的感情对我,我都不会这么绝望,白考儿!!”
我伏在桌子上,将脸埋在双臂中抽泣起来。
“你真的不想知道我会怎么收拾你们吗?”他咄咄逼人。
我缓缓抬起头:“随你。”
“好,有你这句话我很欣慰。”说完他直直地站起身,冲不远处的服务生喊:“埋单!”
他消失在咖啡厅门口的时候,我还没醒过来,脑子里一阵接一阵的眩晕,让我几乎透不过气。回到公司大楼,办公室的冷气开得太低,我缩在皮沙发里瑟瑟发抖,如果不是英珠推门进来,我怕我会冻死在房间。
“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英珠伸手摸我的额头,惊叫,“上帝,你在发烧,都快烧成一块炭了!”
“没什么,昨晚受了点凉。”
“还没什么呢,赶紧回家吧,或者我送你去医院。”
最后英珠送我去附近的医院打点滴,路上她跟我说:“本来还想下班后让你陪我去婚纱店的,看来只能改天喽。”
英珠和高澎要结婚了,前两天才宣布的消息。
“明天我就陪你去。”我握住她的手,由衷地感到欣慰,“你终于修成正果了,我很开心。你们若幸福,我很开心。”
她一把钩住我的脖子,“我现在就很幸福啊,骆驼说了,蜜月就带我去西藏,青藏铁路刚刚通车,我们坐火车去西藏。你知道吗,那可是我最向往的地方,自从去年在摄影展上看到那么多漂亮的西藏照片,我就向往死了……”
“呸!呸!什么向往死了,尽说瞎话!”
“哈哈……”
在医院打完点滴,已经是晚上,我们随便在外面吃了点东西就回公寓了,英珠要我上她家坐会儿,我不想当灯泡,没去。刚进门,陈锦森就打电话过来,问白天怎么联系不上我,他想请我跳舞。我说太累了。
“你生病了吗?”他好敏感,听出我说话嗡嗡的。
“还好,下午已经打过点滴了。”
“那我过来看你。”
我还来不及阻止,他就挂断了电话。二十分钟后,当他提着花篮和水果按响门铃时,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没有穿西装,一身白色便服,神清气爽,怎么看都像《魔戒》里的精灵王子奥兰多。我请他在
客厅的布艺沙发上坐下,远远的,某种熟悉的烟草气息隐隐散发在空气里,但我不想给他任何机会,给他倒了杯水,开口就说:“如果你能跟安妮一起过来看我就好了。”
他到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