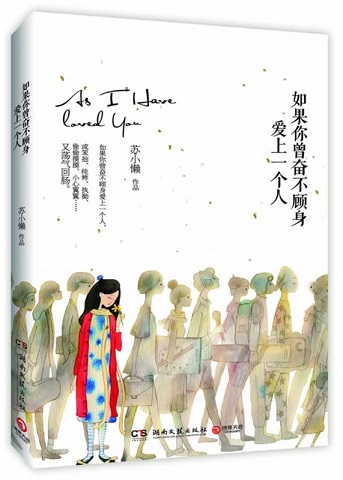如果可以这样爱.续-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旁边,主治医生毕恭毕敬地在跟祁树礼说:“祁董事,我们都很尽力,这次能逃过一劫,很大程度上都靠他内心的意志,他并不想死……”
“废话!谁愿意死啊?你愿意吗?”祁树礼立即翻了脸,气势汹汹地吼道,“我要的不仅仅是你们尽力,我要你们救活他,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不惜一切代价!”
医生低着头,战战兢兢,想辩解什么又不敢开口。
我叹口气,走过去把手放在祁树礼的肩上,说:“不要怪医生,生死有命,岂是人为可以控制的,你的心我了解,他也了解,我们都了解。”
“不,不,你不了解,”祁树礼连连摇头,焦急异常,“他必须活下来,只有他活下来,你才能很好地活着,如果我……有什么事离开,他是唯一可以给你照顾和关爱的人……”
我没理会他的意思,终于忍不住哭出声。
医生这时候又说:“请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我号啕大哭。祁树礼怎么劝都劝不住我,他的胆结石看样子又有发作的迹象,一直捂着胸口,后来可能是疼得太厉害了就一个人回了家,留了两个人在陪着我。我把他们都赶走了,独自在病房外的走廊上流泪到天明。
第二天上午,耿墨池醒过来了。
我还是不能去看他,医生进进出出,在给他做各种检查。
他的保姆这时也过来了,问起发病的原因,保姆说,是他太太去闹的。
“他太太?米兰?”
“是的。”
“她闹什么?”
保姆摇头,又说:“不清楚,只听到他们在争遗嘱什么的。”
“没错!”祁树礼刚好走了过来,背着手,神色很冷酷,“米兰逼耿墨池修改遗嘱,她知道耿墨池一个子儿都没留给她,想抢在他咽气前扭转乾坤。”
我气得浑身发抖。
这个女人,怎么如此贪婪,就算是想要财产,一定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吗?自己的丈夫多活一天,她都看不过去吗?明眼人都知道,耿墨池不是一个守财的人,他不给她钱,只是想维护自己作为丈夫的最后一点尊严,因为他左手给她钱,她可能右手就给了她的日本情人中田。没有廉耻的女人!
我直奔米兰下榻的酒店。可是在酒店门口,我却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一辆救护车被人群围着,一个满脸是血的长发女子被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抬进救护车。我的心一紧,挤过去想看个究竟,伤者的脸没看清,却看到了她指间的硕大钻戒,不用问别人,我已经知道她是谁。
我傻了似的站在人群中,目睹救护车呼啸而去,感觉不到悲伤或者焦急,只觉得一颗心像灌了铅般,沉重得就要窒息。
我怎么能够轻松得起来?
开怀大笑吗?
我做不到。
是谁做的呢?
我不知道。而颇具讽刺性的是,接米兰去
医院的急救车正是白树林医院的,她跟他的丈夫躺在了同一家医院。我将这事告诉祁树礼,他表现得很平静,只淡淡地说了句:“这种女人,不会有好结果。”末了,又补充一句,“别告诉耿墨池。”
晚上我终于可以进特护病房见耿墨池。他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鼻腔中插着氧气管子,床边的架子上挂着输液瓶。
他的脸很平静,见到我时还吃力地挤出一丝笑容:“你走,我没事。”
我知道他是不愿意让我看见他这么痛苦。
可是我真的舍不得,哪怕多留一刻也是好的。因为跟他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珍贵,值得我用全部的记忆去收藏。他却一直让我走开,走开。原来他也是个狠心肠的人,挣扎到最后,什么都无能为力,只是让我走开!
我不走,扑在床沿,握着他插着针管的手,就是这双手,曾经无数次地被我抚摸过,还是那么的修长,却因为过于消瘦,指关节的骨头突兀得触目惊心,“别让我离开你,也别为难自己,什么都不重要了,真的,那些都是身外之物,放手吧,让自己轻松点有什么不好?”我将他的手贴着自己的脸说。
他无助地望着我,长而悲地叹口气:“如果米兰有你一半的善良,我也不会这么对她……本来我将她以后的生活已经作了妥善安置,足可以让她的下辈子衣食无忧,没想到她并不满足,竟然逼我修改遗嘱,我本不是个在乎金钱的人,可她实在太贪得无厌了,她拿着我的钱自己挥霍还说得过去,可是她,她……你能理解的,这对我是一种耻辱,纵然我有对不住她的地方,她也没有权利让我到死还戴绿帽子,我也没有义务拿钱给她和中田花天酒地……”
他越说越激动,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呼吸很重。
我连忙阻止他继续说下去:“何必呢,不就是钱吗,给她就是……让自己解脱吧,你难道到死还要被她缠着吗?还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
他说:“那你就错了,考儿,我不久于人世,只要躺进坟墓就可以彻底地摆脱她,至于我的心,从来都是自由的,因为她从未拥有过我的心,她没资格,她不配!”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把目光投向站在身后的祁树礼,期望他能帮我劝劝,可是祁树礼开口却说:“你说得很对,不能这么便宜了她,否则她会以为这个世界全是以她的意志而存在,何况她还是把钱拿去给小白脸花,凭什么!”
我瞪他。他没理会,继续说:“你现在的身体很虚弱,不要太为这件事烦心,我敢保证,她不会从你这多拿走一分钱,她也必定跟你
离婚!”
“不劳你费心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能处理好。”
耿墨池感激地笑了笑,又把目光投向我,伸手轻抚我的额头,虚弱地说:“她最近瘦了好多,还烦你多照顾她一点……她这个人呀,从来不会怜惜自己,Frank,我把她交给你了,相信你能让她生活得很好的,对吗?”
我看了看祁树礼,立即被他的表情吓住了。他眼眶陡然通红,眼角渗出晶莹的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悄然淌下,他当着他昔日的情敌淌泪?
“你不要说这种话,现在还不知道谁能最后留下来照顾她呢?”他说着我不懂的话,目光无限眷恋地停留在我的身上,“她爱的是你,纵然我再怎么对她,她也不会把爱从你身上转移过来,我已经尽力了,觉得好累……”
我低下头,什么都不想说。
出了病房,我在医院的电梯门口跟米兰狭路相逢,我这才知道她伤得不轻,头上脸上全蒙着纱布,只露出一双美丽空洞的大眼睛。要不是她拦住我,我是断然认不出她来的。
我们相互对视着,杀气腾腾,大有决一死战的意味。我不太明白她怎么能用如此仇恨的目光刺杀我,难道她以为是我叫人弄伤了她?
米兰痛苦地扯动着嘴唇,想对我说什么,却因为刚刚缝过针无法张嘴说话,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从我身边昂首走过去。我转身正想进电梯,却猛然看见祁树礼就站在不远处打量着米兰,他很“欣赏”地目送米兰远去,嘴角还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我心里咯噔一下,此君的表情无疑泄露了他心里的秘密,别人看不出来,我却是太熟悉不过了,每当他用那样的目光去打量一个人时,这个人八成就有麻烦了,或者说已经有了麻烦。
“你是不是做得太狠了?”我走过去责备道。
“没事,伤口不是很大,我已经派人从韩国请来了最好的整容师,”他若无其事地瞟了我一眼,丝毫没觉得哪里不妥,“可能要花我几十万呢,我保她旧貌换新颜,整出来的样子比那些个韩国
女明星不会差到哪去,到时候只怕她感激我都来不及。”
说着他居然还呵呵地笑了起来,好像他做的是善事,末了,又补充道:“我就是看不得她那张嘴脸,贪得无厌,贱!”
“可这不是君子所为!”我还是觉得不妥。
他冷笑:“君子?考儿,你跟我相处也有这么些年了,我何时称自己是君子?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的‘好’只是对你而言,撇开你,杀人放火我都不在话下。”
我横他一眼,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脸色变得肃穆起来,“有个不好的消息,想告诉你。
“什……什么消息?”我本能地缩了下。
他看着我,眼神透着悲凉和无奈。
我一看他这样子就急:“什么事啊?你快说!”
他叹口气:“从新西兰传来消息,Steven他……他母亲病危……”
我用所有报答爱
我用所有报答爱(1)
耿墨池的病情时好时坏。
又先后两次进了抢救室。
我更加不敢将他母亲病危的消息告诉他。
有一天他的状况较好时,对我说:“我这几天老做梦。”
“你都梦见什么了?”我故作轻松地问。
“我……梦见我母亲了,”他神情恍惚,嘴角微动,吐出每一个字都很吃力,“她可能不太好,躺在床上,不停地朝我招手,我……我忽然好想见她,算算看,我已经半年多没去看过她了……”
我瞅着他发愣。脑子里反复闪现耿母端庄优雅又伤感的面容,在新西兰相处的那一个多月,她如圣母般的美丽和慈爱让我倍觉温暖。我甚是感叹,难道他们母子有心灵感应,这边病入膏肓,那边也生命垂危?
忽然觉得他们母子好可怜。
一个在海外郁郁寡欢了半生,一个被病痛折磨至今,彼此连见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莫非是老天的蓄意安排?莫非他们母子真要到天堂去相聚?
他何其的敏感,我六神无主的样子让他察觉到了什么,目光犀利地在我脸上扫来扫去,疑惑地问:“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抬起头,躲躲闪闪,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有些不悦:“怎么了,有什么事就干脆点,干吗吞吞吐吐?”
我知道瞒不住了,心一横,支吾着说:“前两天,从新西兰传来消息,你……母亲她老人家……”
“别说了,我知道!”他打断我,闭上眼睛,眉心都在跳,“她……过了,是不是?”他低声问,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又是一场空前的灾难,我几乎可以听到他内心山崩地裂般的声音。
“不是,还没有,她只是想见你最后一面……”
“知……知道了。”
耿墨池喃喃的,泪光闪动,强忍的悲痛又怎么藏得住。他扭过头,想必是不想让我看见他脆弱的样子。
“你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你没事吧?”我担忧地看着他。
“没事,让我静会儿就好。”他蠕动着嘴唇,像在说梦话。
我只得离开,轻手轻脚的,生怕刺激到他。
一个护士刚好进去给他量血压。
我还没出病房十米就听到护士冲出门来大叫:“不好了,快叫医生,308号病床心跳停止……”
安妮突然提出要搬出去住。
每个人都措手不及。
祁树礼伤心欲绝:“难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你来说都是多余的吗?”
安妮只是答:“我不想成为你们的累赘。”
“没有人把你当累赘,这阵子因为你哥哥的状况很不稳定,所以忽略了你,难道这就是你弃我们而去的原因吗?”祁树礼的声音都在颤抖。
安妮看不见她哥哥,但目光终于还是有些不忍。
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这阵子她很少到
医院探望耿墨池。而且听保姆讲,她经常一个人坐车出去,去哪里了,去见谁,没人知道。祁树礼想问个明白,她却别过脸一声不吭地摸索着上楼,重重地关上了卧室的门。我和祁树礼面面相觑,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心头,环顾富丽堂皇的
客厅,竟有种风雨欲来的压抑和阴沉。
我在内心还是责怪安妮的任性,她是否知道,她的哥哥在死亡线上挣扎得有多痛苦、多艰难,那次心脏停止跳动达十分钟,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才恢复生理运转,在医学上称得上是奇迹了。可即使从上海、北京请来最好的心脏病专家,每天二十四小时一刻不停地对他进行观察和检测,但若离开那些仪器和管子,他一分钟都活不下去。
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就在他昏迷后的第四天。
每天,我都趴在病房的玻璃窗户上,看着他靠用机器维持着脆弱的生命,看着床边的各种仪表不断显示的不同的数字,我的眼泪哗哗地涌出来,模糊的泪光里他的脸遥远而陌生,千辛万苦啊,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从前,到了今天却都是枉然。说什么一生一世,一生一世那样久,是他放弃,还是我坚持不了,到了现在时光的钟摆突然就止步不前,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永恒”,我宁愿不要!
但我没法恨他,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可怜的人,生命的存在,如今对他而言只是仪表上闪烁着的枯燥的曲线,现实世界实际已经远离他,而他却浑然不觉,他知道他母亲离世了吗?他睡得那么沉,是不是又做梦了,他又梦见他母亲了吗?
很想大声呵斥他:耿墨池,你不能就这样丢下我,即使你会在西雅图的那块墓地里等着我,可漫漫人生,凄凉无边,你要我如何可以撑到那一天?我什么都答应了你,什么都满足了你,甚至做了你一天的新娘,可是你连最后的存在都给不了我!
新西兰。惠灵顿。仰望天空的地方。
仿佛依稀还是昨天,却原来,已经这么久远。远得成了前世的废墟。而我站在玻璃窗前,几乎没有望他的勇气,我这样懦弱,这样在意他的存在,发狂一样的在意。可是怎奈何曲终人散,我和他的这一辈子,终于还是完了。无法容忍,不能接受,他竟以如此沉默的方式离开,还说什么如果实在不忍,就让我转过身,他自己其实比我更不忍,所以才闭着眼睛一声不吭。可是闭上眼睛我就不心碎了吗?他闻得到我泪水的气息,他是故意的,他故意这样让我心碎!
可是,他昏迷的第七天。我还是趴在玻璃窗上看他。
“我们都输了。”米兰突然走了过来。事实上她站在一旁已经观察我半天了,我伤心无助的样子应该让她觉得很痛快。
“我们谁都没得到他,不是吗?”她淡淡地说,头上的纱布已拆除,一张脸陌生得让我不能相信站在眼前的女人就是米兰。
“你怎么会来这儿?”我恍惚问了句。
“我是他太太,我不来谁来?”
这个时候她倒想起自己是他的太太了。
我别过脸,懒得理她。
“听说耿墨池把全部财产都留给了你,”米兰直奔主题,也不看我,望着她的丈夫自嘲地冷笑,“他对你真是爱到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