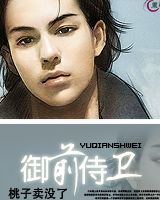御前疯子-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严吉说的不假,他的确是从鬼门关回来的。哪有人走路撞柱子撞到了后面,哪有柱子会把人的脑袋撞出个这么大的窟窿来?
疯了倒也好。
她缓慢地将手收了回来,重又挪回原来坐的地方,然而在这时,马车却倏地颠簸了一下。她一个没扶稳,整个人往后一倾,重重撞在了夏笙寒的身上;一抬头,恰好对上他的一双明眸。
“你想非礼我么?”他低头注视着她横七竖八倒着的样子,眼中笑意不止。
“才才才才没没没!”傅茗渊的脸“刷”一下就红了,语无伦次地喊叫了一通,手臂却被对方忽的一拉。
夏笙寒的面色沉了下来,将她拽到了马车的最里边,头也不回地叮嘱道:“呆在这里别动。”
“怎么了?”她急问。
“有杀气。”
不等傅茗渊反应过来,他已然执着伞跃下了马车;与此同时,外面顷刻响起了一阵骚动,混乱的马车响彻耳畔,继而是云沐高声喊道:“速速护送陛下与公主离开!”
上一次遇袭还是去年冬天;此次随行的人马虽然不多,但也没有少到让人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袭,除非是——提前便知道了他们的行程。
百官虽然知晓景帝要出宫,可具体的路线和目的地却是少有人了解;即是说:这幕后之人的地位绝对不低。
傅茗渊心里一阵烦乱,虽然夏笙寒让她呆着别动,可他看起来就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相信他不如相信自己,再这么坐着便是让人瓮中捉鳖。
她心念一动,当即跳下了马车,却不敢在原地多作停留,弯着身子朝阿尘所在的方向奔了过去,余光瞥见几道黑色的身影与云沐的兵马纠缠,也来不及多想,低声唤道:“阿尘,出事了。”
她虽然竭力奔跑,但到底还是被其中几个刺客看见了,有两人瞬间向着她的方向刺了过来。便在这时,车门大开,那二人顷刻被一股力道踹了出去。
傅茗渊的手臂被人一抓,一抬头,是面色沉静的阿尘:“阿渊,没事吧?”
“我没事,我们去保护陛下。”她说着往车内看了一眼,只瞧见吓坏了的辛公公,却不见严吉,“严公公呢?”
“严公公去陛下那里了啊。”
傅茗渊讶道:“他会功夫?”
“谁知道啊。”
“”
二人心知不可多作停留,遂将辛公公带到一旁的隐蔽处,混乱之中奔向了景帝所处的位置,好在他毫发无伤。傅茗渊松了口气,立即拽过他的手,“陛下,我们先走。”
“不行。”景帝的脸色发白,四处张望着,焦急道,“亦纯刚才突然跑出去了!”
傅茗渊一惊,即刻开始搜寻信阳公主的身影,然而在一片混乱之中,却是怎么也找不到。尽管我方在明敌方在暗,但云沐征战多年的实力不是吹嘘出来的,短时间内便将刺客们击毙了大半。
其余的刺客见状不妙,当即转身撤退;云沐正气凛然地大叫:“活捉!”
在他话音刚落之时,竟有一道道暗箭从附近的树上突袭而来,想必是这些人为逃跑准备好的最后手段。
四面八方的暗箭几乎将他们包围,不少护卫都中了招,纷纷坠马。傅茗渊虽然带着景帝退到了安全的地方,但仍旧不见信阳公主,急得冒了一身冷汗。
暗器的准备显然十分周全,她连马都不会骑,丝毫搭不上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云沐一人在马上持枪对抗。霎时间,在一个不易被察觉的角落竟忽然射出数枚暗器,直刺云沐的后背。
“——小心!”
傅茗渊忍不住叫了出来,以为他就要血溅当场,视野之中却忽然现出一抹白衣身影,熟悉到令她看一个背影便知晓是谁。
乍现的冷光从那柄紫伞中射出,她甚至没有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后的一波暗箭已被销毁殆尽。而在云沐的身前,夏笙寒正波澜不惊地站定,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徐徐走到傅茗渊的面前,用伞轻轻敲了敲她的脑袋:“谁让你跑出来的?”
“呃”她愣了一瞬,耳边却骤然听见一声啜泣,抬眸望去,竟是信阳公主跪坐在不远处,手里沾着血,面色惶然。
头一个跑过去的便是景帝,拉起小公主左看右瞧,确定她没有受伤,才松了口气,责备道:“你刚才为什么忽然跑出去?”
信阳公主却像没听见他说话似的,茫然地盯着前方,惊慌失措道:“臭小子他他”
傅茗渊上前一看,竟是殷哲半跪在地,用银枪支撑着身体,但背部有一道显而易见的伤口,两袖也被暗箭划了不少伤处。
“阿哲!”夏笙寒连忙上前一探,神色适才有了缓和,“还好,伤的不重。”
殷哲面无血色,但还是露出腼腆的笑容,摇头道:“王爷,我没事。”
听到这句话,忍了半天的小公主终于开始掉眼泪,嗅着鼻子道:“刚才我脚崴了,害得臭小子中了一刀,还有好多好多箭”
她说到一半便开始语无伦次,最终还是被景帝安慰着到一旁坐着。损失不算惨重,却是吓坏了不少人,故而只得暂时休息。
云沐的臂上淌着血,却像没有察觉似的,在周围的刺客身上探查一番,但什么也没找到,皱着眉道:“不行,全死了。”
傅茗渊见状有些不忍,屡次想要走过去却又折了回来。在她内心挣扎之时,眼前忽然闪过一张脸,是夏笙寒突如其来凑了上来,睁大双眼盯着她。
“你你还吓我!”她猛地喘了两口气,才注意到对方的脸色比先前白了许多,便问,“你怎么了?”
夏笙寒耸了耸肩,信手掷了个东西给她,随后转身便走,轻声道:“想去就去罢。”
她抬手一看,才知他方才扔来的是一团干净的纱布,大约是看出了她想给云沐包扎。傅茗渊也没多想,径直朝着云沐走了过去,试探地说:“云大人,我看你臂上破了不少口子,要不先处理一下吧?”
云沐抬起头望她,目光有些惊讶,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有劳傅大人了。”
傅茗渊冲他笑了一下,蹲下来撕开他被割裂的袖子,看见那一道道清晰可见的伤痕,有新伤有旧伤,不由地倒吸了一口气。
见她一时愣了,云沐有些不适地往旁边挪了挪,不耐道:“不过是在战场上的旧伤罢了。”
她连忙点头,仓促处理了一下伤口,用纱布小心翼翼地给他包扎好。她皮肤白皙,手很小也很软,丝毫不似男子的硌人,处理伤口时也是十分谨慎。
云沐微微皱着眉头,盯着她瞧了半晌也没有开口,眼神不自在地扫向远处,默然不语。
因这一行信阳公主受到了惊吓,他们不得不在最近的一处行宫落脚。傅茗渊一时想不出是谁下的手,遂将手揣在袖子里,在庭院里散了会儿步。
种种猜测扰乱着她的心神,眼前却莫名现出了夏笙寒那张略略苍白的脸。直觉告诉她有哪里不对,遂决定前去对方的房间问一问。
一更钟漏,月华如水,大多数人已经睡下,唯有几间屋子里亮着火光。她轻手轻脚地走到夏笙寒的门外,正欲敲门,忽地听见里面传来严吉的声音,话里带着责备:“王爷,这暗箭都刺到肉里去了,刚才为何不说?”
傅茗渊微怔,顷刻想起他在救下云沐之后,面色便有些怪异,竟是因为这个。
“说了又怎么样,反正也没有人给我包扎。”
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不是说有仇么,怎么还如此拼命?
她在外边驻足,感觉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给揪了一下,好似潭水里被丢了一颗石子,漾起的涟漪久不停歇。
最终她还是没有去敲门,小心翼翼地退了两步,踮着脚尖走回了屋子。
绕过回廊的另一间屋子里,云府随同的小厮正在给云沐换药。这小厮跟随他征战多年,处理伤口的功夫不亚于大夫,不一会儿便清理干净,一抬头,却看见自家少爷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不对。”他突然吐出了两个字,把那小厮吓了一跳。
“少少少少爷你怎么了?!”
云沐摇了摇头,可紧蹙的眉依然不松,目光落定在小厮的手上,琢磨道:“手,不对。”
小厮闻言,立即抱紧了手臂,两眼通红,“少爷难道你要剁了我的手么?!”
云沐不知道他想到哪里去了,神色不耐地摇头,摆手道:“你出去罢;小心点,这里不大对劲。”
小厮不解道:“何处不对劲?刺客不是都死了么?”
云沐凝神思索了一会儿,扶额叹气:“不是刺客,而是出宫时我便有所察觉,有谁一直在盯着我。”
「秣陵」
秣陵位于江南水乡,沿路都是好山好水好风景。初秋的天气微凉,傅茗渊算着来葵水的日子快要到了,遂裹了不少衣裳。
她琢磨着,连京城的慧王府都是那般寒酸,想来远在江南的藩地更是好不到哪里去,指不定早已长满了杂草,被百姓们装点装点,在鬼节用来吓人。
她对这个想法深信不疑,然而事实却通常出乎意料。
城中繁荣红火,百姓安居乐业,大街小巷里都有人在感叹:真是慧王殿下的功劳啊。
开开开开什么玩笑?!
傅茗渊不可思议地往夏笙寒那里瞅了一眼,想瞧出他究竟给人吃了什么迷药,可对方只是笑呵呵地不答。
慧王府在城南方向,但一行人未至王府便看见外面排了一条长龙,一人端着一个碗扯着一个麻袋进府,随后兴高采烈地捎着食物出来,纷纷笑逐颜开:“慧王殿下简直是活菩萨啊!”
傅茗渊揉了两下耳朵,确定没有听错,不可思议地奔下马车往里边一瞅,瞧得人群之中正立着两个男子,一人是个胖乎乎的和尚,另一人是个坐着轮椅的青年男人,正在四处分发食物;而百姓的那一声“慧王殿下”,唤的正是这个中年和尚。
不可理解。
她看向夏笙寒:“你被人冒充了?”
“没有啊。”他摊开手。
见他丝毫没有进去的意思,傅茗渊也只好在外面候着,直到前来领食物的人们都走光了,云沐才护送着景帝与信阳公主前来。
这间府邸与京城之中的慧王府是天壤之别,虽然占地没什么不同,却是收拾得干净整齐,一尘不染,更重要的是有生气。
“王爷?”忽听一个浑厚的声音自不远处响起,原来是那中年和尚注意到了他们,大笑不止,“你可算回来了啊!我们都等得急死了!”
景帝盯着那人瞧了片刻,顿时惊喜道:“小皇叔,这就是你说的帮你治病的和尚?”
听这一言,那二人才注意到面前站着的是当今圣上,连忙行礼,但那青年男人由于腿脚不便,方一颔首便被景帝拦住:“不要紧不要紧,朕是微服私访。”
傅茗渊始终不能理解这究竟是什么情况,遂问那和尚道:“他们为何唤你为‘慧王’?”
和尚朗笑道:“我们住在慧王府,他们就以为我是慧王了。”
因这二人一个没有头发,一个坐着轮椅,她仍是有些不可置信,遂与景帝道:“陛下,这里不寻常啊。”
景帝摊开手,无所谓道:“反正小皇叔疯了,有什么不可能的。”
不知为何,这句话竟让傅茗渊有了一瞬的认同,没再多言。很快,她便了解了这二人与夏笙寒的关系。
和尚名叫一心,是个常年走江湖的出家人,与夏笙寒一见如故,就留在了慧王府帮忙看家;而那个腿脚不便的男人则是府上的食客,名叫水仙。
傅茗渊一口水呛了出来:“他不是男人么?”
夏笙寒瞥她一眼:“男人就不能叫这个名字了?”
果然,所谓疯子便是物以类聚。
秣陵毕竟是大城,富人多,吃不饱穿不暖的也多,一心和尚便会定期给百姓分发一些食物,这钱自然是由夏笙寒来掏。
她与景帝一致认为,是这二人对一个疯子进行的残忍敲诈,但见百姓们如此快活,也就没说什么。
近来信阳公主总是有些神色恍惚,傅茗渊屡次看到她出现在殷哲的房门外,站了一会儿,却又不进去。
她也理解这份惆怅从何而来:倘若不是小公主崴了脚,殷哲也不会受伤;纵然是意外,可心里不好受却是真的。
景帝亦看出了自家妹妹心里不开心,遂提议一道上街游玩,顺便逛一逛秣陵城。
休憩一宿之后,傅茗渊作好准备随行,刚一出门便被夏笙寒给叫住:“你去哪里?”
她蓦地一惊,故作镇定道:“当然是去街上。”
“我看你图谋不轨。”
傅茗渊听罢,反应再慢也知道他指的是云沐,当即反驳道:“我是去陪陛下!他天生是个路盲,走丢了怎么办?”
夏笙寒盯着她,显然不太相信这个解释,云淡风轻地来了句:“云大人也同去?”
傅茗渊点点头。
“那好,他肯定不是个路盲。”他一把将她拽了回去,丢回厅中,“严吉对秣陵也熟,让他带着更好,比你有用。”
傅茗渊瞪了他一眼,挣扎了,反抗了,失败了。
景帝显然是早与夏笙寒串通好,出门之时没瞧见她,却问都没有问,倒是云沐有些疑惑道:“陛下,傅大人怎么没有来?”
“傅爱卿说他病了。”景帝摆摆手,看着对方的惑然之色,补充道,“水土不服。”
云沐点点头,想到傅茗渊那小身板,立即相信了这个解释,很快便在严吉的带领下,前去秣陵一日游了。
傅茗渊闷闷地坐在屋子里边,其实要出去也不是没有办法,但夏笙寒与她说话的时候,尽管如往常一样疯疯癫癫,可那苍白的脸色是装不出来的。
她清楚记得就在前不久,他为了救云沐,被一支暗箭刺伤了肩膀,当时用伞遮得很好,可到底是伤着了,一条右臂不怎么能动,连吃饭都是用的左手。
她愈想愈觉得应该表达些什么,遂前去询问懂医理的一心和尚,但出了屋才发现,除了

![[病娇]疯子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