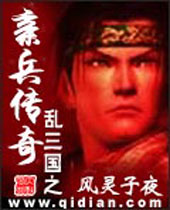凌烟乱-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碍事。”
“”
“好了,你先退下去吧,山庄里人多眼杂,不宜久留。行事多加小心。”
“是,属下告退。”
这个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缦舞侧着头在记忆中搜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房间里已是一阵寂静,看样子,那人已经离开。
她在门口呆愣愣地傻站了一会儿,方才想起手里还端着拿来给轻寒喝的药,赶忙敛了敛情绪敲敲门踏进房门,波澜不惊的脸上似是什么都不曾听见一样。
“师父,我把药端来了。”缦舞佯装无事人一般,心里却执念于“夙翎之毒”,难以释怀。
轻寒坐在桌前,面无表情地看着缦舞走进来,霍地开口道:
“你都听见了。”
《凌烟乱》苏窨 ˇ悦君君不知ˇ
“你都听见了。”
轻寒小啜了一口杯中茶水,面色似水无波,清冷如月,冰冷的视线如同一道精芒,直直逼向毫无防备的缦舞。
被这样的视线盯得浑身一颤,缦舞捧着药碗的手下意识抖了抖,药汁毫无预兆地洒到她的手背上,滚烫瞬间化为刺痛,在她手背上肆无忌惮地蔓延。
缦舞吃痛地倒抽一口凉气,强忍着疼痛走到桌边将药碗放下,暗自松了口气,所幸没有洒掉太多。
刚一放下碗,她的手腕倏地被轻寒握住,“怎么这样不小心。”轻寒的眉梢拧在一起,缦舞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背已是又红又肿,锥心似的痛楚一阵接着一阵。
“还疼不疼?”轻寒一面小心翼翼地给她上药,一面柔声问道。
缦舞摇摇头。这药乃是轻寒多年私藏,即便是那些个大夫郎中也未必有着方子。凝胶状的药抹到手背上,沁凉之感很快盖过原有的灼热,沿着皮肤一直往下渗透进骨子里。
表面的红肿没一会儿的功夫便消退了下去,果真药效显著。
暗自赞叹之余,缦舞偷眼瞧着为她上药的轻寒。
素来沉黯的眼眸中,摇曳着隐约可见的心疼。心疼?轻寒也会露出这般表情么。缦舞回想起幼时,每每贪玩摔伤,师父总会如现在这般替她悉心上药。
及笄之后,性情愈发沉静的缦舞,再未做出过年幼时那样不知天高地厚的事儿来,自然也就再没有机会如此这般由着师父给她上药。
时隔多年,缦舞恍惚间宛如回到了多年以前,自己犹是天真幼童的时代。
只是,曾经的静好年华,早已在四季交叠间湮没于时光洪流之中。
情深似景,景逝弃隅。
“为何不松手?”缦舞心头一紧,却听轻寒继续道,“都洒到手上了,为何不将那药碗丢了。逞强,到头来还不是伤了自己。”
轻寒的话听着似是责备,个中关切之意却是明明白白显露无疑,听得缦舞心里一暖。
“若是都洒了,师父今儿就吃不上药了”这药是特意为了轻寒调配,一副药得煎上足足三个时辰,错过这一副,可不是得等到第二日了么。
缦舞的头垂得低低,淡漠的表情里含着一丝委屈。
又陷入了一阵静默,轻寒变态凝视着眼前这个默默不语的少女,霍地举起桌上药碗,仰头之际一饮成空。
苦涩的药汁顺着喉管灌下,尽管药味浓烈呛鼻,轻寒照旧面不改色。几滴从嘴边逃脱的汤药,沿着唇角缓缓流下,溅落在他纤尘不染的衣衫上,晕开小小一圈深色印渍。
而他并不在意,手一扬便将空碗随意地置于桌上,再不看它半眼。
轻寒背过身收拾起方才拿出来的药品,一面将摊了一桌的瓶瓶罐罐往药箱里收,一面不紧不慢地开口:“方才你在门外都听见了。”
这一回,缦舞的反应显然比先前轻微很多,心里纠结了一阵,盘算着该用什么借口搪塞过去。但转念一想,既然轻寒都这样开口问了,必然已有十足把握,她再狡辩,又有何用。
思及此,她懒懒地呼了口气,有些沮丧。
从小到大,从没有什么事能够瞒得过师父,也不知她是该喜还是该忧。
缦舞深深吸了口气,再一次抬起头时,眼中闪现的,是作为凌烟山庄风堂堂主应有的坚忍。
“师父,为何一直不告诉我,你所中的是夙翎之毒?”
所谓的夙翎之毒,乃是一种罕见的慢性毒,起初时其毒性较弱,隐于中毒者体内,随着时日流逝,毒性渐渐挥发出来,一点一点侵蚀中毒者的精魄,使其愈渐虚弱,若不能及时解毒,终将油尽灯枯。
而夙翎的解药,唯有
“说了也只能让你担心罢了。”轻寒总是如此清冷,清冷到,使得缦舞不由地怀疑起自己存在的价值。
只能担心么。缦舞苦笑。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便轻寒果真将自己身中夙翎之毒的真相讲予她听,结果,也未必两样。
她能做什么?她能为他做些什么?连缦舞自己也不清楚。她能做的,恐怕也只有如今这般,默默转身,然后,离开。
屋外忽然下起了雨,大雨滂沱,惊雷划破天际,闪电将昏暗的天幕撕碎,破碎天幕如同凋零夜花。雷鸣,即为她的哭泣。
早春雷雨,空气中的湿冷仍是一刻不断地往骨子里钻,渐渐积聚漫高成溪的雨水,打湿了女子素衣飘摇的裙摆,贴在脚踝,冰冷刺骨。
她赤着脚走近院子,任凭雨水发疯般的冲刷,雨中,她本就娇弱的身躯显得羸羸不盈一握,像是随时都会被雨水同化,化作满地涟漪消散不见。
她紧闭双眸,耳边充斥着雨水磅礴之声,再听不见,再看不见。
如果可以,她只希望大雨能够带走在她心头积压许久的忧悒,带走她心中那份无法割舍的思念。
如果可以,是否可以放下十年来始终存在,却不应留下的痕迹。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君不知
大雨没有带走缦舞心中的抑郁,只带走了她的意识。
朦朦胧胧,似乎有人在唤她,“舞儿,舞儿”叠声呼唤,有些焦急,有些疼惜。
回头的时候,一道坚毅挺拔的身影伫立在她身后,不远不近,刚巧一步之遥。硕大的伞面遮挡住了那人的面容,缦舞唇边漾起一抹微笑,凄美如胜放的鸢尾。
宿命中的游离和破碎的激情,美丽而又精致,可是易碎且易逝。
谁人说,回眸一笑百媚生。
怎奈这样的笑容并不属于他。
城七眼看着缦舞将自己淋湿,回眸一笑之后,整个身子像是被抽光了所有气力,软软滑落,仿佛凋零的花瓣。
他本能上前接住了她,油纸伞被无情弃到一旁,跌落在大雨滂沱之中。
缦舞的身子无力地落在城七怀里,脸上胡乱流淌的,是雨水,还是泪水?不得而知。
城七将昏迷不醒的缦舞抱进屋子,他望着衣服全部湿透、浑身冰冷的缦舞,心里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伸手抵上她的额头,滚烫的温度透过掌心传达给城七。
好烫,发烧了。
“师父”昏睡中的缦舞动了动唇,喃喃出声。
城七眉心微蹩,拍了拍她的脸颊,“舞儿,舞儿。”
可是,无论他唤她多少遍,缦舞仍是处在昏睡不醒的状态,嘴里不时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额上的温度越发高了。城七不由地开始着急。再这么下去可不要越来越严重了。
他在房里踯躅半晌,来回踱步直到他自己心里头都开始变得烦闷,终于咬咬牙,跑向了嬿婉的屋子。
当不明所以的嬿婉被城七拖到屋子里时,甫一看见浑身湿透昏迷不醒的缦舞,立即明白过来,这丫头必然是淋了雨,烦闷未有消除,却是把自己的身子骨给折腾坏了。
嬿婉把城七推出了门外,城七不解:“你这是做什么?”
嬿婉横他一眼:“我这不是要给舞儿换衣服么,总不能让她就这么一直穿着那身湿衣服吧,本来没病也得捂出病来了。”
被嬿婉说得面上过不去,城七在不言语,悻悻推了出去。
隔着门,城七的忧虑传达不进去,缦舞的情况也不得而知,这让他的一颗心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即便在她的眼里从未有他,即便对她而言他永远只是“师兄”,他认了。只要她能平安,他便不再多有奢求。
不时,房门忽然打开,嬿婉擦着额上的汗走了出来。其实缦舞并不重,说她弱不禁风也不为过,只是陷入昏迷的人总会让人觉得死沉死沉,这不就是,嬿婉给她换下湿衣服,再换上一身干净的,费了好大的劲儿。
她侧开身给城七让了条道儿,“进去看看吧,这丫头烧得不轻,你先照顾着,我去找大夫来。”
“恩。”城七沉声应道。
有些事总是难免,无论如何躲避,终究狭路相逢。
就好像城七,看着轻寒同大夫一道踏进屋子,又能说什么呢?他承认,他的内心是自私的,即便缦舞烧成了这个样子,他还是不愿告知轻寒。
倘若缦舞能够将他视作值得依靠的男子,是否便不会再只是“师兄”这般简单?
大夫留下几句话和药方就匆匆离开。
——缦舞姑娘本就身子虚,今日心火渐旺,偏偏未得好生调养,劳累过度,再加上淋了雨,长期在体内积压的病症统统爆发了出来,所以才烧得这么严重。
——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家,怎么也不知道爱惜自个儿的身子呢。
——看这缦舞姑娘,身上该是带着儿时的伤病的,虽说面儿上确实已经痊愈,可仍是存着后遗症,要不悉心调理,恐怕总有一天是要出事的。
——缦舞姑娘岁数不大,可心火着实旺,恐怕是平日里操心的事情过多了,她这身子,不宜操劳过度。
——哎,怎么说呢,依老朽所见,缦舞姑娘习武本就是个天大的错误。
床头,桌边,门口,三人各怀心事,或颦眉忧悒,或焦虑难安,或面无波澜。
轻寒坐在桌边,举起手中茶盏轻抿一口,放到唇边才惊觉盏中早已空空如也。就变从容如他,也有如今这般不淡定的时候么。他苦笑这放下茶杯,转过头望向床上躺着的少女。
是否果真如大夫所说,自己这十年来所作的,归根结底是在害她。
他有些懊恼,不得不承认确实是他的疏忽,忽略了缦舞的状况。这几日她每日每夜地给自己煎药,照顾自己,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一刻才突然明白过来,自以为是的那人,一直都是自己。
只是,他当真没有料到,十年前的那次意外,会对缦舞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
她的腕子,她的身子骨,似乎都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而自己,过了这么多年都为曾关心留意。
沉默,在这师徒三人之间无止境地蔓延开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还是昏睡中缦舞的呓语将这几人从失神之中唤醒。
《凌烟乱》苏窨 ˇ往事恍入梦ˇ
幻梦之中,似实似虚,时间空间均不可考,缦舞只觉自己飘飘然到了一处熟悉却又想不起来的地方,几张面孔从眼前一一闪过,全然都是陌生人的样子,却叫她看得一阵揪心难忍。
时光错乱场景变换,这一回缦舞觉得自己的左手手腕隐隐发胀,抬眼看去,竟被一条粗重铁链拴于窗框。
耳边竟是漫无边际的哭喊、哀嚎,在她的眼前,一双年轻夫妇相继惨死于一群黑衣人之手,临死前,他们含泪的不甘的眼,直直望向她,她只觉得胸腔恍要撕裂的疼痛。
房里散乱地分布着不少人,除了手持刀剑奋力厮杀,可那几个黑衣人显然技艺更甚,并且仗着人多势众,毫不费力就将其余人等砍到在地。
放眼望去,满地刺目腥红,空气中弥散开的血腥味,足以让她干呕数回。
她想逃,挣扎许久,终是迫于锁链的束缚,无法逃离。
黑衣人这才留意到了床上被锁链桎梏的她,缓缓向她逼近。
她一味的向后躲,很快背脊一凉,回头一看,已经紧紧贴在墙上,退无可退。摇头,挣扎,哭喊
一切都无济于事。
画面在那群黑衣人狰狞的□面容前,逐渐变得缓慢而又模糊
“爹,娘,救我呜呜呜救我”
缦舞的梦呓将一旁师徒三人的思绪强行拉回,她躺在床榻上,嘴里不住地低喃,神色痛苦挣扎,却半分醒来的意思都未见得。
自从六岁那年被轻寒带回凌烟山庄,缦舞的身世一直是个谜。城七和嬿婉从来不向他们的师父询问这名女童的来历,只觉得必然不一般。
彼时初进凌烟山庄,昏迷不醒的小缦舞被轻寒抱在怀里,浑身的衣衫褴褛,露在外头的皮肤几乎难见一块肉色,青青紫紫的痕迹遍布全身。
特别是她的左手,苍白得不见一丝血色,手腕高高肿起,似是中间分离了一般,毫无质感。
也不知是何人所为,竟将这样一名无知幼童的左手生生打断!
缦舞被带回凌烟山庄之后,足足昏迷了十天之久,醒来时就连自己姓甚名谁都记不起来。
幸而轻寒私藏不少灵丹妙药,其中一味黑玉断续膏对筋骨错位有着奇效,未出三月,原以为此生都无法再抬起的缦舞的左手,竟奇迹般复原。
虽说也能如正常人般使用无碍,难免也落下病根,但逢阴雨连绵,她的腕子都会隐隐作痛。后每至梅雨,轻寒都会为其针灸,驱寒祛湿,方保她少受痛楚。
轻寒坐在桌前怔忡良久,回想起十年前领会缦舞那一日的景象,至今仍是唏嘘不已。
回忆如昨,恍似千年。
光阴尚且来不及从指缝间穿过,转眼,已是今朝光景。
是否将缦舞留在身边,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错误?
并非不了解缦舞心中所想,因他神伤,因他泪流,因他彷徨,因他受罪。只是如此果真值得么?
伤她至深,他哪里还能待她如初?
一声轻叹,转眼化作清风,消失无踪
十年朝夕,是否亦能如此清风,只当过眼云烟?
回忆可否忘却不得而知,凌烟山庄如今面临一大难题倒是实打实的。
那一头缦舞仍旧昏迷不醒,这一头以凤瑶为首的一众白道掌门人,纷纷向轻寒请辞,其间,或婉转其词,或缄默不语,或支支吾吾,大多没有说出突然离开的原因。
蹊跷。凌烟山庄众人本能地感觉此间不同寻常。
从那些个掌门人的闪烁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