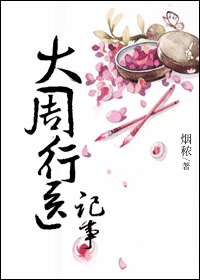大周主母-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百里一愣,不会儿圆圆胖胖的脸有种颓丧之色。没错,他当时是被季愉说服了,后来听她说自己是乐氏子孙,存了私心。他服输道:“先生所言极是。我等到此为追寻名乐器。与她交往并无错。”
司徒勋对他的话,却似乎已是没有去听了,眼光是放在了路尽头即将消失的季愉。忽然想起那首她一直念叨的《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裹。诗句固然悲,但诗中的女人是如此之美。他与她一样,一直是十分喜欢这首诗,对此念念不忘。
因此司徒勋对百里笑笑:“你所言也有道理,我是喜欢贵女季愉,因我喜欢诗歌,她也喜欢。”
百里目瞪口呆。司徒勋才不管他怎么想了,拍打一下他肩膊。掉身踏进门口时,抱起小申。想到她的话,他眉头微皱:她真是认得信申君?
话说,这边叔碧与季愉两人一路走一路说话儿。
“你猜司徒勋是从何处来?”叔碧问,对司徒勋外表长得不太像鲁国人介怀在心。
“不知。”季愉答,隐隐约约却能猜中,从他藏书里的神话故事,那个祝融的第六个儿子。如果回去再查一查相关书籍,或许马上就能知道答案了。不过,有必要去查他来历吗?绞眉,没有答案。
回到了驿站。阿慧在门口等候她们两人,见到她们便伏了下身,道:“贵女,信申君来访。”
叔碧正愣着神儿,季愉已是一个大步越过阿慧。
心,像是要从胸口里跳了出来。哗一下拉开门,季愉脸上潮红,气喘呼呼。里屋坐的两名男子闻声转过头来看她。
“贵女?”师况紧绷的脸在知道她进来时,似乎才松懈开。
季愉好像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一双眼睛愣愣地在信申脸上停驻。信申看见她的那刻,嘴角轻扬,温煦的笑如风一般立即吹掉了季愉心头的种种忧愁。季愉忽地别开脸,一只手捂住了胸口,里边突突突地跳着。
叔碧与阿慧从后面急匆匆跟来,见她扶着门边的样子,惊道:“何事?”紧接叔碧抢先一步扶住她的手,摸她手背煞是滚烫,更吓得叫了出来:“阿慧,取被子来!不,请医工——”
季愉反捏住她的手,摇摇头。叔碧是热锅上的蚂蚁,嘟哝:“病了请医工方是。”
信申这时起身。叔碧看到他走来才意识到他在这里,一下反倒怔了。季愉握着叔碧的手在打哆嗦。她猛一闭眼,为了甩去这不该有的感觉,咬咬牙。结果,一只温暖的大手在她额头轻轻触摸,伴随他温柔的声音:“不怕,是热,但我想并非重病。”
不怕。只道这温柔的二字已是如毒一般侵入她心里,比病更可怕。
为何?为何要对她说这么温柔的话?从没有人,这般温柔地对待她
“非重病?”叔碧找回了自己的嗓子,问。
“是。”信申转过头对她吩咐,“贵女,请嘱咐庖人备姜汤。我想病人应是疲惫而偶犯了风寒。”说完,他微微对叔碧一笑,是自信又鼓励的笑容。
叔碧觉得心安了。有他在这,绝对心安了。她笑着答好,带阿慧走去找驿站的寺人。
季愉可一点也不觉得好。叔碧一走,她连捏个手压制心跳的人都没有了。而且,那只手还被信申握住了。
“季愉,是名季愉,是不?”
他的声音,这一次低沉中带了丝严肃。
季愉睁开了眼,仍不敢抬头去看他。
他是轻轻捏住了她手心,道:“平士称在城门遇见你,我想在途中路室已见过你,知你必是到曲阜来了。来曲阜是为何事?可否与我说?”
原来他知道,确实,以他的智慧和眼力,她们那小小的偷窥怎可能瞒得住他。可让她感到既喜悦又惶恐的是,他惦记着她。
“找——医师大人。”在深吸口气震住了心悸后,她终于开口。
“医师大人?”信申轻轻念这几个字,是在琢磨,“何人病了?”
“乐离大夫。”季愉答完,立刻对着他欲下跪,“恳请信申君救主公一命!”
“季愉!”信申双手慌忙扶住她。
季愉想到乐芊,膝盖还是往地上落去。
“季愉!!”他加大了音量,似乎厉声疾呼。
季愉被他两只手的力气惊到,抬起了头。
他的脸上没有了笑容,而是肃穆的:“不要对我下跪!永远不要对我下跪!”
“可——”她是突然不明了,他这话是何意,是不愿意救,还是?
他将她扶了起来,并把她带到室内暖和的火炉旁边:“歇会儿,再慢慢说。”
她犹豫着,不敢坐下,始因她承担不起后果——失去乐离大夫后乐芊的后果。
这时候一直默默的师况帮腔了:“贵女,凡事不能急。”
因此季愉是忽然想起师况曾经与她说过的话,说她命运坎坷,有贵人相助能化险为夷。不知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但急于一时确实无济于事。她坐了下来,是恢复了些冷静。
叔碧与阿慧未归。信申拣起室内他带来的一件外衣,展开后披在她肩上。
季愉觉得不好,想把它拿开。信申按住她手,道:“听我话。”口气像是长辈,一个无法让人拒绝的长辈。她只好又依了他意思。
信申跪坐她旁边,问的是师况:“乐离大夫可是病了许久?”
“是。”师况实话实说,“大人应该略有所闻。”
“是有所闻。”信申没有否认自己的信息网,“有人言是病,有人言大夫是遭小人所害。”
“信申君又是如何以为?”季愉急急插话。
“无穴不成风。”信申说这话带了一丝嘘叹,“若是病,再遭毒害,我是无能为力。”
季愉的希望猛地落空,心一抽竟是有点儿疼,为了乐芊。只因她清楚,他这话不会假,他不是不救人,是能力不足。
“我非医工,更不是医师,仅是向某位大人略学医术。小病尚可诊治,若是疑难病症,我也必须求助于医师。”信申还是把话说清楚,将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他一点也不想她有误会于他。
“信申君可否代我求得医师大人?”她恳求询问,没有就此放弃。
然,信申仍摇摇头:“鲁国医师大人,为鲁国公红人。欲求他出诊,需鲁国公应允。我非鲁国人士,不应插手鲁国内国事。”
季愉从他话里听出了些信息,捉住了他的手,急切地问:“你是不是听说了世子进宫求国公何事?”
“季愉。”感觉她把自己的手捏地很紧,信申一向舒展的眉毛拧了起来,“请听我一言,我非听说了何事,不过我身份在鲁国境内实属尴尬。”
她望他的眼神,便是从热切慢慢地黯淡下来。
信申将她肩头滑落的外衣拉上,想拍拍她肩膀再安慰她,结果见到她把头几乎埋到了两个膝盖中间。她的这种落寞,忽然让他的心一疼。因自己无法帮到她
贰肆。童谣
信申在屋里坐了有片刻。叔碧与阿慧回来,端上姜汤。他看着季愉喝下了汤水,方才起身。
叔碧着急说:“信申君,您是要走了?”
“是。”信申面对她们略带严肃,道,“我此次前来,是为了告知两位贵女尽快离开曲阜。最好在今明两日之内。”
这话说得众人都仰起头,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他。
“为何?”叔碧心直口快,急忙道出心中疑问,“我等必须逗留于曲阜,直至完成使命为止。”
“可以暂时离开几日,再回来。”信申是以命令的口气说这些话。
叔碧皱皱眉,还想问清楚。旁边季愉拉住她袖子,缓缓地摇一摇头。
信申向她们两人含头,进而告辞。她们起身,欲送他至门口。走到一半路,叔碧转了下心思,放慢了脚步。因此只有季愉陪伴信申走到了驿站门口。
门前他的白色骏马好像认得她,小踏步走来,马鼻子朝她方向嗅嗅。信申一笑,用手抚摩坐骑鬃毛,对季愉说:“它喜欢你。”
被一匹马喜欢?季愉耸耸肩头,不予置评。不过,这匹马儿似乎与他感情相当的深厚
信申看出她的疑问,述说起:“曾经在战场上与它共过生死,犹如难兄难弟。”
“战场?”
“我乃燕国公家臣,数次奉天子之命随主公讨伐戎人。”信申描述起战场上的生杀,语气里透发出一股可怕的清冷,瞬间仿佛变成了另一人。
季愉仰望着他,想:无论他变成什么样的人,自己还是会喜欢上他。
信申在上马之前,对她说:“答应我,季愉。”
“哎?”她轻轻地应着,是他的话,她都是愿意听的。
“听我话,离开曲阜,越快越好。”他一再重申刚才的话,足以让她以为,若不是有公务,他或许会亲自带她离开此地。
因此她不会再问他为何。即使问了,他也不会告诉她。她只能是从他这话里体会到时间的紧迫。她于是顺从地应答他“好”,让他放心离开。可是,她没有办法按照他的话去做。乐离大夫的时日不多了,能不能拖到几日后都难说。百里所说的名医,是她们唯一的希望。他既然说了期限是今明两日之内离开,说明今晚还是安全的。她必须赌一赌今夜!
望着他与他的白色骏马缓慢地没入日暮中,季愉再次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为了以防万一,季愉要求叔碧留下,自己独自前往。
叔碧执意不肯:“去陌生人家中,不知会发生何事。”
季愉不让她:“正是如此,你必须在驿站待命。若我发生何事,你方能救我。”
叔碧知道自己是说不过她的,想偷偷跟踪她走。可是,百里这次来接她,用的是马。季愉抱着瑟,骑上马。马儿脚程飞快,不会儿便没了影子。
叔碧在原地跺脚,嘟嘴:“司徒若是斗胆骗人,我剥了他皮。”
阿慧安慰她:“贵女季愉所想均是深思熟虑之策,贵女尽可安心。”
叔碧气呼呼哼一声,返回屋内。阿慧笑着跟她后面走。唯有师况,站在原地,目送季愉远走的方向。许久许久之后,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据百里称,名医居所并无在城中,而是在近郊。
“吉夫人嫁予隐士后,两人远离尘世,隐居在曲阜内,鲜少人知晓。”百里一边让马儿小步跑,一边对季愉说。
季愉没有问他为何他能知道这鲜少人才知道的事情。他尽可编造谎言来遮盖自己的来历。况且,她的目的不是要知道他和司徒勋是什么人。为此,她只是问:“吉夫人对接诊可有要求?”
“吉夫人心肠仁厚,只要是病人,一律鼎力相助,不收取报酬。”百里把话咬得很死,像是在用性命保证季愉这次绝不会空手而归。
季愉暗暗地想:他们之前必是与吉夫人沟通过了,才敢允下如此重诺。至于他们是如何与吉夫人沟通,季愉甚至可以猜测:若不是以钱财诱惑,或许是以权力,或许是晓之于理动之以情?若是如此,司徒勋果真是贤者之类的大人物呢
有她在马上,百里不敢将马速放快。马儿抵达居所时,已是夜里了。有寺人在门口迎接。百里将她交给寺人,自己并不入内,只称:“明早我会来接贵女回去。”
季愉也想:乐离大夫的病不是普通医工能治,与吉夫人不止要交谈,要交心方可解决问题。她向百里点头,随举火炬的寺人进入宅中。
吉夫人与隐士两夫妇道是隐居,置于这山脚下的家宅却是宏大。季愉尾随寺人在宅内行走,夜深风高,看不清宅邸全貌,但可感受到曲径幽深,院落一层层向内推进,怕是这里寻常也有上百号人居住生活。
来到一居室门前,寺人向门内主人禀报:“夫人,访客已经带到。”
门里传出的先是小孩的啼哭声,紧接一个温婉的女子声音说:“快请贵女入来。”
寺人爬上台阶,拉开门。季愉双手捧瑟,以恭敬的步态进入居室。
里边,室内火炉旺烧,四处垂有挡风的帷幔,是由于有个刚出世不到周岁的孩子,身体孱弱不能受风。
吉夫人将襁褓交给照顾的食母,仔细嘱托:“世子不可喂食太多。”
食母抱着婴孩恭谨退到仅相隔一扇门的邻室。
吉夫人转回身,笑吟吟走到仍跪在地上的季愉,双手亲自扶起:“请起吧,贵女,您是贵客,如此大礼我承受不起。”
季愉抬头,见眼前的贵妇或许是生完孩子不是很长时间,身材较为丰满,脸稍圆,然一脸亲切的微笑似乎在告诉她:你我已是亲近之人。季愉便起身,在客座的蒲席上跪坐下来。
“汝之事百里已有告知于我,我略有所闻。但事情详细,还是由贵女细言。”吉夫人在寺人端上茶后,将底下的人全部遣退出室外。寺人离开时,放落四边帷幔,好像一个大布包将居室包裹起来,没有人能听见或是看见她们两人在中间说什么做什么。
仅观察这些训练有素的寺人,季愉知道了百里所言非假。这位吉夫人,必是在宫中呆过,深知事情轻重,有处境不乱、游刃有余之风。安心后,她向吉夫人全盘托出:“我家主公患之乃上气疾,久病不愈,又不幸遭小人陷害。”说罢,她拆开膝盖上的包布,露出里边一张瑟。
吉夫人见到瑟第一眼,不由叹道:“此瑟看似平凡之物,又不似平凡之物。”
季愉微微地笑,不着急回答她,把一只手伸到瑟的底部,摁下机关。她再把手挪出来时,掌心上已是搁置了一个四方形的铜铸盒子。
吉夫人从她掌心接过小盒,轻轻打开盒盖,里面刹那散发出一股寒气。原来盒内是塞满了大量的冰块,加上密不透风的铜壁,令冰冻的寒气捆锁在盒子内部。此方精心作为,为的是使冰块中间保存的物体不会发生腐烂。吉夫人用指头拨开冰,暴露出的是一小块冰霜的牛肉片。
季愉在旁解说:“此乃乐芊夫人艰辛追寻之下,唯一可取到的证物。”
“不知何人下毒?”吉夫人问。若是知道谁下的毒,再逼问出是什么毒药,对症下药,一切不是问题。最怕是,一直都不能知道是什么毒。
季愉摇摇头:“幕后之人诡计多端。宅内寺人众多,出入乐宅之人也多。乐芊夫人忧心打草惊蛇,无从查起。”
吉夫人从季愉一句话,便洞察出这下毒之人恐怕关系到乐邑主公膝下的几个孩子。因此,把下毒人捉出来,又能怎样呢?管理乐宅的女君或是宗长,都绝不会答应处置这些有继承身份的子孙,唯恐的是引起整个乐氏的动乱。为今之计,只能把主公的病医好,让主公重持大局,重新安排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