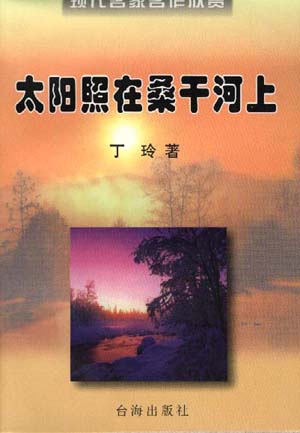书至河上-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脖子、后背以及小腿上都被野狗咬了,很痛,痛得寸步难行,但包袱里有金疮药,她不怕。好容易走到盘子前,伏身去端,却感到一个人站在了她面前。
依旧白衣淡然、面具华丽的孙茯苓。
白天刚同他吵过架,此时她纵然心有余悸,可也不打算求他怎样。
徐荷书视若无睹,径自端着盘子向屋里哭泣的白花走去。
孙茯苓忽然道:“真白。”
什么真白?故弄玄虚?徐荷书不理他。
“你背上的肌肤真白。”
徐荷书一听,头都炸了,快步走进了屋里。刚才和几只野狗那样厮斗,衣服岂有不破之理?孙茯苓竟然走了进来。真不知廉耻。
在幽暗里,徐荷书镇定地喂白花喝汤。
孙茯苓道:“这又不是你的孩子,你如此”
“也不是你的孩子,你有何资格多嘴。”话很尖刻,可她声音却因激动未已而有些虚弱。
孙茯苓笑道:“难道,你就不怕那野狗有病,传染到你身上?”
徐荷书心中一动。
“对不起,我来晚了。现在请回到寒舍,让我为你诊治。”
咄咄怪事,傲慢的神医竟然这样低声下气起来?徐荷书不便、不愿也不敢再逞强:“多谢。”
徐荷书的老屋之夜终究是半途而废,她和白花一起被“请”到了孙茯苓的住处。
那间茅屋内的三个病人没有嚎叫,不知又被孙茯苓用了什么手段。
徐荷书自己给伤口敷了药。背上的伤口只好交给神医本人。然后,她披上了斗篷。白花躺在竹榻上睡着了。
“他是方爱的孩子”孙茯苓悠悠地道,“方爱和那个男人的孩子。”
徐荷书抬起了眼睛看着他。她的猜测,果然差不多对了么?
安静的夏夜。外面凉风习习,树影婆娑。是个适合讲故事的时间。于是,孙茯苓也真的讲起了他的故事。
两年前,在汉水之上,方爱于舟中弹琴,恰好被附近的孙茯苓听见。那时候,孙茯苓喜欢游历行医,他听见那琴声,顿时就感到魂魄渺远不知所之。他也是爱琴且擅琴之人,虽然并未想过要寻觅一个知音,但听到那琴声,他立即就了解了那其中无边的寂寥、淡淡的哀怨。循着琴声,他找到了那个琴艺非凡且容颜绝俗的弹琴人。
尽管她的性子是冷的,态度是傲的,孙茯苓也用自己的才华和温情打动了她。他们很快相爱。那时候,他收敛着自己的傲气,而用男人对女人的爱怜包容着她的骄傲,聆听着她的琴,她的心。
后来,大河盟的盟主何大梦不知如何得知了方爱的艳名,便发动部下去寻她。方爱与孙茯苓正在各地漫游,得知此讯,便只有逃。逃的过程并不狼狈,也没遇到什么危险,但是他们的心情却产生了一点变化。有时候,心高气傲的孙茯苓受不了方爱的冷若冰霜,有时候,冷若冰霜的方爱受不了孙茯苓的心高气傲。总之,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世界应该受到对方多一点的温存和俯就。
很不巧,这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风流倜傥不逊色于孙茯苓的男子,薛湖。薛湖爱慕方爱,完全无视她身边男人的存在,大胆而热烈地追求她。方爱一贯地冷淡,却并不对他厉色冷语。渐渐地,他讨到了她的欢心。她对他笑,对他撒娇,弹琴给他听孙茯苓急了、气了、怒了。
终于有一次,薛湖志得意满地告诉他,方爱有了身孕。孙茯苓这下是怒极!怒不可遏,怒火中烧。他并不是丝毫没有想到她怀的是他的孩子,但看到薛湖得意的表情,以及方爱平静的态度,他就已经确定,方爱已经是薛湖的人,怀了薛湖的孩子!
他简直痛不欲生。于是拂袖而去。
“你真的要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然后,方爱不再说什么,只漠漠地弹着琴,好像是在祝他一路顺风。
孙茯苓失魂落魄地回到了茯苓村,一年多以来不曾离开村子一步。有时候,他会哀哀地想,那女人已经生下孩子了吧,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她会比和他在一起时更快乐?他也努力不让自己想她,不让自己记恨,不让自己关心——他是举世无双的神医孙茯苓,爱医擅医,为世人尊敬和崇拜,怎会因为一个女人失了拿得起放得下的气度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
岂知刻意要达成的境界,事实上你常会离它越来越远,甚至和它背道而驰。
徐荷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恨屋及乌。这就是你对我也不客气的原因吧?”
“这个孩子,长得真像她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叫‘白花’,为什么会姓白?为什么你带着他,而不是方爱或者那个姓薛的?”
徐荷书道:“我与方爱,也不过是一面之缘。她现在应该在大河盟中,做了何大梦的妾。方爱的祖父告诉我这孩子姓白,至于为什么,我也不得而知。老人家已经去世,我是临终受托,五个月后,应该就可以把白花还给方爱了。”
孙茯苓声音冷峻地自言自语:“她,毕竟还是被何大梦迫嫁了那么薛湖呢,为什么不救她?”
但徐荷书有自己的怀疑:“你真的认为方爱是用情不专的人吗?”
“事实如此,不在我怎么认为。”
“可是,我却认为她不是这样的人。”徐荷书只是凭着感觉,至于理由她是说不出来的,“可是,你真的能够对她忘怀吗,你还是很关心她现在的处境对不对?”
“哼,我忘不了、很关心又如何,她现在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虽然被迫顺从了,但一定会与何大梦作对。其实,我很担心五个月后她能否获得自由身,与我见面。”
“自由身”孙茯苓好似出了神,“那又与我何干,不应该是薛湖去解救他的女人吗。”
“咳,你真是入了魔障,如果白花真是那薛湖的孩子,为什么方爱没有让他姓薛呢。而且,薛湖也不知去向,他会毫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吗?”
“哼,薛湖也许是惧怕大河盟的势力,自己保命要紧逃之夭夭了。”
徐荷书于是不知再该说什么。在她现在看来,这个孙茯苓与方爱真的是很般配的一对,闹到今天这步田地,其中款曲,当局者恐怕已迷,外人更是难以了然。
这孙茯苓,今日来来去去,不过是想知道白花的来历。想知道却又抛不下面子追问。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实在是莫名其妙地就会很累很伤。再加上方爱自己也很奇怪——孩子居然姓白——他们两人长久相处,恐怕既无法默契,也无法理论。
孙茯苓因爱而生的忌讳,也折磨了他自己。由此,徐荷书想到她自己——带着白花这么个小孩子,颠簸了千百里,只是为了要回自己离开了十多年的荆州老家一趟,且并无要紧事?父亲一养好了病,他们全家就会一起回荆州,她何必今次非要到达?在本县的时候,她为何要执意离开——不是因为要去荆州,而是因为她要离开那个有谢未与苑桃的地方。
正文 第三十八章 俱为北上
更新时间:2010…10…15 10:54:40 本章字数:3752
月亮终于升起来了。徐荷书透过窗纱望见这一轮皎洁而寂寞的月,感觉着身外陌生的此地气息,一时之间,几乎忘了自己身在何处。真是奇妙
她与白花睡在竹榻上,而孙茯苓睡在竹帘后的一张床上。相距不过是这道帘子的距离。之前,他是对她说:“我知道你是要杀李有理。明天我就放他走,离开我这里之后,你请自便。”然而一夜有风——
因为一夜有风,致使他们都睡得很好,致使天亮后才发现李有理等三人已经不见了。逃走了。他们逃走,不见得是李有理知道这里有个人想要杀他,而是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承受神医的“诊治”,再“治”下去,治不治得好且不说,他们会疼死。
于是三个人乘着这个有风的夜晚,连摸带爬地溜出了“病房”。李有理本打算临走前给这个神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下,却被明智的同伙阻拦了。害人虽然很有必要,但一定要建立在自己性命能够保全的基础上。
其实,来向孙茯苓求医的人虽多,他接诊的却少,很多人还没来到他的屋子,便被他拒之门外:“请移驾邻村陈大夫家,他可以治你的病。”
病人愣了:“难道孙神医不能治吗?”
“我不想治。”他的回答很自傲。
陈大夫不但钦佩孙茯苓的医术,还很明白孙茯苓此举的用心,于是感激他。
现在三个没付诊费的病人逃走了孙茯苓有些愣,却并不惊讶。明知病情尚未痊愈,病人却私自离开病房,那么大夫就不必担负任何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徐荷书却抱着白花,策马追寻而去。他们走不远,一定能追得到。
三个白天还在痛嚎的伤病之人在夜间就行动自理,靠的一定不是体力,而是意志和脑子。所以,他们不可能在大道上狂奔,而是在野地里摸爬滚打先躲藏然后再路等交通工具的到来。所以,徐荷书在附近寻找、追了很久也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
骑着马,她无奈地在一条小道上打着转。如果她是求生者,那么她也会逃得令追击者不得要领无法找到。因而她想起了捕快谢未。倘若有他在这里,罪犯一定不会逃脱最终落网。倘若有他在这里那么她会不会还在这里?
白花在她怀里挣着要下地。于是她下了马,在这片野草猖獗、野花缤纷的草地上暂作停留。白花兴奋滴颤巍巍走了几步,便跌倒了,然后爬着,去抓那些黄色紫色红色的小花。徐荷书微笑地看着他,黄花灿烂,紫花雅致,红花艳丽“白”花可爱。白花,白的花。白衣,白的衣。
——孙茯苓白衣的白可同白花的白一致?
不远处有水牛在小湖边吃草,却不见牧人。一只白色的鸟在湖上盘旋不去。一片辽阔,直到远得烟雾缭绕的地方,而烟雾里隐隐有一道绵延起伏的青山。
京城没有这样的地方。而这里离荆州老家已经没几天路程了。荆州一定也很美。在她残存的记忆中,也确然如此。
那白鸟忽然一阵急拍翅膀,飞向了远处。紧接着,传来了马车的辘辘声。
在飞扬起来的车窗帘后,她看到那是一角白衣。侧脸影影绰绰。是孙茯苓。而马车是向北而行。
徐荷书笑了。孙茯苓对方爱的处境终究不能安之若素,要去找她、帮她、救她。
“喂——”她大声喊着朝马车摇摇手。过了一会,马车停了,窗帘掀开,露出了孙茯苓那已然戴上面具的脸,看着她。徐荷书带上白花骑马奔去。
“孙神医这么好的闲情逸致,出来郊游啊?”
孙茯苓点点头:“对,郊游。”
徐荷书笑道:“我倒知道一个好地方,山水壮丽,殿堂神秘,要不要介绍给你?”
“请讲。”孙茯苓摸了摸面具的鼻梁。
“河南境内,黄河之畔。”
孙茯苓随即笑道:“原来是那里。徐姑娘可愿与我同去?”他当然知道徐荷书是要西往荆州。
“我嘛,才从彼处来,不想又回去不像有的人,去那里会遇见故人。”
孙茯苓有心调侃回去:“莫非那里有姑娘不想遇见的‘故人’?”“故人”二字语气尤其奇怪。
徐荷书瞪了他一眼,哼了一声:“非也。那里也有我想见的故人。”说这话的时候,她心里想的是张长长、费施、赵小会、厉宁、王素、念儿,甚至是闲闲一家人。
“徐姑娘,说真的,我需要你的帮助。”孙茯苓下了马车,站在她的面前,忽然认真起来,“我要去找她,带她离开大河盟。而你和她又有四个月后的约会,你带着她的孩子反正是一路游历、颠簸,向来路回去也无妨吧?”
徐荷书低下了头。
的确无妨。而且她早已开始想家了,有时候,她的确考虑了要不要回家去。
——回去,不见谢未就是。
——就算见了,也大可以心无芥蒂、一笑而过。
——何况,也不一定见得到他。
——果真见不到吗
而且,李有理逃走,很有可能是逃回他的老巢邻县了。忽然想起一件事,徐荷书便来了精神,想借机捞点好处:“孙神医,要我一同去也容易。只要你揭开面具,让我一睹神秘的尊容”
孙茯苓昂首无语对苍天。
“白花,想不想把这花里胡哨的玩意拿下来玩”徐荷书故意逗白花。
孙茯苓很似寂寞地说道:“其实,我只在女人面前才戴面具”
“哈哈哈”徐荷书大笑起来,“这么说,你、你真的是潘安再世宋玉投胎了,若以真面目示人,会祸害”
孙茯苓咳道:“这,这很可笑吗?”
“可笑,又可怜!快点,让我和白花都瞻仰一下你惊人的美貌!”
孙茯苓背过身去,摘下了面具。
再转回身的时候,平野上恰有一阵清风吹过,一绺发丝斜斜地拂在他脸上。眼是冷意的,嘴是冷意的,如削的下巴却像在诉说热情。凝然伫立于此,宛如风中玉树。
徐荷书脸红了。她想起自己的弟弟徐松诗,本以为已是少有的美男子,现在想来,他不过还是个孩子。“果然”她讷讷地说着,“面具是必要的。你还是戴上吧。”
孙茯苓的美貌,倒不是让她如一般女子那样迷恋歆慕,而是给她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孙茯苓洒然一笑,重新将面具戴上。白花不依地叫了一声,他一直伸着手想要那面具玩,却没人理他。徐荷书忽然想到这面具的妙用——除了遮盖美貌避免惹起不必要的麻烦,当初也一定吸引了方爱的好奇心,待到见到他的真面目,应是芳心已折。
接下来的情况是,徐荷书把白花放进马车和孙茯苓呆在一起。她实在是太思念一个人快意纵马的感觉了。
在马车里,白花望着孙茯苓脸上的面具,笑笑,然后伸手去抓。孙茯苓便卸下来给他玩。白花摆弄着这个奇怪的玩具,一会是摔,一会是啃,又往他身上拍打。孙茯苓任他打。白花打得起劲且未受阻挠,便抬起脸望着他嘻嘻地笑。孙茯苓很给面子,好容易挤出了一丝笑意。方爱的孩子——不是他的孩子——但毕竟是方爱的孩子——但终究不是他的孩子,再想,便成了联想、幻想,于是一颗心由于愤恨、嫉妒、悲哀而如在煎熬,反复不定。
远山依然朦胧。徐荷书策马疾驰,远远地跑在了前面,而在风中的偶一回望,那么纯粹地喜悦着,令人心中顿时充满美好的向往。虽然,并没有谁能够看到她这样子。虽然,她唯一可能的观众是那位沉默不言、鬓发花白的老车夫。
徐荷书北上,有同行者;谢未北上,却是孤身一人。他其实是把徐荷书从家出发的这条路走了一遍。在这路上,他常常会想着她,想着她在经过此处时的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