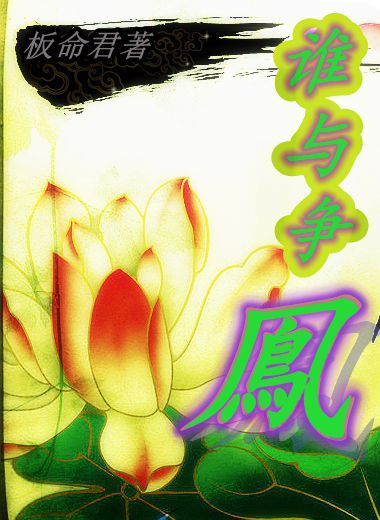谁与争疯-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感动就感动,我要见他。”
“帮不了你,幽禁期间,谁都不能见。”他别过头,不去看她固执的眼。
可惜阻挡不了那些固执的话语钻入耳中,“那你能不能帮我去跟皇上说,我不要那个什么免死金牌了,我要见他。”
“姚荡!你能不能有出息一点!”为了个连当众哄骗她几句都不屑男人,她竟然蠢到把那道保命符往外丢?
“我就是没用没出息,除了患难与共,我做不来任何事了!我要见他!”
“再等几天。”他眼眸一闭,承认自己拿她没辙了。
是个傻瓜,还以为她够冷静够清醒,懂得明哲保身。说怕她坏事、说要娶她六姐,何尝不是想把这个女人推到是非之外,她和他们毕竟是不同的,没有争权之心,更不会懂这种在只字片语间毁人于无形的生活。
结果,她倒好,领不了情,还一头热地往里栽。
第三十七章
任是谁都没料到,事态会在瞬息之间发生那么大的转变。
太子是真的打算娶姚家六小姐了,皇上亲口允了这桩婚事,街头巷尾都在说姚家女儿生得好,随便挑个都懂得如何见风使舵,让整个家族地位扶摇直上。位极人臣算什么?国舅爷加上往后国丈爷的身份,那才叫一时无两,赢得漂亮。
吉祥赌坊也是真的被封了,那两张惨白工整的封条赫然出现在门板上,往日辉煌荡然无存。听说重要的人一个都没抓到,只收押了一批无关紧要的小喽喽。
至于苏步钦
原先以为毕竟是皇子,何况还有皇上的愧疚在,即便是幽禁至少也好吃好睡,最多不能随意出门罢了,而他原本也就不太爱出门同人打交道。
可眼前景象分明是另一幅光景。
一抹橙红色的身影穿过花瓶门洞,颇为诧异地微张着唇静看着面前的那栋院子,不再有人费心去打理那些奇珍异草,枯黄落叶积了一地,踩在上头都能明显感觉到地儿是松软的,倒是满园的桂花香飘不败,闻起来有丝凄凉的味道。
所有侍卫都被撤了,连旦旦都不见了,只有零星几个丫鬟在偌大的宅子里插科打诨。被拨来照顾一个已经失势的皇子,自然是没必要像佛似的供着他,那扇紧闭的房门,几乎没人会去主动推开。
她手里正端着的那份比阳春面还简单的面食、几碟没什么油水的配菜,是苏步钦的晚膳。不清楚一个厌食的人,这些天是怎么咽下这玩意的。
想着她吸了吸鼻子,压抑下忐忑,正打算叩门,身旁传来了一名丫鬟狐疑的询问声,“咦?你是哪来的?生面孔啊。”
“是太子让我来的。”她微微偏过身子,回给对方一道浅笑,随后便从腰间掏出块刻有太子金印的红玉牌子,递给守门的丫鬟。
对方接过后只随意扫了眼,又递还给了她,“进去吧,那个半死不活的病鬼可饿不起。”
“嗯。”她应了声,没再多说话,兀自抬手推开房门,跨了进去。
细微的交谈声还是穿过门板,钻入苏步钦的耳膜,这显然不是个普通丫鬟。他紧了紧神,凝眸看向逐渐被推开的房门,当招摇的橙红色跃入眼眶后,他屏息,很清楚自己在期待什么。
然而,看清来人后,他的期待也随之落了空,“你来这做什么?”
冷淑雨,这是个他万万想不到会在这种时候出现在这儿的人。
“来看你死了没。”他脸上的失望之色未加掩饰,全数飘进了淑雨眼中,想要装作视而不见都难。她难掩微冲的口气,将手中餐盘重重摔在桌上后,不甘地又补上一句,“我做不到像十三荡那样没心没肺,你出了那么大的事,她都可以坐视不理,我可按捺不住。”
姚荡是怎样的人,苏步钦清楚得很,不需要旁人来指点。如果真是没心没肺,还会有那晚的不欢而散吗?他纵然可以料到那道免死金牌横空出世后,会有人坐不住;但料不准她会在这当口把话挑明。
他没有机会去为自己的口是心非做弥补,又凭什么去奢望她一如当初,“她还好吗?”
沉默了那么久,就迸出这么一句话?淑雨气得涨红了脸,不知究竟是该哀其不幸还是怒其不争,“苏步钦!她再怎么也不会比你差!她就算是把天给捅破了,都有姚四爷替她兜着,你有这闲工夫担心她,还不如想想怎么翻身。”
“哦?你有好的建议?”他收敛游走的心绪,抿唇似笑非笑地问道,静候她的下文。想来,这女人绝不会是为了看他活得好不好而来的。
“皇上说了,你若肯娶我乖乖听他安排,他自有法子扭转局势”
他支着颔,不动声色,未觉意外,不发一言地聆听着冷淑雨那番据说是在救他的说辞。那个老头子还是这样吗?总觉得无论谁的生死都该交由他来掌控,即便是自己的儿子也可以毫不留情,想要苏家天下连绵不断,就必须有所割舍。
是该庆幸风水轮流转,现在的他不再是被割舍掉的那一个,而是被选中的傀儡。可惜,他庆幸不起来,做不到去为百年之后的事深谋远虑。半晌,他溢出寡淡凉笑,冷嗤,“嘁,冷姑娘何必特地跑来游说,你们有给我其他选择吗?”
﹡
所谓的“再等几天”究竟是什么概念?最终,太子将它视作了一句戏言。
对他而言,要让姚荡去一趟钦云府并非难事,在她的坚持之下,有那么一刹那他确实心软了。不过是举手之劳成全了她,有何不可?然而
——无毒不丈夫。若今日沦为阶下囚的人是你,苏步钦会心软吗?会善待在意你的人吗?他只会杀无赦。
姚大人的一句话,警醒了他所有的防备。
的确,以苏步钦这般蓄势而出的个性,他会斩草除根,不给敌人丝毫反击的机会,甚至可能会让人死得不明不白。
他收敛住不该有的心软,听从姚大人的安排,顺势将姚荡软禁在他宫外的别院里,不让她坏事闯祸,还要佯装不知情,眼看着姚四爷动用所有人手满城寻找十三荡的下落。要说全然掩藏着天衣无缝,那是不可能的,他的演技远不及苏步钦。
直到姚寅像是死心了,忽然带着商队离开了琉阳,他才松了口气。
可惜很快他就发现这口气松得太早,相较于姚大人,姚家四爷的敏锐度更高,他无预警的离开,预示着一切并未结束,才刚开始。
“太、子、殿、下!!”
中气十足又怨气冲天的叫喊声自他身前飘来。
太子嘴角一抽,不用抬头也能猜到跟前站着谁,不过才刚跨进别院,就被姚荡逮个正着,这女人该不会每天守在门口就等他自投罗网吧?
“你终于出现了!我还以为你说过的话就跟放屁似的呢!”姚荡气势汹汹地冲上前,一扫这些日的郁结,强装出从前那副天塌了就能笑开怀的模样,只可惜,嘴角笑意涩得很。
“怎么可能?爷是君子,一诺千金!”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她那种如夏花般明艳的笑容下,彷佛所有尔虞我诈都不复存在。也只有姚荡能这样,分明所有阴谋都已摊放在了台面上,她可以视而不见。依旧像个朋友般,同他打打闹闹。
如果,生活真能平凡如斯多好,和朋友一起喝酒赌钱,不需要去想那些太沉重太远大的事。
“是吗?”她狐疑挑眉,龇着牙,装作没看懂他脸上稍纵即逝唏嘘,“那是不是都安排好了?这就可以带我去钦云府了?”
“嗯”他应了声,很轻。
姚荡察觉到一丝不对劲,没多问,怕又生变,只顾急匆匆地往外走。
记不清这些天她是怎么过的了,用“度日如年”来形容恰如其分。就像被软禁般,去到哪里都有人跟着。伙食不错、被褥够软、老虎头鲜少出现、一切平静,日子在旁人眼里是逍遥快乐,只是所有人在她面前都对姚家和苏步钦的事三缄其口。
她开始懂得,原来是否开心,并不取决于物质,倘若心里牵念的事太多,连笑容都很难纯粹。
“姚荡。”相较于她的迫不及待,太子一动不动地立在原地,双唇翕张了许久,才飘出浅唤。
“嗯?”她停住脚步,却不敢回头,他过于沉重的口吻激得她心头惊颤。
“兴许钦云府很快就能解禁了。”
“他没事了?”她重重地吁出口气,僵硬的背脊瞬间软化,睁大双眸旋过身。
“也许吧。”苏步钦是不是没事了,他还没收到消息,但可以确定的是“有事的是你家。”
“什么意思?!”她爹不应该是最大的赢家才对吗?有众多官员拥虿,还有皇上的言听计从,能出什么事?
太子没有回话,倘若只是轻飘飘讲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恐怕姚荡也听不明白。他索性从怀中掏出封探子送来的信件,示意她自己看。
那满纸的官话入了姚荡的眼,只有茫然,她废了好一番功夫,才把那些话解读完全,“他娘的这算是什么狗屁东西啊!压根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恐怕没有人在面对自己爹的无数罪名后,还能维持住冷静。何况是姚荡这般直来直往的性子,素养家教被她全数抛到了脑后,一溜的脏话不加粉饰地从她丰润的唇间钻出,与颇为悦耳的嗓音极不协调。
尽管如此,她仍是没觉得事情有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还固执地挤出干笑,近乎语无伦次地用滔滔不绝来掩盖脑中的那团乱麻,“什么叫‘家藏大珠,胜于御用冠顶’?家里有颗珍珠比皇上脑袋上的还大,也算罪?那采珠人岂不是死一万次都不够!还有还有,管理吏部和兵部,任人唯亲这又不是我爹抢来的官,是你父皇硬赏给他的啊!谁定的罪?那么荒唐屁竟然都放得出?!”
用荒唐来形容这一纸数不清的罪状完全不为过。
然而这看似鸡毛蒜皮的罪名,真的会用不痛不痒的方法了结吗?太子苦笑,撇了撇嘴,“父皇忽然召回了卫大人,他参的奏折。”
卫大人?是卫夫人的夫君吗?在姚荡的印象中,姚家和卫家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自为官的,“我们家又没欠他,他发什么癫?拿我爹寻乐子?”
“姚荡,这不是寻乐子,这是贪赃枉法的罪,如果父皇定了,会被抄家。”事实上,姚家还有幸免的可能吗?他叹了声,自小受的教育让他太过了解为君之道了,这些罪名显然不会是卫大人擅自为之,也只有在父皇属意的情况下,才会拟出这种当诛却又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的奏折。
抄家这两个字如同一道晴空霹雳,不偏不倚地打中姚荡,让她白了脸色,心间一空。
来不及让混乱的思绪有理清的机会,她的身子已经做出本能反应,拔腿就往外跑。幸是被太子及时拉住,可她的力道让他有些措手不及,比起上回听闻苏步钦出事时的执拗,这一回她就像是疯了般,让他一不小心就被挣了开来,只能招呼一旁的护卫一同出手去拦。
“要去哪?”她那股不知打哪来的蛮力,惹得场面一团糟,太子逮到空隙,好不容易才挤出了声音。
“回家!”倒是姚荡仍然气息平稳得惊人。
“别发疯!父皇还没定罪呢,你就算现在回姚府也无济于事。去钦云府,想帮你爹就去钦云府找苏步钦,这事一定和他有关”
这话就像魔咒般,让姚荡忽而冷静了下来,停止了挣扎,“怎么可能?他不是被幽禁了吗?不是任何都不能踏入钦云府吗?他哪有可能联合卫大人弹劾我爹。你怎么不说是你人心不足蛇吞象,反咬我爹一口,那才更可信!”
“你能不能别那么天真,我和你爹是一条船上的人,他出事了,我也逃不了,我有什么理由害自己?冷淑雨去过钦云府,转达了父皇的意思,只要苏步钦愿意娶她,谋反的罪就能洗去。这种能让自己翻身的好事,他有可能会拒绝吗?”
“”这话很有说服力,让姚荡找不到论据去反驳。的确像是皇上做出来的事,就像之前他没有选六姐而是让淑雨和太子订亲一样,皇上从来就没想让姚家做大,他需要的制衡。
“民风富足天下太平了,功高盖主的人父皇是不会留的,冷丞相比你爹听话。”他无奈在最后关头才看明白这道理,而偏偏有人早就懂了。在苏步钦小心翼翼傍着冷家的时候,他却傻乎乎地避之不及,只看见那些表面的光鲜,还以为自己运筹帷幄。
呵,要说君临天下的能耐,他显然比不上那只处心积虑的兔子。那好,愿赌服输,他只是不想死得太难看。连姚家都落败了,乱了阵脚的太子唯能把姚荡视作最后的救命稻草,“去找他,也许他能看在你的份上劝父皇息事宁人。”
“娘的!那你倒是让他们放开我啊!”姚荡是没有把握的,她不清楚在苏步钦心里自己究竟是一枚棋子还是一枚稍微有些感情的棋子,可如果这是唯一能帮爹的方法,她愿意腆着脸去求他。
但连太子都没料到,这一回父皇的动作要比幽禁苏步钦时更迅速。
他才刚命令禁锢住姚荡的那些护卫松手,一队人马就浩浩荡荡地闯了进来,从他们的打扮和井然有序的阵仗看来,是宫里的人。
领头的人像是也没想到太子的别院会那么热闹,他的目光环顾了圈后,落在了姚荡身上,颇觉好笑地哼了声,“这不是姚姑娘吗?难怪我那几个去抄姚家的同僚说搜遍整栋姚府和姚寅的别院,都不见你的身影,还以为你同姚寅一块潜逃了呢,原来是在太子这儿呀。”
这阴啧啧的话,让姚荡徘徊在了喜忧之间。诚如太子所言,姚家还是被抄了吗?“还以为你同姚寅一块潜逃了”,这话是不是代表四哥幸免于难了?
“来人呐,把姚荡带走。”这是皇上特地叮嘱一定要找到的人,眼看着功劳在前,没人会错失。
“不准!她是爷的人!”
即使太子这声负隅顽抗般的阻拦只是想保住她,让她有机会去找苏步钦,仍是让姚荡眼眶一热。她愈发觉得人与人之间,果然是没有信任可言的,只有利益才能维系住。可就算是利用,如老虎头这般的,起码还有未泯的人性在。
“太子殿下,卑职劝您还是先顾好自己吧,皇上请您即刻进宫,姚家的事儿您还是别再插手了,免得被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