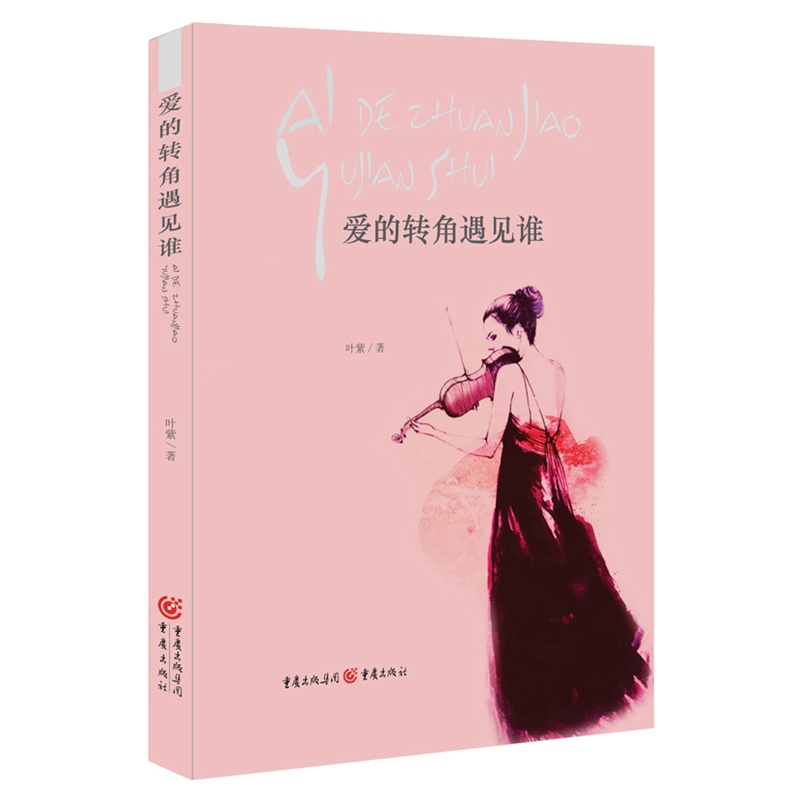遇见春夏秋冬-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斜眼看去,那个声音的出处不是别人,正是那徐建!
蹭亮的光头仿佛灯泡一般,照得人无法直视。
徐建又开腔了:“老师,SB这个词有很深厚的含义,您还是原谅他吧”。
“你”!我瞪了徐建一眼,“你”了半天,也接不出什么有意义的单词。
全班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笑声。中国人特有的笑声。
淑君老师也跟着笑了,仿佛看够了戏,手指一挥,一股难以察觉的笑容爬上了她外焦里焦的脸:“好了!去吧,下次注意点”。
我撇了淑君老师一眼,连法国人挂嘴边的“Merci(谢谢)”也未说,便迈开腿往桌位走去。可未等我走到座位,那尖锐而刺耳的声音又再次传来:“SB生气了”。
班上淅淅沥沥的笑声,忽然安静下来。
我停住脚步道:“够了!别再唧唧歪歪!我智商很高的。”
徐建嗤笑了声,又面带笑容转向前去,“SB”,嘴里再次骂到。
我缓缓走到桌边。突然,一种不知名的力量涌上我的身体。我盯着徐建片刻,提高了嗓门大声吼道:“草泥马啊!SB够了没有!神经病”!
徐建脸上的笑容凝固了,迟疑了一秒,转过头不屑地加大嗓门:“SB就是SB”。
我一手抓起了书本,朝他猛地甩去。兴许是没吃早饭的原因,书没有飞多远,可徐建却“啪”一声拍了桌子,迈出几步,已经到了我跟前。他面色潮红,未言一词,拳头便直接挥来。
瞬间,尖叫声,叹气声,劝解声交杂一片。
不到几秒的功夫,我已经躺在了地上。我仍听见那个刺耳的声音在叫唤:“SB就是SB”!
我半撑起身子,正想站起,脚踝突然袭来的疼痛让我头晕目眩又坐了下去:“我的腿你这个SB”
徐建听罢,撇开几个人的拉扯,高举起书本,正往我砸去。突然,从他背后伸出两只粗大的手。
一秒钟后,飞出去的不是课本,却成了徐建。
“猿芳!”我道,费力撑起了身子。
阳光透过玻璃洒过来那个明晃晃的轮廓。粗犷的身材,强健的手臂,斯文的表情,幽香的古龙水,戴着一副近视眼镜。
“够了,都别闹了!这是上课!这么多外国人在看!”猿芳一把将我的手臂扛在自己肩上,扶着我的脚问:“怎么样?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
“要快点我疼”我冒着大汗,眉头皱成一团:“猿芳这事你怎么看?”
“我觉得你的腿和你的人都有点蹊跷。”
这个青春有点热
在医院忙活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屁颠屁颠赶回Les ulis,已经是有些暗色的黄昏时分。中世纪装潢的灯柱同时点亮,照亮了这座清冷而古老的小镇。
楼梯上不知是谁撒了片片红点,随意黏着许多散金碎末,几张写着“新年快乐”的大字报贴在楼梯间。早上还是平素生生的楼道,此刻终于有了点中国新年的味道。
舞会举行的大教室,其实就是间几十平方的老旧课室。听说是由于修建时不想浪费,便在走廊的末端规划了一块作为场地。大教室时常人满为患,还有几个阿拉伯人有事没事拿着毯子绑着头巾捂着嘴在大教室门口不知念着哪个食人族的咒语,让人感觉9月11日可能发生点什么。
我从墙上的大字报挪回视线。一旁的猿芳指着我的鼻尖,将两双拐杖搁在自己手里,拍了拍眼前我腿上那坚硬无比的石膏,咆哮道:“你说你!今天过年,又是舞会,你没事和徐建去计较那些干什么?他上午真把你打成SB了?”
“别吼我!”我嘴里叽里咕噜了声,想起徐建那蹭亮的光头,一阵窝火:“我偏参加,跳不了我也看!”
“居然还先动手?你难道不知道”猿芳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改口道:“你腿都扭成这样了,还参加舞会?”
我说道:“这新生团聚,留学就是混个人脉,回宿舍干什么?”
我的脑海里又出现那寒冷得如冰箱一般的宿舍,充斥着水泥石灰味儿的微信二维码。想到这,我抓过猿芳手里的拐杖,往大教室蹦去。
“等等。”猿芳喊道。
“又怎么了?”
“诺!”。
只见不远处的大教室,突然响起阵阵鼓掌声,在深长的走廊里回音不断。淑君老师正穿着黑色丝袜,坐在大教室中间滔滔不绝。有人说丝袜是权力的象征:女人穿着它可以征服男人,男人穿着它可以征服银行。
淑君老师正挥动双臂,慷慨陈词,红光满面地坐在讲台上,余光里出现的拐杖,一下子吸引了她的目光。于是,缎绸旗袍的裙尾在空中滑了一道弧线,又是一阵风驰电掣的吼叫:“门口的,别站在那里,进来!”
没等我坐定,淑君老师便走到了我跟前,撅起的通红的嘴唇,像放了地沟油的炸油条:“怎么样,走得动吧?还来参加舞会?”
“过来看看。”我瞄了瞄这个穿着5厘米的高跟,却依然不到肩膀的领导。
淑君老师伸出一根手指,脸上泛起红晕,随后用爱民如子的口吻道:“既然参加舞会,那100欧,待会儿交给我。不要开支票,最好是现金”
“老师,我这样跳舞,有一定难度”
淑君老师打断道:“好了好了。今天除夕,我就先不批评你了。上课都敢干这种事情!”
“又不是我先”
“舞会是学联组织的。跟大家多多活动是好事。既然要来参加,费用不可以少。每个同学都交了。因为我们要提供点心,布置场地,开销很大。不然你就别来。其他事情,另外找时间和我谈。”
说完,她便转身往教室中央走去。负责人果然有负责人的气魄。
大教室正中央的霓虹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旋转起来,尽管满是灰尘,款式老旧,但下面围着一群女学生,露着雪白的大腿,表情红润,却抱着身体瑟瑟颤抖,模样楚楚可怜,仿佛一辈子没见过霓虹灯地尖叫着:“好大!好粗!好棒!”
我朝女学生们瞄了眼,内心纷乱起伏。我拿起一旁的《故事会》,朝猿芳道:“今天的货,质量有问题。她们对霓虹灯的看法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你好好完成你的业绩。我看会儿书,没啥意思。”
“何必呢?”猿芳问:“既来之,则安之。你那么强硬要过来,还看什么书?”
“腿疼。”我瞄了一眼和女生打成一片的徐建,补充道:“心也疼。”
“咳,你这人,这点小破事!”
说完,猿芳朝那群雪白的大腿走去。只见他微笑着,绅士一般调侃几句,便拉起一位女孩的手,领到教室中央。那舞步时而明快,时而深沉,不拖不沓,干净利落,音乐仿佛为他雕刻一般。所有人都围在猿芳和雪白的大腿旁,不断发出惊讶的赞美声。
我不知怎么,忽然想起《动物世界》里有句低沉的开场白:“春天到了,动物们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正在这时,教室中又晃进一个陌生的身影。
炫彩的霓虹灯映射出一张清秀的脸庞,那会说话的眼睛弯成迷人的弧线,高挑的鼻梁,小巧的嘴,桔红色的头发盘绕在娇贵的肩膀上。
这是谁?
我正想着搭讪理由的当口,女孩却主动走了过来。
“你好!”
女孩主动说道,一只细腻白皙的手,轻柔地停在空中。
这莫非难道
我的嘴角升起无法控制的弧线。
那双手是如此精美,仿佛一件珍藏的雕塑品。曲线修长而且完美,再配上金手镯,有种高贵的气质。特别是皮肤,淡淡的白,光滑而且柔顺,就像一幅珍藏的画,玲珑而且淑静,典雅却不失乐感。她的无名指上,一个亮白的银戒闪着光。
记忆中“无名指戴戒指”,应该是“单身”的意思。
“好!你也好!大家都好!”我放下手里的《故事会》,赶忙上前。
“新年快乐!”女孩清秀的面颊涌上绯红,身上清淡怡人的薰衣草香:“你们是雷堡大学的学生?”
“你你怎么懂中文?”
“噢,我妈妈是中国人,我是混血儿。”女孩走上前一步继续说:“请问,中间那个跳舞的人是谁?”
“他?”
场中央的猿芳依旧翩翩起舞,人群不时爆发出尖叫。闪烁不定的霓虹灯,映衬出猿芳健硕有力的臂膀和帅气的脸,像故事里令女人着迷的白马王子。我哼了一声,心里忽然出现一匹在草地上吃着泥的马。
“不知道么?”女孩问道,笑容依然甜美:“中国人?日本人?”
“他,是我同学。他姓他姓草。”
“跳得真好!”
我瞅着猿芳半天,又看看女孩。每次看完故事会以后,我便知道自己的智商前300年和后300年都无人能够超越,于是我热血涌上头顶,不知哪来的勇气,上前一步拉起女孩的手,放在自己的肩头。
“你”女孩张开嘴巴,却并未抗拒,反而问:“这样也能跳?”
“这叫单边舞。”我轻搂起女孩柔弱轻盈的身子。女孩红晕醉人的脸上,清澈的大眼睛在忽明忽暗的光影里像一片迷人的湖泊。
周围的人也心领神会,不约而同吹起了口哨。女孩闪动着动人的光泽的樱唇,呼吸声近在咫尺,微微隆起的胸脯轻靠着我,像只优雅的美丽的蝴蝶。
“你叫什么?” 我问。
“Elodie”女孩说:“中文名叫‘爱乐迪’”。
“你也在雷堡大学?”我问。
“我刚刚毕业。雷堡法律本科。”爱乐迪说道:“我上班了。现在一家律所里实习。”
“噢?”我追问:“住这附近吗?”
爱乐迪抬起头,目光在我的脸上停顿了会儿说:“巴黎。和我朋友住一起。”
“巴黎!哪?”我道:“我也很想住在那里。”
“16区。”爱乐迪长长的睫毛动了动。
巴黎像块蛋糕,被从外到里被切成八圈,只有最里面的两圈被称做小巴黎。小巴黎又被法国人分成二十个区。而其中的16区被称为法国顶级的富人区。这寸土寸金之地虽然离雷堡大学不远,和书香墨水古老的大学相比却是两个世界。中世纪的宏伟和现代化的摩登、左岸的浪漫和右岸的时尚尽显于此。埃菲尔铁塔高耸入云,周围点缀各色缤纷的花卉盆栽,永远不断的车流从粉彩琉璃的香街和雄伟的凯旋门旁穿过,随处可见高贵的法国女人。
而眼前的爱乐迪!
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这混血儿不正是我苦苦寻觅,又寻觅不到的那个人么?
“怎么?你也想到巴黎住?”爱乐迪雪亮的眼睛上下打量了一下我。
“那可不!离学校那么近,生活又那么方便。”
“怎么不搬去?”
我耸耸肩膀。这个问题他早已问了自己无数遍,谁想留在这连拉屎的鸟都没有的地方,这里只有饥饿、枯燥,还有赶死赶活的匆忙。
“我是很想去,只是手头”我搓搓手指:“诶等腿好了再说吧!”
我叹了口气,看看天花板,突然间,脑袋里晃过一阵不知从何而来的一阵晕眩。一瞬间,明亮的世界仿佛被撕开一个口子,从口子里涌出了墨水般的、浑浊的黑色音乐也突然跟着暴躁起来,像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野兽,发狂地撕咬着喉咙,令人无法呼吸
“啊!”
我叫着,倒了下去。
怎么回事?
迷糊中,耳旁是混乱的叫喊。有人扶起我的身子,紧接着一阵刺耳的惊呼。
猿芳和几个人七手八脚将我抬到了一旁的空地上。“喂,喂?!” 猿芳蹲下来,拍拍我的脸,将水杯塞到我嘴边问:“怎么搞的?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我我”我抬起眼皮,嘴巴却不听使唤,滚烫的汗顺着额头滑落到地面。
“这在医学上叫做晕阙。”周围有人道:“会出现虚脱、发冷等症状。”
“说说说,说你妹的!”猿芳站起身子,吼道:“人家都晕过去了,你们只知道围观吗?赶快拿些水,打医院电话!我你你怎么了?!”
“不用了。”隔了几分钟,我自己慢腾腾坐了起来,有气无力地摇摇头,双眼通红地往人群看了一眼,随即低下头去:“我没吃早餐中午在医院跑来跑去腿又痛,晕了。”
我擦擦汗,接过猿芳的点心,耷拉着脑袋咬了一口。
“省这钱干什么?神经病,这样迟早会出问题!”猿芳站起身子,撑着我手臂:“走!扶你回宿舍去。”
说完,他从人群中拨开一条路,和几个人七手八脚将我搀扶出了大教室。
高雅神圣的舞会音乐又重新奏响,恢复了浪漫的情调。精致的甜品,炫彩的光,优柔的舞曲,醉人的香
找淑君老师去
被风蹂躏一个晚上的宿舍,像个巨大的冷库。以往,睡在被窝里,暖洋洋的被窝仿佛和床结为一体,被子一蒙,醒来就是天亮。
可是今天,除了头疼,就是头疼。脑袋横着痛,竖着也痛,像被人敲进了一根钢钉,用力地拉扯,从麻木而肿胀的石膏里一直疼痛到头顶。
在这样的被窝里多呆的每一分钟,都是世界末日。
我掀开被子,跳到镜子前。
镜子里,依旧是那张被岁月侵蚀过的脸。坑坑洼洼的月球表面,布满血丝的眼睛,扁平的鼻子,尖嘴猴腮的下巴,一点儿特点也没有。
一个风华正茂,情商智商都是99的留学生什么时候成了这颓废不堪的中年宅男的模样?
我长叹了一口气,突然,长长的走廊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
“白杉!”
五大三粗的猿芳一把推开那扇遮掩的门。
“这么早,什么歪风把你吹来了。”我说道:“有屁快放。”
“哟,你居然非主流了?”猿芳道。
“非主流?”我问。
猿芳将拐杖抗在自己身上,一拍门板:“这不,你瞧?”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个大大的太阳图案出现在门的正中。
我就跟被雷劈似的愣在那里——这哪是什么非主流,不就是那黑老大手上纹着的图案吗?
“怎么?说你非主流还不高兴了?”一旁的猿芳问。
“这个图案,好眼熟,好像是在别人手上见过。”
猿芳“咯咯”笑个不停:“你从昨天到今天还没清醒呢?就一个太阳,中间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