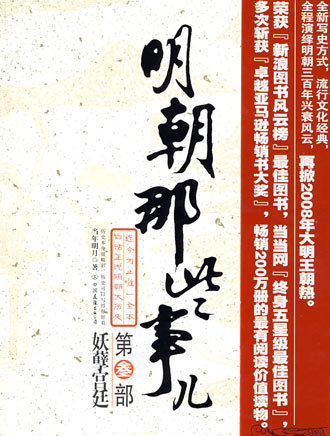画虫儿-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哈哈,两千块钱!你呀,棒槌一个知道吗?两千块钱,这样的画儿,能买十张!”
“什么,能买十张?”梁三的眼珠子快要瞪出来了。
冯爷的那只小眼微微合上,睁开了那只大眼,“月亮”又射出一道让人匪夷所思的柔光。他转身把女服务员叫过来:“去,给我拿个打火机来。”
他不抽烟,平时身上不预备能打着火儿的家伙。
服务员的身上都备着打火机,准备随时给顾客点烟用。她掏出打火机递给了冯爷。
梁三愣了一下,莫名其妙地问道:“您这是干吗?”
冯爷不屑一顾地冷笑了一声:“干吗?玩儿!”
“玩儿?您打算玩儿什么?”
没等梁三把话说完,只见冯爷展开那幅文徵明的假画,打着打火机,把画儿给点着了。
“哎哟,您这是?”梁三被惊得目瞪口呆,像是冯爷捅了他一刀。突然他明白过味儿来,扑上去,想一把夺过烧着的画儿,被冯爷给拦住了。
眼瞅着那幅画儿已烧了一半,冯爷干巴呲咧地对梁三笑道:“怎么,烧了你的心是吗?哈哈。”他随手把冒着烟的画儿往地上一扔。
梁三过去,把余火踩灭,看着一幅画转眼之间烧成了灰,耷拉着脑袋说:“冯爷,您干吗烧了它?”
冯爷道:“干吗?我怕你拿着它再去欺世!”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子钞票,数出两千块钱往桌子上一拍,冷笑了一声,说道:“这幅假画算是我买的,拿着吧!我不白吃你这顿饭,让你今后玩儿字画长眼睛!”
说完,他拂袖而去,给梁三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儿。
这就是冯爷的性情,他干出来的事儿,常常出人意料,像是说相声的,说着说着突然之间,抖出一个包袱,把您干在那儿,他抬腿就走,不给您留半点面子。您呢,说不出来,道不出来,哭不起来,也笑不起来。
第二章
冯爷,敢称冯爷,自然身上带着一股子爷劲儿。他的爷劲儿上来,向来不管不顾,用北京话说,爱谁谁了。
老北京人管在某一种行当里干了几十年,具有相当高的专业知识,详知一切的行家里手,叫做“虫儿”。“虫儿”原本是一个褒义词,可是有些人觉着“虫儿” 这个词儿显得不受听。虫儿嘛,天上飞的,地下爬的虫子,不咬人也腻歪人,不招人待见。小爬虫儿。夸人,有这么夸的吗?所以认为这是个糟改人的词儿。
其实,有些自认为深沉的人,压根儿就没明白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钱大江就属于这种“深沉人”。
有一次,在古玩城开画店的秦飞,淘换到一幅吴昌硕的《富贵清高图》,画面是两朵牡丹和两枝含苞的玉兰,落款是吴俊卿,鉴印是老缶。他一时吃不准是真是假,找冯爷掌眼。
冯爷拿他的“阴阳眼”一量,从嗓子眼儿蹦出一句话:“赶紧把它撕喽!”
甭再多问了,这是幅赝品。
这幅画儿是秦飞从一位老先生手里,花一万块钱买的。撕?那不等于撕人民币吗?他当然舍不得。可是冯爷却给它判了“死刑”,自然,他心里挺别扭。
别扭,也让他不忍心把这幅画儿当废纸给撕了呀!他憋了几天,想到了书画鉴定“大师”钱大江。
说起来,钱大江在京城书画收藏圈儿的名气不比冯爷小。他的岁数也比冯爷大,今年六十岁出头,按说年龄并不太大,但已然是满头白发,当然这白发是他有意染的,戴着一副金边眼镜,透着一股学究气。
他要的就是这种气质,当然他也是学究。不说别的,单看他头上戴着的几顶桂冠,就够“学究”的。钱大江本是某高等学府教美术史的教授,此外还是某艺术研 究院的研究员,某权威文物鉴定机构特聘的书画鉴定专家,某博物馆的特聘鉴定专家。在治学上,他也有不俗的业绩,近年来,不断有论文见诸报刊,还出版了几本 美术史和书画鉴定鉴赏方面的著作。当然随着民间收藏热,他还以鉴定家的身份,频频在电视上露面,给收藏爱好者指点迷津。这些光环足可以使他在收藏界占一席 之地。
当然,有这些光环罩着,他说话不但举足轻重,而且还能点石成金。他鉴定过的字画,拿到任何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都会亮绿灯,是真是假,有他的签名,那 就是板上钉钉儿,谁敢再说一个“不”字?自然,买家也不会怀疑他的眼睛。手里有他签名的鉴定证书,像吃了“定心丸”,心里会踏实许多。
在这方面,可就把冯爷给比下去了。冯爷的“阴阳眼”再“毒”,范儿再大,他的鉴定也拿不到台面上来,他签名的鉴定证书,拍卖公司也不会认。当然这位爷也向来不干这种事儿。
为什么?冯爷没名分,他既不是什么委员,也不是什么教授,更没人封他是什么专家。说不好听的话,他连个正经职业也没有,整个儿是白板一块。您说这样的闲云野鹤能摆到台面儿上来吗?自然,他的爷劲儿再大,那些专家、教授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秦飞通过“泥鳅”的关系,结识了钱大江。
“泥鳅”是郭秋生的外号。在见钱大江之前,郭秋生特意拿话“点”给秦飞:“找钱大师鉴定画儿,您得出点儿‘血’,别忘了带‘喜儿’。”
“还用你告诉我吗?这我明白。”秦飞对“泥鳅”说。
“喜儿”就是老北京人说的谢仪。在早,北京人的礼数多,求人办事儿,不能光嘴上说两声谢谢,要用银子说话,也就是给人家点儿好处费。这种好处费就叫“喜儿”,也叫“打喜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给人家打一个“红包儿”。
秦飞给钱大江打的这个“红包儿”挺瓷实:五千块钱。几年前,这也不算小数了。您想秦飞买这幅画才花了一万块钱。
秦飞是山东济南人,做买卖出身,他知道能得到钱大江的签名,似乎比得到这幅画还重要。山东人透着实在,既然“打喜儿”,就不能让人家小瞧了自己。
他本想设个饭局,邀钱大江出来撮一顿,在饭桌上看画儿。但钱大江没给他这个面子。
“你直接到我家里来吧,我实在是太忙了。”钱大江在电话里说。
秦飞带着画儿登门拜访。钱大江似乎不想让秦飞多待,寒暄过后,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让秦飞把画儿展开,他瞭了两眼,就让秦飞把画儿收起来,然后坐在了沙发上,拿眼瞄着秦飞问道:“这画儿是你的祖传吗?”
“不是。”秦飞答道。
“嗯,从别人手里收上来的吧?”
“是是。”
“嗯,我说呢。”钱大江拉着长声说。
他的眼睛一直看着秦飞,架子端得挺足,让秦飞觉得他不是在品画儿,而是在品自己这张脸,他觉得有点儿难堪。
突然他意识到带来的“喜儿”,该出手了。于是他微微一笑,侧身从包里把那个装钱的信封拿出来,递给了钱大江。“钱老师,这是一点儿小意思,您收下。您平时做学问,写东西费脑子,留着买点儿什么补品吧。”
钱大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上带出挺不高兴的样子,冲秦飞摆了摆手说:“嘿,你这是干什么?来就来吧,还”
“不不,您别介意,这是我一点儿心意。”秦飞把信封塞到他的手里。
钱大江半推半就地瞪起了眼睛:“你这是干吗?想拿钱贿赂我是不是?我可不是当官的,给不了你什么好处。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我坚决不能要。”
秦飞道:“您这是哪儿的话?您是做学问的文化人,我贿赂您干吗?我不过是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您别想那么多,收下吧,也没多少钱。”
其实,秦飞已看出钱大江玩的是假客套。
钱大江依然犹抱琵琶,嗔怪道:“动不动就掏钱,这样做多俗气!我们文化人是耻于谈钱的。不就是帮你看幅画儿吗?何必要这样呢?”
他用手摸了摸,感觉到那个信封挺厚实,当然他心里清楚,谁也不会把掏出来的“喜儿”再往回收,所以有意地把脸一沉,把信封塞到秦飞的手里。
秦飞转过身,把信封放到桌上,满脸堆笑道:“我知道您是个廉洁自律的大师级鉴定家,听说您给谁鉴定都不收钱。我今天绝对不是因为您帮我掌眼,才给您送礼,只是太敬重您了,表达一点我对您的敬意。”
这几句话倒让钱大江挺受听,他咧了咧嘴,干笑了两声道:“好啦,咱们别为这点儿小钱来回争执了,下不为例吧。好不好?”顿了一下,他说道,“嗯,你再把画儿展一展,我细看看。”
秦飞感觉到他说话的语气变了,心想,这是“红包儿”起了作用。他赶忙把画儿重新展开。
这一次,钱大江看得比较仔细,还拿放大镜看了看画儿上的款识和印章。
“嗯,有吴昌硕的金石气味儿。”他放下放大镜,让秦飞把画儿卷好,拧了拧眉毛说,“看吴昌硕的画儿,要看他的古朴老辣,也就是宋朝人说的‘老境美’。 你是玩字画的,应该知道吴昌硕最初是搞书法、篆刻的。据说他五十多岁以后,受任伯年的启发,才开始学画儿,所以他把书法艺术运用到绘画当中了。”
秦飞点了点头说:“是呀是呀,他的画儿写意的味儿很浓,喜欢用粗笔重墨。”他事先看了不少书,也是现趸现卖。
钱大江道:“光看他的粗笔重墨不行,要看他的画儿的意境。”
“是是,那您看这幅画儿,有没有您说的这种意境?”
“没有,我说它干吗?”
“这么说它是吴昌硕的真迹了?”
“应该说是他六十岁以后的作品。印章也对,‘老缶’是吴昌硕的别号,他的别号很多,除了‘老缶’,还有‘苦铁’、‘大聋’、‘破荷’等等。当然,他的原名叫俊、俊卿,字昌硕,号缶庐,很多画儿署名吴俊卿。”
“大师的眼睛就是‘毒’,既然这幅画儿过了您的眼,您能不能”
“让我给你写几个字对不对?”钱大江自我解嘲地笑道,“这还用你说吗?你大老远的找我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是是,您的大笔一挥,这幅画儿就有定论了,也有收藏价值了。不然,我心里总不踏实。”
“拿到这幅画儿,好像有了心病是吧?听得出来,你玩字画儿的时间还不长,对吧?”
“是是,刚摸到点儿门道。”秦飞唯唯诺诺地说。
他本来想让钱大江直接在画的背面写上自己的鉴定证明,但钱大江没应。他另找了张纸,用签字笔写了一行字“经鉴定《富贵清高图》为吴昌硕的真迹。”然后写上了他的名字,并且盖上了印章。
秦飞抖了个机灵,在钱大江写字时,他拿出数码相机拍了两张,之后又跟他一起合了影。
秦飞拿到这张鉴定证书诚惶诚恐,连声道谢。钱大江看他心满意足,便站起身,预备打发他走人。如果事情到此结束,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偏偏秦飞为了讨 好钱大江,临出门,冒出一句可说可不说的话:“有您这几个字,这下我算是吃了‘定心丸’。您可不知道前些日子,我让一位高人看了这幅画儿,他非说是假的, 让我几天几夜没睡着觉。”
钱大江听了,随口问道:“你找哪位高人给看的?”
“冯爷,您认识他吧?”
“冯爷?噢,你是说长着一对‘阴阳眼’的那位他叫什么来着?”
“冯远泽,对了,他还有个号,叫拙识。”
“嗐,你找他?他能看出什么来呀?他不过是个‘画虫儿’,倒字画儿的。”钱大江撇了撇嘴,漫不经心地说。
“是是,经您这么一说,他那对‘阴阳眼’,还真是二五眼,他能看出什么来?”秦飞恭维道,“您说他是‘画虫儿’,对对,我看他也像条虫子。”
说起来,也是秦飞多嘴。钱大江把您带来的这幅画儿鉴定成真迹,您自然高兴,因为冯爷的那对“阴阳眼”,已然把这幅画儿判了“死刑”,而钱大江的一纸鉴 定书又让它“活”了。这一“死”一“活”,等于您把几十万块钱的存折攥在了手里,可是您一时高兴,就回家偷着乐去呗,干吗非要借机贬损一顿冯爷呢?再退一 步说,您在钱大江那儿贬了一通儿冯爷,也算是过了嘴瘾,发泄了一下,就别再跟圈儿里的人没完没了地磨叽这事儿了,可是他却把这事当成了话把儿,逮谁跟谁 说,成了圈儿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您想这种闲言碎语能传不到冯爷的耳朵里吗?
“哈哈,说我是‘画虫儿’,这个封号好!”冯爷从一个朋友那儿,听说钱大江把他贬损了一通儿,忍不住哈哈大笑。
冯爷打电话把秦飞邀到一个茶馆。一见面,他的那对“阴阳眼”上下翻了两个来回,把左眼闭上,睁开右眼,“星星”在秦飞脸上定了位。他单刀直入地问道:“信不过我,找专家给你那张破画儿鉴定去了,是不是?”
秦飞被那“星星”晃得不敢正眼看他,低着头说:“您别介意,不是我信不过您,我是想多找几个人给量量活儿,心里不是更有谱儿了吗?”
“别跟我这儿玩哩哏儿愣了!你呀,棒槌一个知道吗?”冯爷对谁都爱说这句话,几乎成了他的口头语。
“是是,我是棒槌,要不我怎么总想多找几个老师给掌眼呢。”秦飞的话也跟得快。做买卖出身的人,信奉拳头不打笑脸人,礼多人不怪的人生哲学。
“你是棒槌,你找的人也是棒槌,知道吗?”冯爷的那只小眼突然变成了一口深井,那井像是要把秦飞给吞了。
秦飞怕自己掉到井里去,一直不敢跟那只眼睛对视,他打着稀溜儿说:“怎么,您认为钱大江先生也是棒槌?他可是大学教授,国家聘请的专家。”
“哈哈,教授、专家?你们这些人呀!眼睛都是怎么长的?教授、专家就都是神仙?教授、专家里就没有滥竽充数的?迷信,什么叫迷信?这就叫迷信知道吗? 这个钱大江,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知道他吗?别看他人五人六的,什么教授、专家的帽子戴着,臭大粪一个知道吗?你找他掌眼,是你瞎了眼!”
“您这话是不是说得有点儿过了?”秦飞嘀咕了一句。
“过?这还是好听的呢。秦飞,你可以把我刚说的都给他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