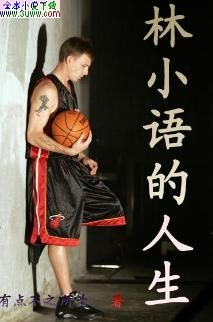真正的人-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伐木者吗?是像他一样的俄罗斯人,正在从被围困的德国人的后方经过前线溜到自己人那儿去?或许是当地的农民什么的?他不是听见有人清清楚楚地用俄语喊了一声“人”吗?
他的手爬得发麻,手枪在这发麻的手中抖动着。但是,阿列克谢还是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要好好地利用剩下的三颗子弹……
这时,从灌木丛里传来了一个孩子的焦急不安的声音:
“喂,你是谁?陶依奇?维尔什泰奇?”①
①德语:“德国人吗?懂吗?”不是标准的德语,而是俄音德语。
这些奇怪的话使阿列克谢警惕起来,不过喊话的人毫无疑问是个俄罗斯人,而且是一个小孩,一定没错。
“你在这儿做什么?”另外一个童声问。
“那么你们是什么人呢?”阿列克谢回答了一声,接着就沉默起来。使他惊讶的是,他的声音是多么的软弱无力。
他的问话引起了灌木丛里一阵骚动。那里的人们低声细语了半天,大幅度地做着手势,以至于把小松树的树枝都晃动了。
“你不要给我们兜圈子了,你骗不了我们!德国人哪怕离我们五俄里远,我们也能闻出他的气味!你是陶依奇吗?”
“而你们是谁呢?”
“你管得着吗?聂维尔什泰①……”
①德语:“我不懂。”这句是俄音德语,不是标准德语。
“我是俄罗斯人。”
“撒谎……我敢起誓赌咒:你在撒谎,弗利茨①。”
①弗利茨是德国人的普通名字,这里用来代指德国人。
“我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我是飞行员,我是被德国人打下来的。”
现在,阿列克谢用不着担心了,他确信灌木丛里的人都是自己人,是俄罗斯人,是苏维埃人。他们不相信他,有什么办法呢,战争教人处处小心。在全部征途中,他是第一次感到自己极度虚弱,无论是手还是脚都不能再动弹了,既不能移动,也不能自卫。泪珠顺着他那乌黑凹陷的脸颊流了下来。
“瞧,他哭了!”灌木丛里面有人说,“喂,你哭什么?”
“我是俄罗斯人,是俄罗斯人,是自己人,是飞行员。”
“那你来自哪个机场?”
“你们是什么人?”
“这关你什么事,你回答就是了!”
“来自蒙恰洛夫机场……请帮帮我吧,快出来吧!你们究竟为什么……”
灌木丛里吱吱喳喳地说得更热闹了。这时,阿列克谢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一段话:
“咦,他说是来自蒙恰洛夫的……大概是真的……还哭呢,……喂,飞行员,你把手枪扔掉!”他们对他喊叫:“我们说,扔掉;不然的话,我们是不出来的,我们要跑了!”
阿列克谢把手枪扔向旁边。灌木丛拨开了,两个小男孩——他们神情警觉,像好奇的山雀,随时准备飞快地逃走——互相挽着手,小心翼翼地向他走来。年龄较大的那个孩子,长得瘦瘦的,生着淡蓝色的眼睛和纤维般的淡褐色头发,手里握着准备好了的斧头,大概是做出了决定:一有机会就动用它。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头发是棕红色的,脸上长有许多雀斑,他躲在那个大男孩的背后,老是探出头来,用充满掩饰不住的好奇眼光偷看,边走边嘀咕着:
“他在哭,真的在哭。他多么瘦呀,太瘦了!”
大男孩朝阿列克谢走近时,一直握着准备好了的斧头,他用父亲的大毡靴把落在雪地上的手枪踢得远些,并说道:
“你说是飞行员吗?那么有证件吗?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是谁在这里?是自己人,还是德国人?”阿列克谢不由自主地微笑着,低声问道。
“那我怎么知道?没有谁告诉过我。这里是森林。”大男孩机智地回答道。
阿列克谢只好把手伸进军便服里掏证件。这是一本带有一颗星的红色指挥官证,它给孩子们留下了神奇的印象。在祖国被敌人占领期间,孩子们失去了童年,现在因为在他们面前出现了自己敬爱的红军飞行员,那童年仿佛立刻又返回到了他们身上。
“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已经来了三天了!”
“叔叔,你为什么这样瘦?”
“……我们的人在这里把敌人打得胆战心凉,落花流水,狠狠地把他们猛杀了一顿!这里的战斗大激烈了!把他们打死了很多很多!”
“他们逃跑的时候,是遇到什么就坐什么……有的人把桶绑在车辕上,坐着桶走。要不然就是两个伤兵拉着马的尾巴跟着走,还有的人像德国男爵就骑着马……叔叔,你是在哪儿被他们打下来的?”
孩子们连珠炮似地说了一通后,就开始行动起来。按他们说的,从伐木场到有人住的地方大约有五公里。阿列克谢已经疲惫不堪,甚至联想翻过身来仰躺得舒服一点都不可能。这儿有一辆雪橇,那是孩子们拖到“德国伐木场”上来运载柳树的,但是太小了,再说,让孩子们用雪橇拖着一个大人在没有大路,没有人走过的雪地上走,力气也不够。大男孩名叫谢连卡,他吩咐弟弟费季卡拼命地跑回村子去叫人,而自己却留在阿列克谢身边,照他的说法是给阿列克谢放哨,防备德国人,其实却暗暗地不相信他。他想道:“鬼知道他是什么人,德国鬼子狡猾得很——又会装死,又会弄到证件……”不过,这些疑虑慢慢地消失了,大男孩就无拘无束地和阿列克谢闲聊了起来。
阿列克谢躺在松软的针叶上,半睁半闭着眼睛打瞌睡,对男孩子讲的故事似听非听。一阵舒适的睡意突然一下子束缚住了他的身子,只有几个不连贯的单词透过这种睡意传到他的意识里。阿列克谢并不去深入理解它们的意思,而是透过睡意欣赏着母语的声音,直到后来他得知帕拉夫尼小村居民的悲惨故事为止。
还是在十月里,当时白桦树上的黄叶像在燃烧,白杨树似乎是笼罩在红色信号火中,就在这个时候德国人来到了这些林区和湖沼区。帕拉夫尼这一带没有发生战事。在它西面大约三十公里的地方,有一队红军在守卫匆促筑成的防御工事。有几个德军纵队由强大的坦克先遣队率领着,在打败了这队红军后,路过隐藏在路边林中湖旁的帕拉夫尼村,向东开去。为了占领鲍洛高耶这个铁路大枢纽,然后再切断西线和北线的联系,他们就向那儿突进。在通向这个城市的漫长道路上,加里宁州的居民——城里人、农民、妇女、老人和小孩,各种年龄不同和职业不同的人——在雨淋和酷热中挖掘与构筑着防御工事,遭受着蚊子叮咬、沼泽潮湿和臭水的折磨,不分日夜地干了一个夏季和秋季。防御工事穿过森林和沼泽地,沿着湖边、河沿和溪岸,从南到北绵延几百公里。
建筑者虽遭受了不少痛苦,但是他们的劳动并不是徒劳无益的。德国人突破了几处防线的入口,可是在最后一道防线被遏制住了。战斗变成了阵地战,德国人因此没能突进鲍洛高耶城,他们被迫把进攻中心再往南移,并从这里开始转成防守。
帕拉夫尼村的农民收成不太好,因为是沙土,一向是靠在林中湖泊里捕鱼所得来维持不足,战争从他们身边绕过去了,他们已觉得万分幸运。他们把集体农庄主席改称为村长,这是按德国人的要求这么做的,但他们仍然过着以前的集体农庄式的生活。他们希望,占领者不会永久地践踏苏维埃大地,他们这些河滩之民在他们的僻静处或许可以避免敌人进攻。可是,在那些穿着沼泽地浮萍色军官制服的德国人后面,又跟着来了一批穿黑色制服、戴船形帽(而帽上有白骨头徽号①)的德国人,他们是乘汽车来的。他们命令帕拉夫尼的村民: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推举出十五人“自愿”去德国,永久地在那儿工作,否则,全村就要大难临头。村尽头的那个小木屋原是集体农庄的仓库和管理委员会,志愿者要去那儿报到,自带换洗衣服、汤匙、刀叉和十天的粮食。期限到了,谁也没有去。再说,穿黑制服的德国人可能已经有过教训,对这件事他们并不抱有希望。他们拘捕了集体农庄主席,不,是村长,幼儿园的女教员微罗尼卡·戈里高丽耶夫娜——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集体农庄的两位工作人员和十来个落在他们手里的农民,在管理委员会前面把这些人枪毙了,以示惩戒。他们不让埋葬尸首,还宣称:如果一昼夜之后,志愿者还不到命令中指定的地方去,那么他们就要这样来对付全村。
①纳粹德国党卫队的徽号。
志愿者还是没有出现。可是,早晨党卫队特别指挥部的德国人走过村子时,发现所有的小屋全部空了,什么人也没有——连老人、小孩也没有。他们抛下自己的房屋、田地、日积月累积攒起来的全部财产、几乎所有的牲畜,借助这地方的夜雾,在晚间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全村一个人也不剩,都撤到密林里——十八俄里以外的一个老伐木场上去了。成年男子掘地洞打游击去了,妇女们则带着孩子留在林子里受苦,一直熬到春天。这个地区被德国人称之为死亡地带。德军特别指挥部像对付这儿的大部分村庄一样,把这个反叛乡村烧得精光。
“我爸爸就是集体农庄主席,他们称他为村长,”谢连卡讲述道,他的话似乎是从墙壁后面传到阿列克谢脑子里的,“所以他们把他杀死了,把大哥也杀掉了。大哥是个残疾者,缺了一只手,他的那只手是在打谷场被切掉的。有十六个人被杀掉……我亲眼看见的,他们把我们大家都赶去看。我爸爸一直在喊叫,不住地破口大骂:‘你们这群狗鬼子,我们的人会找你们算帐的!’他不断叫喊着说,‘你们要用血泪来偿还我们付出的代价……’”
这个小男孩的头发是浅色的,一双大眼睛疲倦、忧郁,听了他的诉说,飞行员体验到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感到像是在有粘性的雾中游泳。他的整个身体因为遭受极度的紧张而疲惫不堪,不能克制的倦意牢牢地缚住了他的整个身于。他甚至连手指也不能动弹,他简直想象不出,就在两小时以前他怎么还能移动。
“这么说,你们就住在森林里吗?”阿列克谢费了好大力气才摆脱睡意的羁绊,用极其微弱的声音问小男孩。
“那当然,我们就住在这儿。眼下我们只有三个人:我、费季卡和妈妈。本来还有一位小妹妹纽什卡——她冬天死了,是浮肿死掉的,后来,还死了一个小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只有三个人了……怎么样,德国人不会回来吧,啊?我们的外公,也就是妈妈的父亲,他现在是我们的代主席,他说他们不会回来了,人们不会从墓地里把死人挖出来的。可是,妈妈一直害怕,老想逃走,她说,要是他们再回来……瞧,外公和费季卡来了!”
棕红色头发的费季卡站在森林边缘上,他用手指着阿列克谢给一位驼背的高个于老人看。那老人穿着一件破烂的土布上衣(这衣服用葱染过),腰里系着绳于,戴着德国军官的高顶制帽。
那个老人,高高的个子、驼背、削瘦,孩子们称他为米哈依拉。他生有一张和善的脸,像乡间常见的画书上面的那个圣尼古拉。他的一双眼睛是明亮的、纯洁的,很像孩子的眼睛。他的胡须完全是银白色的,有波纹,柔而不密。他把阿列克谢裹在一件老羊皮袄里——那皮袄打满了五颜六色的补丁,毫不费劲地抱起并翻动着阿列克谢很轻的身体,同时他一直带着天真的惊奇不停地说:
“唉,你,真作孽,一个好端端的人全给耗干了!唉,我的上帝,你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简直像一具骷髅!战争可把人害苦了!啊——呀——呀!啊——呀——呀!”
就像对待新生婴儿似的,老人把阿列克谢小心翼翼地放在小雪橇上,用缰绳在上面绕了一圈。他想了一想,脱下自己的粗呢上衣,把它卷好枕在阿列克谢的头底下。然后走到前面,自己套上用麻袋布做的小马套,给每个孩子一根绳子,说道:“好了,愿上帝保佑我们!”他们三人就拖着小雪橇在雪地上走起来。雪缠在雪橇的滑木上,咯吱咯吱地响着,像踩在马铃薯粉上似的,脚底直往下沉。
第15节
以后的两三天,对阿列克谢来说是宠罩在一层炎热的浓雾里的,在这朦胧幻景中他隐隐约约地看见了发生的情景。事实和虚妄之梦搅和在一起,只有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才把一件一件的真事连贯地回忆起来。
逃亡的农民住在一处百年老树林里。许许多多的窑洞都覆盖着积雪,还没有融化,上面铺着针叶,乍看起来是难以发觉的。从一个个窑洞里冒出来的炊烟,很像是从地里冒出来的。阿列克谢来到这儿的那一天没有风,很潮湿,炊烟粘在藓苔上、绕在树木上,因此阿列克谢觉得,这地方像是被困在快要熄灭的林中火灾里面。
全村居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还有几个老人——知道了米哈依拉要从树林里运来一个不知其来历的苏联飞行员,照费季卡的描述像“一具真正的骷髅”,都纷纷出来迎接。当“三驾马车”拉着小雪橇刚在树林间出现时,妇女们就把它围了起来,拍着巴掌、拍打着脑袋把缠着不走的孩子们赶走,接着就像一堵墙似地把雪橇团团围住,叹着气、哭哭啼啼地跟着走。她们都穿得破破烂烂,看上去好像全都是上了年纪的。因为生火没有烟囱,所以窑洞里的烟把她们的脸熏得黑黑的。只有根据眼睛的光泽度、牙齿洁白的程度,才能在这些褐色的脸上辨别出哪是青年妇女哪是老年妇女。
“娘儿们,娘儿们,唉,娘儿们!你们都聚在这儿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是戏院呀?是演戏呀?”米哈依拉一边发脾气,一边熟练地紧压马套,“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不要在脚底下走来走去,一群母羊,上帝饶恕我吧,简直是要疯了!”
阿列克谢听到人群里有人说:
“哎呀,多么可怕!真的像骷髅!一动也不动,还活着吗?”
“他昏过去了……他怎么会弄成这样?啊,老奶奶,他是多么瘦,多么地瘦呀!”
后来,惊奇的浪潮消退了。这个飞行员的命运未卜、很可怕,很显然,这使娘儿们吃惊。在他们拖着雪橇沿着森林边缘慢慢地走近地下村庄的时候,开始了一场争执:阿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