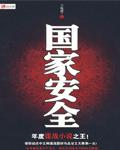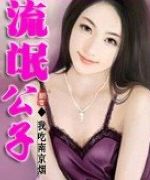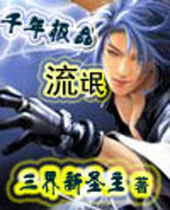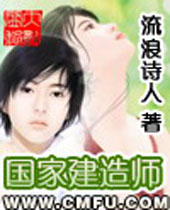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ダ翘踉嫉母H俣嗄昀矗锰踉家恢敝С抛诺ヒ幻褡宥懒⒐业南执侍逯啤U庖惶踉急臼俏崾暾秸�1648年签订的,作为一项基本的国际关系原则,它承认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和一国不能干预别国的内部事务。布什的理论似乎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又与纽伦堡审判中将“先发制人的战争”以战争罪论处的结论相悖。联合国宪章禁止“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这一新政策虽然出乎世人的意料,实际上却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苏联在老布什政府接近尾声时垮台,美国防御机构突然面临一个存在判断的问题。在没有“邪恶帝国”存在的情况下,美国继续维持一支大规模的、分布广泛的军队并给予其预算支持的意义究竟何在?当时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要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会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为新的美国防御战略拟订指导方针。鲍威尔在1992年初向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作证时曾对新战略有所暗示。他说,美国需要“足够的力量”去“制止任何梦想在世界舞台上向我们发起挑战的挑战者。”他还说,“我想成为街区的霸王,”这样,“试图向美国武装部队发起挑战就不可能成功了。”1992年3月透露给《纽约时报》的新国防规划指导方针认为,美国防御战略的首要目标是“防止再出现新的对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使盟友和对手都相信,“他们不必力求发挥更大的作用。”先发制人的力量若是一种选择,美国就要保持规模可观的核武库,同时还要劝导其它国家削减或放弃自己的核武库。最后,新的指导方针暗示,未来的联盟将是“临时的权宜性组合,常常不会延续到所对付的危机以后,在许多情况下,只是一般性地赞成要实现的目标。”
这份文件草案的透露,激起了猛烈的批评浪潮。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试图让切尼置身事外,称这份文件是“底下拟的一个草稿,”国防部长尚未过目。1993年1月,五角大楼最终公布了一个口气较为和缓的文本。不过,那时公布已无异于告别之举,因为老布什给新的克林顿政府一让位,后者很快就将新方针搁置起来了。现在,九年过去之后,小布什政府又把它从搁架上取下来,作为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采用了。
此举或许不该令人感到惊奇。上个十年,相当可观的一批先驱就在为新生的美帝国标划航程了。《华尔街日报》的前主编马克斯·布特要求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朗,或许还有其它地方,并且要在那些地方强行实行自由民主,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京和波恩所做的那样。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学者,后来成了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理查德·哈金斯1997年写了一本书,题名为《不情愿的治安官》。到了2002年夏天,他却在说,如果不得不重写这部书,他会把书名中那个形容词删掉。保守的评论家欧文·克里斯托尔断言,“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会认识到我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这个事实,即便舆论和我们所有的政治传统观念都不赞成这一想法。”
美国的新战略文件出台后,这种新秩序的最佳写照或许可见于2002年10月底的墨西哥。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的各经济大国首脑齐聚洛斯卡沃,参加与一年一度环太平洋主要企业领导人总裁峰会相关的协商。在墨西哥总统维森特·福克斯举行的闭幕晚宴上,总统与总理们坐在大厅一端的高台上,演员们在另一端的舞台上唱着舞着,实业家围坐在两者之间的圆桌旁。由于是在墨西哥,不到晚9点就别想开宴。我朝高台上瞥了一眼,发现许多领导人其实都在受罪。中国的江泽民主席已经76岁高龄了,前一天刚从北京赶到。他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样,显然都还没有克服时差引起的不适,其他人也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疲劳。布什总统是当天早些时候乘“空军一号”从他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牧场来的。由于只有3个小时的航程,他看上去神采奕奕。他坐在末端,紧挨着越南总理,看样子不像在交谈。实际上,他们似乎根本就没说话。到了10点,饭还没有上。我们坐在企业家桌旁的人把餐前饼干都打扫光了,还喝干了瓶子里的水。我正思忖(以早睡闻名的)布什是否能挺过整个晚宴时,他站起身就出去了。他得上床睡觉,以便第二天早晨6点钟能起来到海滩上去慢跑。我敢肯定,墨西哥的官员们事先早有思想准备,知道这位总统可能会提前离席,可企业家们肯定无人相告。他们注意到,美国总统虽然走了,江泽民、小泉及其他人却都撑到了最后。一位墨西哥的企业经理评论说,“布什以为他是谁,是皇帝?”
美国虽诞生于对帝国的反抗之中,但它从一开始即埋有自身成为帝国的种子。17世纪初,冒险到新大陆来建殖民地的有两种人,他们都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命运而来。与约翰·史密斯船长一同奔赴弗吉尼亚的冒险家和手艺人寻求的是财富,与约翰·温思罗普总督去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寻求的是天堂。从那以后,这两股力量就一直在驱使着美国人进行扩张。
首先,在那些开国元勋们的内心深处就存在着一定的两重性。一方面,华盛顿和杰斐逊发出警告,要提防缠人的盟友。大家都知道,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表示过,“美国到国外不是为了寻找要消灭的怪物她有可能变成世界的独裁者。她将不再是自己灵魂的主人了。”但是,梦想有个“自由帝国”的也正是杰斐逊。他大胆地购置了路易斯安那属地,把国家的版图扩大了一倍,还想象着总有一天“我们要大到即便不能覆盖南美,也要覆盖整个北美。”亚当斯对他的想法表示赞成。他说,“神圣的上天似乎注定要让北美由一个国家的人居住。”实际上,对外国采取的单边主义态度和扩张主义精神,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剑就叫做“美国例外论”。
从一开始,美国人就认为自己是个例外,不同于普通类型的国家。他们建立了古典时代以来第一个共和国之后,就认为整个人类从此开始了新的历史。因此,它不能再沾染依赖的习惯或采取旧历史中那些民族的方式。同时,美国人坚信,他们是人类的灯塔,并逐步开始认为自己——用本章前面引语中的话来说——是“上帝特殊的选民——我们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假如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那么,美国就是希望之乡了。美国人必须创立一个两边都是海的大陆国家,这一说法被命名为“上帝所命论上帝所命论——美国历史名词,广义指美国人是上帝指派去建立模范社会的选民,狭义指19世纪美国扩张主义者要把美国的疆界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的意图。上帝所命论是美国扩张主义的辩护词。——译者注”。1885年,上帝所命论已成为现实。当然,这一现实是以墨西哥和美洲土著人为代价换来的。前者在美国人挑起的战争中丧失了一半国土,后者几乎被完全灭绝。这一现实当时不知怎么无人注意到,反而披上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所谓的“扩大自由区域”的外衣。
19世纪末,这一地区发生了一次大跃进。上帝所命论实现后,美国的扩张主义精神转向了本国以外的陆地。事实上,美国对国外并不陌生,它在海外已经打过一百多次仗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游弋在中国的长江中。可是,1898年,麦金利总统却要求国会授权动用武力去保护美国的利益,制止对古巴的压迫。麦金利说,“我们进行干涉,不是为了征服。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赢得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的人的赞扬。”但是,战争结束后,前西班牙属菲律宾却落入了美国人之手。这时,麦金利经过多方“认真的苦思”(尽管菲律宾人已宣布独立)之后断言,“我们能做的只剩下全盘接受下来,教育菲律宾人,提升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成为基督徒。”菲律宾在当了四百年西班牙殖民地之后,就这样又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伍德罗·威尔逊虽然没有领导过对美国所控制的领土进行大规模扩张,却以新的方式诠释了麦金利的使命感,其深刻影响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都余音袅袅。首先,他一直等到德国潜艇发动袭击,将美国“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所行动。接着,他把国家引入战争,目的是为了使世界能够“安心地实行民主”。他搞的国际联盟之所以失败,据说是因为美国参议院中的孤立主义分子造成的。但实际上,反对派参议员是美国殖民地扩张的热心支持者。他们拒绝国际联盟,是因为他们是单边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例外论对美国例外论之争。威尔逊就算输了第一轮,可还是为该世纪下剩时间的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基调与框架。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策和目标,几乎完全是威尔逊式的。罗斯福总统刚一宣战便说,“我们参战,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本国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所处的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是安全的。”当然,美国后来在战争中崛起,成了居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不过,它做了这种超级大国前所未及的事。它摈弃了实行单边政策的老传统,为实行多边政策的新世界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冷战,世界将会怎样?设想一下这个问题会非常有趣。但事实上有冷战存在,杜鲁门总统决定以现在大家已经熟悉的方式做出反应。他说,“如果我们的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将有可能危机世界和平,而且肯定会危及到美国人民的安康。”
美国及其盟国在冷战中借以战胜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主要是以这么几点为基础的:首先,美国是从自己与盟国以及多国机构的关系角度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而联盟和多国机构组成的目的在于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在可能的地方维护与促进民主、全球的法治、互不侵犯及合法程序的实行。其次是要维护一支规模庞大的正规军事力量,并建立强大的巨型军工联合体。这支军队显然属于常备性质,而维持这支军队需要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3%~10%用在国防上,第三是习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尽管美国完全清楚,支持那些独裁分子和专制统治者有损于自己自由斗士的声誉,但只要这些人声称反对共产主义,它还是会频频地去支持他们(现在记忆犹新有伊朗国王,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及拉丁美洲、韩国、巴基斯坦和台湾等地一连串的军事独裁者。)最后一点是,自由贸易和开放时常与推进民主不可分割地连为一体,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实行会导致政治自由化。当然,这些政策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也不无好处。于是,冷战就这样经过前文提到过的美国人对财富与山巅之城的寻求而取得了胜利。
对美国安全威胁的突然消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争先恐后地采用民主政治和市场资本主义,再加上自由贸易,似乎令人感觉几乎没什么可争的问题了。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采纳普遍适用的美国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或者更广义地说,“西方”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将会在全球确立繁荣与和平。既然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明显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个国家可以趁机功成身退,大幅度地削减它的军事设施,关掉不少远方基地,修改美国在国外的义务,安安心心地给世界作表率去了。美国可以作为“山巅之城”牢牢地站稳脚跟了,可以像约翰·温思洛普总督几个世纪前设想的那样,高兴地让“所有人都看着我们”了。
然而,前苏联及其它国家的军队解体后,美国的军队和开支虽有所减少,在国外的存在却依然规模很大,在世界军事力量和军费开支中的比例实际上仍在增加。美国在冷战期间运用过的霸权逐渐开始呈登峰造极之势。冷战期间,美国只是在同等国家中坐头把交椅。它虽然是那些五花八门的盟友的领袖,但遇事仍要通过协商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而今却在朝着完全听凭美国做主迈进。将美国推向这种地位的有惯性和习惯之力,有庞大的专业武装部队带来的好处,有空想社会改良家威尔逊那种美国例外论和单边政策的复活,也有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经济日程表上项目的增加。
不过,失去了能与之抗衡的强国后,有些矛盾就浮现出来了。如果我们这个样板国果真那么强大,还要这么多军队和枪炮干什么呢?战略家们对这个问题最初的回答是,苏联虽然被消弱了,但它还能制造动乱和地区性冲突,而能制服它的只有美国。另外,要想保障新兴秩序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军就必须保持优势状态。海湾战争的发生,更是对这种想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这种想法的背后,却有着更根本性的原因:历史结束,胜负尽显。在1997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总统曾责备中国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1998年7月,他在香港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美国已逐渐开始界定“历史正确的一边”了。用来自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格里奇的话说,美国目前正处于“财富、势力和机会都无以伦比”的时期,可以左右世界命运,这个机会决不能白白浪费掉。后来当上国家安全顾问的孔多利扎·赖斯对克林顿的说法表示赞成。1999年,赖斯对洛杉矶对外事务委员会说,根本问题是美国是否“承担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应负的责任。”
“历史正确的一边”主要包括全球化,消除货物、信息、货币和人员流通的一切壁垒,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商业体系。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所言,“我们既想扩大我们的价值观,也想扩大我们的比萨饼店。”按照克林顿的说法,美国的作用就是要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