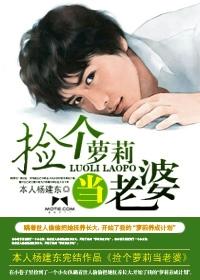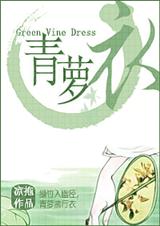������-��2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ˡ���
����ͩû�뵽�������ϵ�Ͱѵ绰�������İ칫�ң��������Ǹ������ҳ�������һ��Ȧ�����ڻ����Ƶ������羯�������ŵ��¡�
����˵�����˸�������Ů���ѣ����ϵ�������û�а���𱸣��������ǿ���Ц��������֪ͩ���������ϵ������֮����Ц��ص��ľ��粻��˭�����������õ��ģ���ֻ���������ӽ��ͣ���û�е��£�������һ�������ã����Ұ�ս�ѵ�Ů�����մӾ�У��ҵ�����Ǵ�Сһ��ġ���һ����ô˵��һ���������ʺ����ĸ�������б����Ҳ̫���˰ɡ�
�ϵ��ڵ绰��һ����Ц������ͩ�����Ҳ���������Ů���ѻ���������ã���Ӧ��֪�����������е����µľ��Ǹ���������㵹���˾����������ã������ˣ����»��ǿ�����ȫ��Ϊ�ã�����һ�������һ���˵�Dz������������
����ͩҲЦ���������ڰɣ������ֲ�������ɱ�˷Ż�Ĺ����������������ѣ����ø����ô���Űɣ���
�����������ϵ��Ц��������������������ͩ���Ҳ�֪���������Ϳ�ػ���װ��Ϳ����Ȼ�Ҵ�δ������ֻ�����·��Ҳ��������ʻ�������ʲô��������ֻ�轫��������������Ǯ�Ϳ����ˣ����㲻���治֪����������ʲô�����ɣ���
����ֻͩ������ð���������˺�һ���������������磬Υ���������Ҳ��ɣ���������Ⱦ���˵���ģ��㲻������ۏ���ˮ������Ҳ֪���Ұ���˭���Ҳ����������Ĩ�ڣ���˵ֱ�ӵ㣬��Ҫָ���Ұָ����ǵ����ƣ����Ǿ��ˣ�һ��������������Ϊ��꣬����������µ�һ������ǹ�ĺ��п��ܾ������������������Ķ��ӡ���
һ������ô˵���ϵ�����������������������ͩ�������˰������϶�����ʶ��������ʶֻ�¶������ʸ���ô���뵽�������˼ҵ������أ�����ҿ��Ը�������֤�����ǵ�������Ȼ̸���Ͼ��ԺϷ�����Ҳ�����ڰ�ǹ�Ӷ�����ͷ�һ����ĺ��ˡ���
����ͩҲ����ʡ�͵ĵƣ���֪���ϵ���������ס������֪���ϵ���������G�кܴ�̶��Ͼ�����Ϊ�����ǿ��㹻ǿ��Ĵ���������˲�������ֻҪ˵�������Ƿ�˾��Ĺ����������ܶ��˶���ɻ����֣����������������������ϵ�������Ȼ�Ͱ�Ȼ�����ˡ�����ǽ����������ܺ��£���G��֮ǰ��û��ô�£���������ô������Ϊ����Ҳ��֪������˭��������G�оͲ�һ����ÿ�����ź����γ�������Ժ˭��֪�����Ƿ�˾��Ĺ��ӣ����ϵõ�����Ҳ���ϵ����ְɣ����÷���ͩ���ӵ�ս�ľ���������һ��������ҡ���������磬���¼�Ϊ�����͵�����������������������»���ʲô�����һ�����Ͼ���ج�Σ�ʧ�ߵĶ����������꣬������ô���İ���
��Ȼ���ϵ�˵����ݶ����ˣ�������̯���˽�������磬�����治����ˣ��Ҹ����������Լ�������Ҳ�����ǰ�������澫�����˲��������㻹����������ɡ���˵����̾����������һֱ�ܾ��ص���Ϊ�ˣ���ȹ��ҵ�������ͩ���Dz�֪��ͼ�����ˣ�ʵ������Ϊ����ƣ��������ȥ�ˣ������ֺܲ��õ�Ԥ�У��ܾ���ǰ���и��ڶ��ſ��˴�ڵ������ң��Ҳ�ϣ�����Ԥ��ʵ�֣���Ϊ�Ҳ������۵����ֵ��ǡ�����Щ����������ί��֮�ʣ���ʵ���������ﻰ������������ˣ��ϵ�ȻҲ������������ƣ����û�д����������˵��
�����������б�Ҫ��������Ϊ�˸�������ֵ���һ��˵�����ҿ��Խ���˾��ҵ�����Ҹ��˵�ȫ�����ý���������ǰ�Ҿ���Ǯ����Ҫ��ƴ������Ǯ������������Ǯ���˷������ָ�������������Ǯ��·����һ����������£����ӻֲ̿����ˣ�˵�䲻����˼�Ļ�������˯������̤ʵ���ҵ�ʧ���ж����ص����Ӧ����������İɣ��������������û�����������Dz��ʺϸ��������Ϊ�Ҵ�С����һ���dz�����ļ�ͥ�г�����Ȼ��С��Ƥ�����˼Ҹ����ٱ��ӣ����������������ǹ���Ҹ����ˣ����ҹ������������Ƿǵģ�֪��ʲô��Ϊʲô����Ϊ��ֻ����Ϊ�ഺ������һ�����������Ÿɣ�����ʾ�Լ���ǿ���һ������������Ū�ɽ���������ӡ���磬��Ҳ�ǹ����ˣ���֪�����ߴ�·�������ͷ����Ψһ�ȱ������˵����һ�����ô�����ʱ���֪���Լ����ˣ�������������ͷ�����ܶ���ȴ�������ް߰�ʱ�����ʶ���Լ��Ĵ������ͷ��û�����ˣ���磬�Ҳ����Ǹ����ӡ�����
ͣ��һ�£�����ͩ�����˵��ȥ���������Ѿ��������ʣ�����˵����ȥ�����붼�����룬��Щ�绯�˵����º������������������һ�����ӣ�ÿ��һ������ֹ��ס����ʹ��������Ŀ��ܡ�
��û�м���˵���ϵ�Ҳ�����˳�Ĭ��Ȼ������Ҷ��˵绰������ͩ���ŵ绰�DZ���ཱུ�æ������������������������ͷ������һ���ﷸ������������ǰ�����˿ɳܵ�ͷһ�����������ˡ�ʱ�����գ������������ˡ������Գ�Ϧ�����������ˡ����ǣ����ܻ�ÿ�ˡ������
��3��
���˰�ص��ң�һ�������̾�������Ц��ӭ��������ͩͩ���°��ˣ��������̣��Ҷ�����ˣ�����ô�С�������ͩ��Ȼ����ͷ���ܲ������̽�����������˵�����ܶ�Σ�������û���ԡ���Ҳû�취������ͩ�����̴�С����ģ���ǰ����ĸ����ס�����µ�ʱ�����̾�ס����ĸ�Ӹ��ڣ�ĸ�����岻�ã������չ˲��˵�ʱ�����ķ���ͩ����������������̣�������������Ǽ����¡����������ٽ�����ĸ�ӽӵ��ˣ��У�������˵���̵�����ȥ���ˣ�����ͩĸ�ж����̹�ȥ���չˣ���������������������Ҳ���˹������������пڷ����и�������һ����ô�����ȥ������ͩĸ�����Ѳ��������������μ��׳����˵��������У�һֱ���ľ������չ��ŷ�����С�������DZ�����С����ķ���ͩ����ȫ���ǰ������������ˣ�ÿÿ������ѵ����ӵ�ʱ�����̶�Ҫ����˵�û���Сʱ���˻�������Ҳ�����������ѡ�
�ۼ�����ͩ��ô���ˣ����̻��ǸIJ��˿ڣ�������ǡ�ͩͩ��������֪ͩ������ʹ��˼���˥�ˣ�Ҳ�����üƽϣ�ֻ����ʱ�ܺ��ǰ�������������ͻ�Ц��������绰������ʱ������������ӵ绰���ܺ��ͻ����ѧ���̵�����������ͩͩ�ӵ绰����������������ˣ����
���̵��ϼ��ں��ϣ��DZߵķ��ԡ��桱���ǡ�ˣ����
����������ͩ�ս��ţ�ƨ�ɶ�û���������̾ͽ�һ�����˴л��Ķ����Զ˵�����ͩ��ǰ��������ȳԣ��մ�ģ������ء�������ͩ�ӹ���ͺ�����غȣ������Ӷ������ˣ����̿������ԾͿ��ģ��������ﻹ�У�Ҫ��Ҫ����һ�룿��
����ͩĨ��Ĩ�죺�������ˣ������Ҫ�������ˡ���˵������ɳ���ϵı�ֽ��һ������ط���һ��ɨ�Ӿ����ĵ����ӣ�������˾䣬���Ұ��أ�������ϰ���Եس���Χȹ���𣺡�һ��ͳ����ˣ�˵�Ǽ����±�ʲô�ģ����ϲ������Է�����
�������أ���
����ָ��ָ¥�ϣ�ѹ�����������ڳ�Ϧ�ķ����أ����������һֱ�����棬�ղŽ����Զ�������Ҳ��֨�����������������Ե�һ��Īչ�����ӣ����Դӳ�Ϧ���ȥ�����������˾ͱ��ˣ���ǰͦ��˵���ģ�����һ�����ڶ�������ʮ�䣬��ֿ���Ҳ��������ȥѧУ�ӳ�Ϧ����������ô�ţ���
����ô�ţ�������ͩ�����˱�ֽ��
����Ѿͷ������ܾ�̽�ӣ�����ʦ˵����Ӱ�츴ϰ�������̴յ�����ͩ��ǰ������˵�����ҹ�������Ҳȥ���������˱ڣ�����ô�����ġ���˵��Ϧ�⺢�ӣ�ȫ���˶�����������������ôһ�����Ծͷ�����أ���������İ����㿴�����������ӣ���˪��������Ƶģ���·�������ŽŸ��ߵģ����ž����ۡ�����
����ƽ��һ�㻰���࣬��һ˵���˾�ϲ����ྣ�������ͩ����üͷ���������ɴ�����ɳ������྿��ˣ�����������˼��Ҳ֪����Ϲ�Ӷ����ó���������˵ǿŤ�Ĺϲ�����Ե���¿�����ǿ�����ģ����ն�ȰȰ�����������ۣ��ù�������ء��Ҿ������ƣ�����ô����ôϲ����Ϧ�أ��ӳ�Ϧ���������Ǽ�����ϲ���ò����ˣ���Ϧģ�������úã�������С�������ڶ���ʮ�ˣ�˭֪���Ժ���ʲô�����Ҫ�����ڴ�ѧ�����������أ������ܵ����𣿰�Ӵι���������������鷳�������⺢���Ը����ºͣ��ɾ����ֵú�����ֻ��������ѵ�ת����������
������ȥ������������ͩ������¥��
���ߵ�¥�ݿڣ������ֽ�ס������Ŷ�����ˣ������Ƥ����������Щ����û�������ˣ��������˸��������ء�������ָ�ſ�����������ŵ�һ��ֽ��˵��������ɶ��������������˵��ʲôҡ�ڻ�����ɶ�ģ���
����������һᴦ���ġ�������ͩ��¥��ֱ�ߵ���Ϧ�ķ��ſڣ����������ŵģ��������ã�û��Ӧ���ƿ�һ��������������������ƵĶ����ڳ�Ϧ�Ĵ��ߣ�������ɢ���ģ�Ҳ��֪������ʲô��
����ţ���Ҫ������ȥ����ۼҲ�ȱ������������ͩû������˵��
�����������������������������һ��С���ˣ������������ϡ��������������ų�Ϧ������ģ�����������Ϧ���������ƽ���������ϣ���Ϧ���ߺ�����ÿ�춼���������˶�����Ħ�����������ù�������ˡ������������˳�Ϧ��С�����������һ������������ʲô�������ߵġ�����������ˣ�������˵�İ���Ϊʲô����ô���ˣ������ϼ��ң������Ϊʲô������
����ͩ�����������Ӿͺ������ɸ֣������ɵ�˺ò��ã����߿϶����������ɣ����Ѿ������ˣ�δ�����¶�Ҫ�����ǽ��������ܸ�����һ���ӱ�ķ�𣿡������������ߵ����ӣ�һƨ������ȥ���������㲲������������ݵ�����������ţ������ѵ�ɣ������������ʵ����Ϧ��������������ң�������Ҳϲ���㣬����Ҳ��������ѡ����������ң���������ҪԶ�߸߷ɵġ���֪��һ˵�⻰���ֲ����ˣ����㲻�ܻر����⣬�������Ǽ����������Ķ�Թ����Ժ��ԣ��������������û���ڸ��߹��㣬���������ȥ����ԭ�������е��ˣ��������������˵���⻰����û˵�����ܺ��Ե����𣿡���ô˵�ţ�����ͩ��ָָ�Լ����ؿڣ������ң�����һ����ɵĶ������Щ���Ҷ�û�취���ԣ������ܺ����ܺ�������˵�����Ͼ�Ҫ����ѧ��������ôƯ����Ů�����ڴ�ѧ���Dz���һ�ѵ����������ֵ�����������ô����ô�������أ���֪�����С�����Dz�һ�������Ǹ��������������е��ˣ���ʲô��ʲô���������ģ���Ϊ��Ҫʲô�Ϳ��Եõ�������ʵ�����������Ⱑ�����������㶼��ô������ˣ��������ʵ�ˣ�������������µ�ëͷС���Ƶģ�����Һ���˵�㣬��Ϊ���������Ҫ���˲��ģ���С�ͱ�����������������Ҳźܵ����㣬��Ϊ��û���ܹ����ۣ��ܶ������㶼���̫�����ˡ�����
����֪����Ϊʲôϲ����Ϧ�𣿡�
����ͻȻ�������̧��ͷ����Ŀ���ſ̹����ĵ����ˣ��ƹ�����ͩ�������˴��������ľ�ϣ�������Ϊ�����Ǵ��ӣ����ɵ�ˣ�ʲô�������壿�����磬��δ���������ң����Ƕ������������ң���Ϧ���Ҷ����ж���Ҫ�����Ǹ�����֪�������ǿ϶��ģ���������������������֮ǰ���Ҿ�����ʲô����������ô��֪���أ���
������˵�㸸����ԩ���°ɣ�������ͩ����������������֪���ò��࣬��������������˽�ġ�
���������ҡͷ�������ǡ���
������ʲô����
���������𣿡�
�������ǣ�����˵�𣿡�
���磬��ʵ�Ҳ��Ǹ����ˣ��������𣿡�
��ô˵�ţ��������ۿ����ͨ�죬�°Ͷ������ˣ����������ĵ�С����Ҳս����������ŵ�����������������ϣ����������߰�ӡ�ۡ�
����ͩ�����������ŵ����Ͻ��ù������˷ŵ������ϣ����ִ�ס���ļ����ô�ˣ���ţ��л��ú�˵��һ������ү�Ƕ���ô�������Ϳް���˵�ɣ�˵������������Щ���Ҷ������أ�����˵�����ż�������
�����ݺݵذ����֡��Լ���ͷ��������һ�ѣ����ʵ������磬����������ҵ�����������ˡ�ģ��������ˣ��ҴӲ�ȥ������ˣ�ʵ���Ǻ���ȥ�룬�Ǿ�������ĵ�һ�����˵IJк���������Ŀȫ�ǣ����������Dz������������ˡ�����
������˵˭����������ͩû�����ס�
���㲻��ʶ������Сʱ���������Ǹ��ˣ�����ʶ����ʱ�����պ�Ҳ�ǰ��꣬����Ϧ������ͬһ����ͣ�����Ҳ�ܿɰ��������С���ѡ���Ϊ���������½��ˣ������Ǽ�ס�ĸ�����������������Ӿ��ǵ��͵��½��ˣ��۾����ģ���ë�ر����˶�ϲ��������������Ҳ��ϲ������ÿ����·��������Ҫ�ƺ�һ�������Ϊ������Ů��������ˣ���������Ұֱ���ԩ���뿪�˲��ӣ��Ҿ�������Ҳ����������һ�������������ˡ���ÿ���ѧ���ᾭ�������������̯λ���������������ֵ��Ա߰ڰ�С���������Σ��Ҿ��������ߵ�ʱ����ż��Ҳ��̧ͷ�������ۡ���ô˵����˼�ǣ�������ʵһֱ���ϵñ˴ˡ���Ϊ��������ر�ϲ�����������������ʡ����ǮҲҪȥ�ö���֮���������ֶ��ϵ����ˡ�������������������˵����СŮ���ܿ�������Ϊ��û�����裬��˵���赱�����·����½���ʶ�����ֵģ���þ��������������������dz����ˣ�һ����سǣ����ɷ���鲻�ɾ���ʰ����͵͵�����ˣ�����Ů����֪��ȥ������ܲҵ��ǣ�����û�Ļ������ﶼ˵�ò������������йز��Ų��ң�һֱû�н������������������˵����ʵ�������Ǹ��������ˣ����������ϼҵ��˶���֪����ȥ���ģ��������½�������ô��֪�������������ģ����ŵ�ʱ�����������Ů���Ĵ�Ѱ�����ӣ�һ�������һ�ߴ������ӵ����䣬�Ӵ˿�ʼ����������������˵����dz����ʱ���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