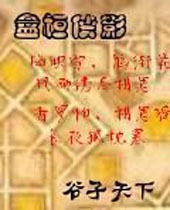征轮侠影-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挺刑,所以气力仍在,这一声悸亡魂,情急成疯,其力更大,杨以德当时吃他抱了个结实。其实马二并非是想和对头拼命,只为神经错乱,挨打时心里害怕,一急一迷糊,眼前一花,误把对头看成朝夕悬盼工部局派来救他的鬼子,一面猛扑上前将人抱紧,口方乱喊。“外国人快救我走,他们打死我了!”旁立卫士一见厅长被犯人抱住,当着情急拼命,俱都慌了手脚,一句也未听清,蜂拥上前,投鼠忌器,不敢开枪,一面撕掳,一面用手枪把乱打。马二失心疯,见状越发情急,抱得更紧,嘶声急叫,口中臭唾沫喷成白沫,死也不放,急得杨以德也顿足大骂混蛋,乱成一堆。最后还是一个卫士聪明,见马二力大如虎,分解不开,倒举枪把照准脑门心猛力一下,这才打闷过去,不再动转。人仍紧抱未放,又是四人合力才行扯开。总算马二没有伤人之心,又是拦腰一抱,只将衣服撕破了些,受了一场虚惊。杨以德自是大怒,喝令:“与我救醒转来重打!”卫士领命过去一看,业已脑浆流出,死于就地,只率罢了。
杨以德也真能干,当晚不令抬埋,先给工部局打一电话,令其转饬马二家属领尸。工部局因以前签得有字,闻说人被打死,大是不快,立即命人来办交涉,质问为何不守信约。杨以德闻说来了洋人,亲自出见,把脸一沉,令翻译回复道:“犯人可恶,屡次不守规矩,日前并对长官行凶,已照中国法律处治。前订条约只是不得枪毙,并无不得打死字样。如今尸首尚在,并未枪毙,不得谓之违约。贵工部局选用中国匪人在租界鱼肉乡民,侮辱官长,死有余辜,如今依法处治,贵局不细查前订条约,为一匪人冒昧出头交涉,实为遗憾。”外国人原想马二死得可怜,想给他家索笔赔款,以示待人厚道,显他租界权力,不料反碰了一鼻子灰。明知上当,无话可说,只得红了脖子回去拉倒。马二算是结果,黄七将来也自另有交代。
那周少章自被山西来人捉去归案以后,阿细因自己钱已用得差不多,年老色衰,如若回转南方,嫁人是决无人肯要,再做土娼行业管保连鬼也不会上门,又有那大烟瘾,不消半年便须流入乞讨之中,倒卧街头而死,想来想去无计可施,深悔由山西初逃走时应该带着那几千元私房逃回杭州,至不济也可活上几年,何致闹到这等进退皆难?连哭了十好几天,最后被她想好一条苦肉计,将余钱找裁缝做了一身粗布衣服穿上,壮着胆子跑上楼去,跪在益甫门前痛哭不起。
益甫本极恨她,因少章留别的信写得异常沉痛委婉,再四苦求,说阿细平日如何服侍周到,就有两口瘾也因前年侍疾所累,不能怪她,务求老父转饬孙男女家人格外优容善待,不可令其失所。益甫晚年来只此独子,一想媳妇早死,儿子年已半百,身边无人,只此妇是他心爱,现在难中,不知何年月日才可营救脱出,家中也不多此一人,又长得活鬼一样,想必不致于闹什么笑话,莫如养在家里,免这不孝子心中难受。一面给少章去信答应,一面令孙女儿转告阿细安分守己,不可出门乱跑。抽烟一层只作不知,也未禁止。这时见她突然上楼长跪痛哭,当是不耐孤寂想要求去,情出自己,当然乐得打发,便问她是何心意。
阿细痛哭流涕说:“少老爷待阿细情深义重,感如切骨,自闻被捕之信,心如刀割,无如身是女子,替他不得。昨天听四孙小姐说,少老爷山西来信,因孙总理托人发生效力,并未作寻常犯人看待,现已改交浮山县看管,单拨三间屋子,还准用人服侍,只等公款交出便可放回。虽然不在牢里,但是少老爷从小到老一直享福,近来年老,早晚均须人服侍,自己实在放心不下,一想起来便如刀割。好在老太爷有孙少奶孙少爷小姐服侍,用阿细不着,少老爷身边没人,打算求老太爷开恩,叫阿细到山西去侍候少老爷,一则报恩,二则老太爷在家也可稍微放心,不知老太爷准不准。”益甫竟为所动,暗忖少章本说她服侍周到,如今身在难中,有他喜欢的身边人随侍自然是好,难得这等人也会天良发现,少章来信虽说浮山县待遇极好,除不能随意走出大门一切任便,但令一妾随身服侍不知能否办到,且先去信问明再说,随对阿细允诺,等回信来了,看是如何再作计较。
阿细已接少章私下来函,说县里待遇甚好,只要有钱照样过瘾,此去无意扎好永久根基,抽烟既不为难,钱又可由少章向家中索寄,岂不比在家看人脸嘴要强得多?心中欢喜,表面仍装悲痛,说了许多好听的话,方向益甫叩了几个头走下楼去。益甫去问的信才发,少章也和阿细同样心思,第二日便与益甫来信,除催父亲去求孙伯岳设法营救使早出困外,并说困中岁月实是难耐,近又多病,无人服侍,日前已和主管人商妥,准其将阿细接往县衙内作伴服侍,务请老父即日派一妥人将阿细送往山西,惮不孝子身侧有人照料,免致终日优郁,疾病相煎,死于异乡,不能再承色笑。未了又说,主管知事虽念同庚之谊诸多照应,不与为难,食用仍须自理,尤其手底下的人不能不应酬赏赉,处处须钱。上次伯岳所寄的钱略微分散便自精光。初上来不得不开发,以后虽只三节开销,现时分文俱无。阿细来时盘川固要充裕,日后用度更为重要,务请转饬大孙儿雄飞设法筹款,或向孙伯岳借用,多多益善,统交阿细带来等语。
益甫看完信直摇头叹气,知道伯岳始终怀疑阿细存有私房不肯取出,营救少章已尽了不少心力,日前并已露出手边如若宽裕,便可代完公款将人营救回津的口风。并且少章初出事的第三天伯岳便寄了一千元到山西,没多少天又去开口,朋友帮忙应有限度,这样实在说不过去。他又认定阿细是祸水,少章官事全受她累,身在难中还离不开,要将人接去,仿佛只有此一人在侧,便牢狱之中也可终老之势,伯岳知道此事必不愿意,自己舐犊情深,凡百曲全,外人决不见谅。以伯岳性情,一提此事必要拦阻,钱借不到手还生恶感,万提不得。自己手边又没有钱,雄飞外场虽较活动,但他用度大大,一时也筹不出多的来,心生闷气。盘算了一夜,只得先去孙家向账房支了三月束脩,一面唤来雄飞,将乃父的信与他看过,命其设法。雄飞皱眉答道:“孙儿连日手边也紧。依孙儿想,细姨娘最好不去,去了不但招声气,伯岳也不愿意。爹爹非此不可,又为爷爷省心起见,那有啥法?钱一时决筹不出,爷爷只孙家几十块钱零花,如何可以拿出?爹爹知道心也不安。孙儿看细姨娘必还剩有几个不多,她只真心跟爹一世,孙儿自会使她自己取出。爷爷不要拿钱,盘川由孙儿想法子筹。爹在山西用度叫细姨娘先垫一步好了。”
雄飞随令人把阿细唤来,晓以利害,告知现时山西方面已然托好人,准其前往随侍,不过借钱路子只有孙家,伯岳已允不久可以代还公款将人接回,再去开口恐生反感有误大局。自己不久也有钱到手,无如远水不解近渴,你能先垫一步便去,否则作罢。你在此全家都难处好。我给你四十元川资,明日可自回杭另觅生路。阿细素怯雄飞,没奈何只得忍痛答道:“来时我虽有两三千块钱,自到北京便被老爷说运动差使两次要去,连在这里花用剩下的共总还有三百三十块,只要将来待我好些,我一定先垫出来好了。”雄飞道:“你既明白事体,将来爹爹好了决不亏你,去拿来吧。”阿细知道不拿出来不行,只得忍着肉痛泪汪汪将钱取到。雄飞随给少章写信,说:“一切照办,孙家现正托他官事,将来还要请他垫笔大款。尤其细姨娘为人素不赞成,实不便为此开口。目前家用尚称困难,无处筹款,幸而细姨娘尚识大体,自愿将私房钱取出三百多块,儿子又在别处设法筹到百元,除去两人路费,必能度用些日。以后来源困难,好在官司已有眉目,请爹爹放心。”益甫也加上一篇手偷,写了些诫勉的话,次日便命一老家人周祥护送阿细起身。到了山西浮山县,见着少章,阿细自免不了悲泣诉苦一番。
益甫祖孙初意伯岳人情业已托到,不久人便可以放回。不料阎锡山虽敷衍京中当局,不对少章严处,钱却不舍放手。只管下令优待,对于所亏公款仍非缴纳不肯放人。伯岳虽有代还意思,偏那两年运气不佳,先在俱乐部内连输巨款,而雄飞代他经营的盐号矿山本是发财的事,又以用人不当,互相舞弊,变为亏累,场面既大,内里却周转不开。伯岳又极重面子信用,闹得日常为难,如何能有余力代朋友完那过万公款,于是延搁下来。少章一直在山西羁押了三年,费了好些手脚人情,才把人营救出来。回到天津无事可做,伯岳知他遭此官事,一时不易营谋,看在老亲老友分上,聘他做了私人秘书,日常无事,便在家同阿细对灯抽烟,每日也去孙家走走。
少章只管生做阔少,嫖赌挥霍,正经花钱却极吝啬,又以遭了三年官司吃了点苦,烟瘾越大,嫖场已无意涉足,人越变得小气。他和周元苏之父怡甫虽是叔侄,年岁相差无几,志趣却迥不相谋,只管少章穷时往寻乃叔有求必应,但是周氏礼教之家,尊卑分严,怡甫一面全力救济,总免不了以胞叔的身分诫勉几句。少章每值穷途,惯以忏悔自责为护身符,表面悔愧,极口认错,自称该死,心却怀恨,背了人仍是故态依然,我行我素。怡甫病故,电信到津,少章知道怡甫近年境况日非,挂牌未久,平素又以清操自励,身后一定萧条,两老弟兄偏是手足情厚,老父如知此事,伤心尚在其次,必要为他遗族打算,至不济也就千方百计筹点钱寄去,弄巧就许责成自己设法,明知早晚仍要知道,仍打瞒一天是一天的主意。头两次电信正落少章手里,早就藏起,没给益甫看。后接元苏北来的信,一面隐匿,告诫子女不令告知祖父,一面忙写炔信与周母力说北方粥少僧多,谋生不易,读书学费更贵得出奇。现众亲友光景俱非昔比,元称千万不可令其冒失北上,免至数千里长途跋涉,流落在外,进退两难。幺叔在南方服官多年,交游众多,无论读书谋事,幺叔新死,尸骨未寒,趁前人交情尚在,余热头上总还可有法想。满拟婶母妇人之见,不舍爱子幼年远离,必能挡住元荪,免得日后家中多一闲人,还须设法为他营谋。哪知元荪母子早打定了主意,并且深知大房不情,伯父虽然骨肉情重,眷念孤儿,无如过时的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少章为人素所深知,此次过津专为省候伯父,全没想要少章父子帮助扶持心意。少章却以为怡甫京中虽有不少父亲门人,大都多年不见,音问早疏,元荪姊夫只做法官,并不当道,乃姊又非同母,素来不和,断定元荪此来是想倚赖自家,心中烦恶,于是引出许多事来。
元荪到津之时,少章出困才只半年。益甫因少章由小至长都无善状,一直荒唐到老,一想起来便生气,尤其提到山西官事气得直抖,虽所说只本文十之一二,已说了个把钟头。元荪见伯父说时老泪盈盈,也不禁凄然泪下,再三婉劝,才用话岔开。益甫素爱元荪,认为吾家千里驹,数年不见便自长成,又是丰神俊朗,少年英发,心甚喜慰,一面唤来长孙媳为元荪安排卧处,又谈了些京中亲友近况。元荪见天已过十二点少章仍未回转,恐伯父年老劳神,连请安歇。益甫又命传话家人侄少爷务要好好侍候,用什东西只管开账,由诸孙男女服侍睡下。元荪随得益甫安卧方始请安退出。走到楼上卧室以内,因见伯父慈爱,期望真挚,想起亡父和远距数千里的慈母兄弟,好不伤感。这一班侄男女辈年纪均比元荪稍长,又都一同生长江南,几把江浙认作第二故乡,早想和元荪打听南中情况,一回房全拥了来。祖父已睡,无什顾忌,少年叔侄似弟兄,称谓应对上虽仍恭敬,别的均极随便,互相问询,谈笑风生。元荪心虽难过,见众人都在高兴头上,也不得不强为欢笑,陪同谈说。
谈了个把钟头,元荪沿途劳乏,又急于想写家信,想和众人说明早再谈,忽见门外走进一个面色灰白、身材瘦长、年近四十的妇人,一进门便对元荪道:“阿叔几时来的?这两年杭州、上海想必更热闹了吧。”元荪看那长相,知是少章爱宠阿细,含糊答了句“还好”。阿细随即坐下,诉那山西经历苦楚,又说少章没良心,全家相待刻薄,没拿她当人,只顾絮聒不休,一面又表示她名分上应是太太。众人也不理她,仍各问各话,掺杂一起。元荪自觉头昏,也不便得罪,几次想叫众人去睡,终不好意思出口。正在难受,忽听门外有一重浊口音说道:“年轻人真荒唐,问三不问四,几千里路跑出来,交津一带多少有本事、有资格的人都找不到一碗饭吃,一个二十不到的年轻娃娃就敢跑这远的路来撞木钟,简直笑话!我是没法给他想的。太太在哪屋里?快去请来做东西,我消夜。”随说便听脚步声音走向对屋而去。阿细撇嘴笑道:“你阿哥今天想必又输了,他简直一刻也离不开我,真个讨厌。”说时作一媚笑走出。元荪见了直欲作呕。因听少章分明取瑟而歌,心中有气,但是礼不可废,只得对雄图道:“我连日车上不曾睡好,你爹爹刚回来,还要抽烟消夜,人想必也累了,今晚我不惊动,明早再请安吧。”雄图应诺,率众向元称道了安置各自退出。元称忙取纸笔写好一封家信,上床安歇。
睡梦中,闻得车声辚辚,当天已不早,赶忙爬起,穿好衣服出到堂屋一看,壁钟刚指六点,全家静悄悄的不听一点声息,街上却是电车往来,声甚聒耳,暗忖伯父高年居此闹市,如何能颐养天和?几时能够小成事业,将伯父接去奉养些时呢?此时出去发信,不知邮局开门也未?正寻思间,忽见老家人黄发在扫天井,见元荪站在堂屋门前闲看,忙赶过来悄问:“二爷怎起来这早?我打洗漱水去。”元荪问明邮局发快信要八点才开门,便自回房等候。一会黄发打来洗漱水,又问:“吃什点心,请二爷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