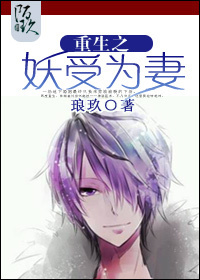与鬼为妻-第8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直到修路队的那个房子里面,还是没找出来,不过,不远处的灯光、人声传来,让陈阳没有那么紧张了,不管是什么鬼物,都怕人多,尤其是男人多,阳气足的地方,到了那里,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到了那里之后,其他早就回来的人不是在吃饭,就是在打牌,看到陈阳他们回来,就立刻招呼他们也过来玩几把,陈阳也没拒绝,走过去就接了那个喊他过去打牌的手,开始打牌,夜深了,人越来越少,熬不住夜的,不想打牌的,三三两两地离开了屋子,到最后,只剩下五个人在了。
陈阳手里拿着牌,有些心不在焉,周围人全都在抽烟,屋子里烟气缭绕,有点呛人。
突然,陈阳分明看到对面坐着的那个同事,变了张脸。
96、赌命
时间在缓缓的流逝;不知道什么时候;灯光变得黯淡了起来;周围的人;似乎都已经变了个样子;就比如坐在陈阳对面那个同事;时不时地,脸就变得毛茸茸的;像是一只兔子;而坐在陈阳左手边的那个同事,则手脚动作僵滞;脸色时不时发绿。
牌还在继续打着;坐在陈阳右边的同事;额头上开始渗出汗水,眼神惊恐,脸色惨白,一副随时会晕厥过去的样子,陈阳能感受到他的恐惧,他已经发现跟自己打牌的人,不是原来那个人了。
但是没有人动弹半分,也没有人敢说不打了。
周围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浓稠,让人喘不过起来,陈阳拿出一盒烟,递给了右边的同事,那个同事手哆嗦着把烟接了过去,中间有好几次,没拿稳,烟掉在了桌上,他手脚发抖地把烟又捡起来。
在烟雾缭绕中,对面那只兔子脸的同事,用尖锐得如同刮擦毛玻璃的声音,怪声怪气地说,“打钱没意思,我们换个筹码吧。”
左边那个同事接口道,“是啊,我们来赌点别的,你们没意见吧?”
陈阳他们当然有意见,右边的同事抖得更厉害了,身体一颠一颠的,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用求救的目光盯着陈阳,陈阳还没说话,那个变成兔子脸的同事伸出枯柴一样的手,狠狠地抓住右边的同事,用阴森低沉地声音说,“玩不玩,玩不玩,玩不玩——”
右边的同事脸色发青,想晕又晕不了,汗水跟下雨一样淌下来,“我,我玩,玩——”
桌面上又开始洗牌,到放筹码的时候,兔子脸那个,不知道从哪儿摸出一把刀,手起刀落,砍断了自己的左手,把还喷溅着鲜血的手放在桌,“我压一只手。”左边一直没说话,惨绿脸的同事,也不声不响地跟着砍了自己的左手,压在桌上,接着,两个已经放了筹码的人,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陈阳跟右边的同事。
右边的同事已经直接软倒在了桌下,连坐都坐不起了。
陈阳又抽了根烟,他不动声色地把手里的牌放回桌上,“这回我不压。”右边的同事听了,有样学样,从喉咙里挤出一句干涩的话,“我,我也不压。”那两个人也没异议,牌还是继续打下去,最后,陈阳赢了,右边的同事在他特意的关照下,也没输。
那两只血淋淋的断手,摆到了陈阳手边,陈阳深吸了一口气,一股刺鼻的血腥味传来,再这样下去,除了自己,这里所有人都会死,然而,又到底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该死的牌局结束,然后各找各妈呢?
周围的灯光越发的黯淡,几乎已经看不清手里的牌。
周围起了雾,雾气里也带来了一些“东西”,影影绰绰地站在屋子里,在围着他们这一桌上,在看他们打牌,屋内的气温随着这些“东西”越聚越多,已经越来越低,到了后面,也不知道是冷还是怕,右边的同事脸色已经发青,隐隐透着股死气。
陈阳暗道不好,他已经被吓得魂魄不稳,再这样下去,牌局还没完,他的魂魄就会被周围那些“东西”扯出身体。陈阳也开始有点急了,烟抽得更多,更凶,烟火气也能稍微挡一挡周围的阴气。
陈阳一直以为自己虽然说不上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也少有能让他感到恐惧的事情,但是现在,那种幼年时候对于黑暗,对于那些“东西”已经遗忘的恐惧全都记了起来,恐惧从心底升起,内心冰凉彻骨。
而他肚子里的阴胎,此时却骚动了起来,似乎在跃跃欲试。
下一局开始,兔子脸那个同事,拿出那把刀子,在自己的大腿上磨着——一刀砍不断,所以他就用刀子在血肉里磨来磨去,脸上还带着诡异的笑,陈阳也忍不住打了个冷战,这个场面,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像今天吴伯杀兔子时的情形。
刀在骨子上磨着,发出“吱呀吱呀”让人头皮发麻发酸又发痒的声音,他终于把左腿切断了,摆在了桌上,而左边那个惨绿脸的,像折树枝一样把右腿轻松地折断了,也放在了桌上。
旁边那些“东西”靠拢了过来,绕着牌桌子,一个又一个地缓慢行走着,陈阳闻到了一股腥臊味,他若有所思地看向右边那个同事,他已经被吓尿了,他连羞愧都顾不上,只是用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眼神,看着陈阳。
对于他的求救和信任,陈阳也只有在心里苦笑一声,他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要是只有自己,也许还能逃出去,可这不还有几个同事吗?难道能就这样看着他们死在自己面前?不说心里面会不会内疚,到了明天,他怎么解释这个事?还不得被当成杀人嫌疑犯,再把他以前地那些案底一查出来,问题就搞大发了。
有“东西”轻轻碰了一下陈阳,陈阳肚子里的阴胎在他肚皮上狠踢了一脚,痛得陈阳脸色发青,然而,那些靠过来的东西,却又往后退了一些,陈阳意识到这一点,心里一动,也许——
他不动声色地拿过桌面上的牌,又喊了一句,“不压。”右边的同事抖抖索索地也跟了一句,“不,不压。”惨绿脸那个嘎嘎不知道是笑还是哭地叫里两声,陈阳熟悉那个表情,赌徒拿个手好牌都会这样,不由自主地露出点兴奋和得意。
幸好,自己为了收拾那个出老千的,学过几手,不然的话——陈阳想了一下自己四肢被切断了摆在桌上的情形,手里拿牌的动作也停顿了一下,这一把,还是陈阳他们赢了,按道理,右边的同事应该剁了自己的一只手或者砍了自己的一只脚给他,陈阳想了一下,环顾了屋子,“他的,先欠着,其他人没意见吧。”
赢的人,愿意别人欠着,其他人顶多抗议两句,确实也说不出什么意见。右边的同事好像一脚踩空就要摔死的时候,被人拉了一把,充满感激地看了陈阳一眼。
牌局还在继续,陈阳突然把牌放在了桌上,不紧不慢地说,“都这么晚了,再玩下去,明天都没精神去上班了,玩了这一把,就散了。”右边的同事,在陈阳的示意下,抖着手,牌都拿不稳,“是,是啊。”
兔子脸的同事尖起嗓子,“不行,不分出胜负就要继续打下去。”惨绿脸那个,一直都没有开口说话,此时却突然间开了口,声音粗得就像千年老树皮,阴阴恻恻,去让人无法抗拒,“打下去,除非死了,一定要打下去。”
陈阳在心里骂了一句,我草,这是要老子舍命陪鬼吗?
不过,他也无可奈何,形势比人强,不过旁边的同事已经直接翻了个白眼,晕在了桌子下,陈阳没等旁边那些“东西”动手,拉住那个同事,啪啪几声,用力甩了他几个巴掌,打得他脸立刻肿了起来,嘴角还溢出了一点血,陈阳见了,反而松了口气。
他刚才故意用手指把那个同事的舌头抵在了牙齿中间,才打下去的,一口舌尖血,一来可以让他坚持下去,二来可以暂时震慑一下旁边蠢蠢欲动,想扑上来撕碎他的“东西”。
陈阳在等,等隔一天晚上就会出现的那只鬼出来,他可以感觉到,肚子里的阴胎在蠢蠢欲动。 陈阳的喉咙有点发干,他口很渴,这场牌局实在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要再这么多虎视眈眈,只要露出一个破绽就会冲上来把他撕成碎片的“东西”面前出千,真不是人做的事。
陈阳在心里庆幸着,幸好这种打法是赢牌的人,下一局归他洗牌,所以他才能做点手脚,他故意放慢了洗牌的动作,让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的“东西”全都能看清楚,这是必在看着他。
它有点怀疑了——只是还不太确定,牌桌也有牌桌的规矩,抓不到证据你就只能自认倒霉。
突然,外面隐隐约约传来一些声音,就好像有人在唱歌一样,幽怨而婉转的调子,在夜晚听来,更显得凄凉,当然,也更显得诡异。魏庄怎么可能会有人半夜唱歌呢?就是魏庄里那个出了名脑子有点毛病的魏三婶,到了晚上,也是老老实实地关门闭户,禁言闭声。
那声音断断续续地,时近时远,让人听了无法自持,简直要跟着伤心欲绝了,右边的同事已经是神情恍惚,表情扭曲到了极点,眼球暴突,脸上的肌肉抽搐着。
陈阳也有点心神动摇,手上洗牌的动作也有点僵滞,他额角的青筋暴突着,外面那个唱歌的“东西”是故意在干扰他,他抬起头,就看到对面那个兔子脸的同事在笑,在无声的笑,恶毒而狰狞,充满着仇恨,这个唱歌的,是他叫过来的,陈阳当即确定了这点。
在那个缠绵悱恻的声音还在继续,“君去远——奴心心那个念念——”陈阳闭上眼睛,再狠狠睁开,他手里的动作快了起来,只看到扑克牌在他手里跟个玩具一样,以快要肉眼看不清的速度洗着,洗了不知道多少遍之后,啪的一声,陈阳把扑克牌盖在桌上。
他呼吸有点急促,随着他的动作,外面那个声音,也突兀地戛然而止。
陈阳牵起嘴角,笑了起来,右边的同事已经是口吐白沫,神志不清了,刚才那一阵超越了极限的动作,让陈阳手都有点抽筋,他用极其缓慢地速度换了一口气,周围阴气太浓了,几乎已经结成了水珠子,此时,如果大口呼吸的话,会被阴气蚀体。
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兔子脸那个,拿起刀子伸到自己的脖子上,开始磨了起来,粗砺刺耳的声音在房间里响了起来,而左手边那个惨绿脸的,则直接把手放在自己的头上,用力一拔,那个头已经被他取下来,放在了桌上,陈阳放在桌上的中指弹动了一下。
这一回,开始就对陈阳很不利,那个晕过去的同事面前,也发了三张牌,不管你是怕,还是晕,这个牌局都要继续下去,不死不休,那个晕了的同事,也许没救了,因为人一晕过去,魂魄就不稳,罡火也降低,旁边那些“东西”已经围拢过去了。
陈阳手里的牌是前所未有的烂,他看了一眼,眼神一沉,这不是他应该拿到的那副牌,跟他打牌的那两个“东西”已经不耐烦了,他们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段,比陈阳在洗牌时做点手脚,无疑,要牛得多。
陈阳知道,这一回是没办法取巧了。
他额头上的汗水也开始多了起来,手心滑腻,就凭他手里的牌,这一局他输定了,虽然不甘心,但是他也不可能打得过眼前一屋子的“东西”,更不用说跟他打牌的,不知道什么来头的兔子脸。
就在牌局到了尾声,掀底牌的时候,一股阴冷把门吹开了,吱嘎一声,一个男人提着个白纸灯笼,不快不慢地走过来,他一进来,屋子里那些“东西”就纷纷往后退,一个个全都退到了屋子角落里,身体一半在屋外,一半在屋里。
那个男人把手里的灯笼一扔,那个灯笼就晃晃悠悠地挂在了墙上,而且,化为了一盏,两盏,三盏——不一会儿,整个屋子的墙上,就挂了无数盏白纸灯笼。
朦朦胧胧的光线下,陈阳看到自己的手指都是惨白的。
那个男人一进来,兔子脸拿起桌上那个血肉模糊的头,按在了脖子上,左右转一转,活动了一下,用尖利的声音喊,“魏林清,这个事跟你没关系。”
魏林清走到桌边,把陈阳拉起来,轻轻一笑,“怎么没关系,他怀着我的孩子,是我的伴侣,你难道不知吗?”
兔子脸尖笑一声,“他逃不了,四方阴煞咒,他逃不了,他害死了我的儿孙,迟早会偿命,你保得住他一时,保不住他一世,他就是那个命,克父克母,克尽家人,活在这个世上,不如死了。”
听到它的大叫,陈阳脸色有点发白,身体摇晃了一下,不等魏林清扶住他,陈阳的双手就在桌子上狠狠一拍,桌上的扑克牌都跳了跳,“老子什么时候死,该不该死,关你这只兔子屁事,老天要老子死还得看老子高不高兴,吃几只兔子,那是天经地义,你叫个屁。”还真没见过吃了几只兔子就吃出什么问题的。
兔子脸指着陈阳放声大笑起来,“你知道什么,你那个奶奶为了给你改命,散尽家财,可是你却吃了我的儿孙,犯了我的忌讳,我把你的命又改了回去,不然,你以为你屋里的人会死?他们都是因为你死的,都是你害死的。”
陈阳脸色青白,身上的肌肉都在轻轻跳动,翻滚的情绪让他胃部痉挛,想吐又吐不出来,他白着脸,抬起头,称得上平静地说,“好,好,原来都是你搞的鬼,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儿孙,都等着给我的家人陪葬。”
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抓住兔子脸,一口咬住他的脖子,牙齿深深地陷进了肉里,兔子脸没防备一下,一声尖叫,浑身冒出了一股股黑烟,不一会儿,就瘫了下来,陈阳把他扔在地上,一脚又一脚地狠踢着,“起来啊,不是叫的凶吗,怎么死在地上了,老子让你凶,让你在老子面前耍狠。”
此时,一直站在旁边的魏林清,拉住已经有点癫狂的陈阳,“他已经走了。”地上那个人,是他的同事,而不再是那个兔子怪,而旁边那个惨绿脸的,也不知什么时候,倒在了地上。
陈阳知道,今晚上的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
知道了那些事,他惨笑了一声,捂住自己湿漉漉的脸,他居然哭了,自他父母去世之后,他第一次哭,那个兔子怪,几句话就让他活下去的理由都快没了,站在他身边的魏林清轻轻叹了口气,他抓住陈阳的手,“克绝六亲不是你的命,是有人在你生下来的时候,把你的命和其他人换了。”
陈阳一听,狼狈地擦了把脸,“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魏林清却没有正面回答,“我答应过你,为你改命,会把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