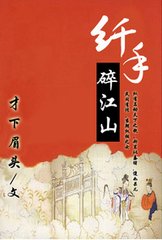纤手驭龙-第8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的安排井井有条,使人实在怀疑不得他乃是喝醉了酒。
闵、杨二人果然就在桌子旁边交拜成礼,又向裴淳行礼,裴淳亦跪下回礼。然后斟满两杯酒,要他们互敬干杯,这才斟满三个杯子,自己祝贺他们幸福美满。
杨岚仗着六七分酒意,毫无忌惮地偎靠在闵淳身上,闵淳也洒脱地伸手围拥住她,说道:“我闵淳何德何能,竞蒙娘子错爱垂青,实是平生之幸。”
杨岚道:“蒙君不弃,结为秦晋之好,妄身亦是梦想不到。”
他们在那儿倩话绵绵地谈起来,可就苦了裴淳,越发感到凄凉落寞,突然间冲动地站起身子。
闵淳讶道:“裴兄要往何处去?”
裴淳道:“我到楼下走动走动。”他平生都不打诳撒谎,是以闵淳完全相信。闵淳此来本有话要跟裴淳说,但这时却想到先让他出去走动一下,回头清醒一点儿始行商议不迟。况且他亦有不少话要私下跟杨岚说,这正是一举两得的好机会。
裴淳大步下楼走出酒家,略一辨认方向,便迅快走去。片刻间已走到薛府门口,但见门前甚是热闹,鼓乐吹奏以及爆竹之声不绝于耳。
他大步走入薛府,一个家人迎了上来,裴淳道:“在下裴淳,意欲求见薛飞光姑娘,烦你进去通报一下。”他若不是有了酒意,拋得开一切世俗礼教的束缚,那是万万不敢如此肆无掸忌地闯人薛府求见。
那家人迅即入内,禾久便回转来,道:“裴爷请这边走,时间无多,姑爷派来的花轿马上就到啦!”
这姑爷两字像一把利剑飕一声刺在他心中,他仿佛瞧得见自己的那颗心淌出血来。
他跟着这个家人走到一座院子门外,那家人道:“所有的人已奉命回避,裴爷请进去吧!”
院落内果然静悄悄的,裴淳跃人院中,叫道:“飞光,你在哪里?”
东首上房传出她甜蜜的声音,道:“我在这儿。”
他一跃而去,落在门前,正要伸手揭开那道门帘,陡然中止,道:“你当真要嫁给别人了?”
薛飞光自个儿在房内,身上全是新娘子的打扮,只差冠帔未曾戴上。她面颊上两颗可爱的酒涡已经消失了许多天,面色苍白,孤零零地坐在榻边,泪痕满面。
她本想立刻把姑姑的约定说出来,告诉他来迟了一步,若然是昨日来找她的话,整个命运就全部改变了,不但不会流泪眼对流泪眼,甚且可以遂双宿双飞的风愿。
可是她又想到何必把这件不幸说出?反正已不能挽回命运,徒然使他大为刺激,痛悔终身,于事何补,于他何益?
因此她终于忍住不说,这正是她的忧心体贴之处,宁可自己吞咽下较多的苦果。
她道:“你进来吧,我们好久没见了,你不进来让我瞧瞧么?”
裴淳一手抓住帘子,欲揭则不揭。他是想到“相见争如不见”这句话,目下正是这等情况,进去相见的话,恐伯只有相对洒泪而已,并无一点儿好处,反而弄得难舍难分,增加无限痛苦。
此刻他的酒意已消了大半,但仍然足够使他不顾一切地道:“飞光,我此来只问你一句话,那就是你能不能违抗三姑姑而跟我走?”
这句话如若不是隔住一道门帘,他再喝更多的酒也问不出口。同时若非这一道门帘隔阻,薛飞光怎生回答便只有天知道了。
她如被雷击似地呆了一下,才恢复神智,极力用平静的声音道:“对不起,我不能那样做了。”
裴淳蓦地揭帘而人,怒气冲冲,但他一眼望去,薛飞光并非如他想象那般平静,却是泪流满面。因此他本想狠狠地骂她几句,却已做不出来。
但他仍然不肯轻轻放过了她,冷笑一声,道:“那很好,听说那黄达又有钱又有面,你嫁给他那是一定终身享福无疑。”
他不让薛飞光有说话的机会,只赂一停顿,又道:“当然嫁给他的话,那是远胜于我这个穷小子,你向来十分聪明,这一点儿哪能看不透呢?”
在他嘿嘿的冷笑声中,薛飞光的大眼睛中泪珠一颗一颗的掉下来。她无法明白向来忠厚忍耐的裴淳,今日为何说出这等尖刻可怕的话?难道这个刺激竞能令他的性情完全改变?
她自知眼下纵然被他如何冤屈,如何的与事实不符,亦不能开口
纠正辩解。因为事实上她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这个事实已经足够了,说任何话都没有用。
裴淳冷笑道:“你见过你的丈夫没有?他乃是镖行中大大有名的人物呢!”
薛飞光拭掉泪水,道:“我们说点儿别的事不行么?为何定要说到那个人?”
裴淳纵声笑起来,轻蔑地道:“为什么不谈谈他,你今晚就要躺在他怀中……”
这句话不但把薛飞光伤得很厉害,连他自己也给伤了。他简直不能忍受幻想中见到她婉转投入别一个男人怀抱中的这个情景。
因此房中只有他的喘息之声,以及她低低啜泣之声,过了好一会儿,裴淳才道:“好!咱们别提他,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我还没有致送贺礼,你希望我送什么给你?但你须得知道我囊中只有十几两银子,贵重的礼物可送不起。”
这话又是近乎致命的挖苦,因为他先前已说过她那丈夫黄达季于多金,而他目下囊里中,只有十余两银子,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
薛飞光深深吸一口气,抑压住一切哀伤痛苦,第一次用平静的声音道:“你爱怎么做都行,但我现下却想知道,那一日我离开战场之后,形势怎生?”
裴淳怔了一下,心想她当此之时,尚有心情提到那些往事,可见得她其实并不十分难过,因此不由得暗暗愤怒起来。
但他为了风度起见,丝毫不肯流露出怒气,还扼要地把那一日直至如今的经过都说出来。
薛飞光沉吟一下,说道:“从上述的演变经过看来,分明是辛无痕姑姑决意重履江湖,掀起武林风浪,从她最近的举动,以及印证我平日听得有关她的事情,我敢断定她自从成名以后,事实上一直拿中原二老做假想的对手。不过她一直都晓得碰不过中原二老,加上情感上的复杂因素,这才终于隐于巫山。”
裴淳漫应一声,道:“若然辛仙子要跟家师比斗,我可不须担心啦!”
薛飞光道:“你错了,当世武林高手之中只有你最须担心,因为只有你的生死,加上李伯伯可能遭受折辱这两件事会迫使令师出山,而辛姑姑最近忽然作此重大的决定,可知她亦是最近才准备妥当,自信已有把握,因此我好奇怪她最近从何而获得这等自信?”
裴淳听到此处已感到似懂非懂,便茫然地点点头。
薛飞光长叹一声,说道:“到了他们这等绝顶高手相争的境界,纵有盖世之智,亦无所用,此所以我是否在你身边为你策划已不重要了。”
这话原是实情,但裴淳却寻思道:“即使你的智谋对我们有用,你亦不能跟着我们,说来做甚?”他这个想法自然是因忿激而生,不过还算他为人忠厚,才放心埋头付想,若是换了别人,那是非说出口
不可。
薛飞光不管他怎么想,又道:“照我的估计,李伯伯已落在辛姑姑手中,接着便要轮到你了,她将使用一种极厉害的方法对付你,以便借你这一次经历,推测出对付赵伯伯时的情形,她将用什么方法还不知道,或者多想几天便可找出一些头绪。”
裴淳冷淡地道:“不劳费心了,将来之事我自己当能应付。”
外面似是传来催促之声,这是新娘子就该上轿前往夫婿家的时刻了,鼓乐与爆竹之声一则使人心乱如麻,二则声声都如利锥刺心,使人感到痛苦。
薛飞光一手抓住他的衣袖,泛起乞伶的容色,道:“就算你不要我帮忙,但请你念在我们相识一场的情分上,为我做一件事。”
裴淳慨然道:“使得,我一生都是为人出力,何况是你呢?”话说出口,便感到好象把关系拉得太近,连忙又扳起面孔,冷漠地望着她。
薛飞光凝望着他,服中露出悲切的折求,道:“三天之后,你无论如何来见我一趟。”
裴淳双眼一睁,道:“什么?我去见你,你丈夫肯让你见我么?”
薛飞光摇摇头,泪水溅堕下来,她道:“不是到那边去,而是在此地。”
裴淳心已软了,很想答应她的要求,可是又觉得这样做实是不对,他终是笃行义理之士,当下坚决地道:“不行,我不能做这种偷偷摸摸之事。”
薛飞光忍泪连连哀求,他都不肯答应,薛飞光见他如此固执,真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可是却又很敬佩他这种正直不阿的为人。
她被迫无奈,只好使出杀手钢,顿脚道:“好!你不肯来我就去找你,反正不管找得到找不到,我的留书上都写明是找你去的,让世人都议论是你带了我私奔。”
若论智计图谋,裴淳自然远不是薛飞光的敌手,他听了大吃一惊,正在沉吟,薛飞光又使出攻心之计,道:“你来此与我会晤之事,我当然在事先跟姑姑讲明白,得到她的允许才行,这样就全然不是私下幽会,而是有事相商了,你怎么说?”
裴淳觉得“私奔”、“幽会”等字眼使人既刺耳又痛心,顿时心乱如麻,叹一口气道:“好吧!但我一定要听三姑姑亲口答允才行。”
薛飞光面色一沉,道:“你还信不过我么?我若不是为了格遵孝道和守诺不渝的话,我何必听话出嫁?你拿我当作什么人看待?你说!”
她一使出手段,裴淳便只有低头认输的份儿,当下说定三日后仍在此房之内会面。
裴淳可也有他的笨主意,那就是到时决计不踏入房内一步,有话隔着门帘说也是一样,总之,下一次会面虽然问心无愧,但嫌疑却不能不避。
他起身道:“我走啦!”
薛飞光娇躯一震,泪如雨下,突然伸手抓住他的衣袖,死也不放。
裴淳见她真情毕露,也自勾起自己的悲伤凄怆,付道:“她明明钟情于我,这是决不会弄错的事,要是命运如斯,偏生使我们凤飘鸾泊,永远分离,这等悲惨之事,怎不令人神伤魂断?”
他呆呆想了一会儿,亦不禁凄然泪下。
宙外夕阳斜斜照在院落中,靠墙边有许多盆景花卉,在残阳之下争饼斗艳,搔首弄姿,这本是十分平静可爱的下午,深庭寂院,使人心静神爽,然而他们却被离情别很所淹没,但凡一景一物,都足以触目伤情。
薛飞光在悲伤中,忽然升起一缕漂渺遥远的思绪,她仿佛从这满庭夕阳的景色中,瞧见了昔日旧居的恬静日子,那时候她从不谙识愁的滋味,只不过偶然之间掠过一丝少女的窃杏情怀,因而微微感觉到淡淡的哀愁。
但那一缕谈谈的哀愁却使她十分回味追思,恨不得多尝一点儿,每当黄昏日落,夕阳余辉投在庭院之中,她便默默地领略这种使她心弦颤动的景致,任由自己沉醉在退思之中。
她深知这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了,外面人嘈乐喧,一直提醒她快快结束这一段恋情。
于是,她放松手,走到门边,为他打起门帘。
裴淳一步步走到门边,眼中含沼,深深对她最后一瞥,然后跨过门槛。
她瞧着他的脚跨出摄外,心中想道:“他这一出去,从此萧郎陌路人了!”
裴淳也默默付道:“此情可待成追亿,只是当时已悯然!”
他离开薛家之后,仍不远走,竞在一条巷子中徘徊连连。
过了不久,鼓乐喧天,一顶花轿在许多人簇拥中经过,他乏力地靠着墙壁,以免跌倒,目送着这项花轿远去,但觉自己那颗心也随之而去了。
薛飞光在昏昏沉沉之中经过许多种礼节,最后,她忽然清静下来,原来已置身在一间布置全新的闺房之内,一对巨大的红烛映出红缎上那个金色的喜字,使她觉得十分刺眼。
新房中照例有合欢酒之设,红烛之下,银杯牙筷都反射刺眼的光芒。
一个瘦小的男子走人房中,正是刚才与她交拜过天地的新郎官,使婢们请新人人席,薛飞光理都不理,她一直没有瞧过那男人一眼,这时目光透过面纱落在那男于白靴上,心中悲哀地想道:“他就是我将要一生倚靠的男人了。”
使婢们把盛满了美酒的银杯送到她唇边,薛飞光一吸而尽,新郎官见了赞道:“娘子好酒量,今夕是大喜的日子,我们痛饮三杯。”
薛飞光酒到不拒,又连于数杯,她很希望借酒力麻醉自己,逃避这可怕的现实。
但她的丈夫黄达却不让她再喝,而且挥手教使婢们离开房。
薛飞光心中暗暗惊悸,忖道:“他要向我动手了。”此时她感到自己当真是个弱者,任人欺凌,又似刀组上的肥肉,等人屠割。
黄达在她身边坐下,笑嘻嘻道:“愚夫曾闻得娘子容貌美艳,文武兼资,真不知是哪一世积的德,修到今生福气。”
说时,伸手把她头上的冠帔取下,见她低垂着头,便又伸手托住她下巴,抬起端详。
他口中发出喷喷的赞羡声,又是直吞馋涎之声,说道:“娘子好生标致,当真大出愚夫意料之外。”
此时薛飞光面庞虽是向上仰起,但却垂下眼帘,没有瞧他一眼,如此反倒平添无限娇羞风流之态,那黄达瞧得火起倩热,抱住她便来亲嘴。
薛飞光本能地躲避他,但终让他亲在面颊上,那黄达也不十分粗野,放松了双手,道:“娘子出落得像朵鲜花一般,真是我见犹怜,愚夫虽是相貌丑陋了一点儿,但心地极好,又最会体贴人,娘子的这一生决不须忧愁,愚夫纵然是做牛做马,也要让娘子穿金戴银,安安乐乐的地日子。”
他词色越卑,薛飞光就越发泛起自怜之感,她恨不得倒在某一个人的怀中放声痛哭,一泄心头的悲根,但这当然只是妄想而已,事实焉能办到。
黄达静静地瞧她,薛飞光虽然直至如今都不曾望他一眼,却感到对方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她几乎听得见对方心中的计较,这使她感到甚是恐怖。
果然他缓缓移动,把银钩上的罗帐放下来,一面柔声道:“嫂子,夜已深了,也该安寝了。”
薛飞光娇躯一震,惊慌地向他望去,在灯烛交辉之下,瞧得清楚,只见他面上皱纹不少,相当的丑陋难看。
她险险反胃呕吐,心想:他实在长得太难看了,但我却须得与他同塌共枕,肌肤相贴……这么一想,更加感到恶心。
黄达龇牙一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