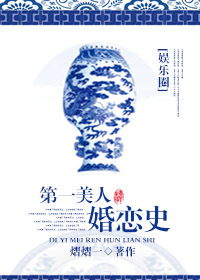文革恋史-第1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师娘知道铁戈爱吃粉蒸肉,特意蒸了一大海碗。
铁戈笑道:“师娘还记得我这个爱好,当年只知道搞阶级斗争,不懂得养身之道,而且那时候条件太差,能吃到肥肉就很不错了。记得有一次我和杨乐上夜班,晚上十二点我们去打夜餐,正好碰上食堂的任师傅当班,他让杨乐自己打夜餐,杨乐也不客气,拿起勺子把面上的肥肉全都捞上来,回到宿舍徐怀青和范火木到五七农场偷了一些大白菜合在一起煮,吃了个疼快,现在可不敢那么吃,健康第一。不过今天我要放纵一次,不能辜负了师娘的一片好意。”
杜师娘笑道:“铁戈我告诉你,你是张师傅最看重的徒弟,我是看你来了才给你做粉蒸肉,换了别人想都别想,我如今连饭都吃不饱,我还想别人给我做粉蒸肉吃呢。”
众人都笑道:“铁戈,这是真的,师娘看你回来了高兴,一般人她根本不买账。”
铁戈说:“师娘,铁戈何德何能,承蒙厚爱,我就愧领了。”
席间大家觚觥交错推杯换盏,回忆往事言谈甚欢。
酒至微醺时铁戈的徒弟吴国之突然举杯说:“铁戈,我敬你一杯。七六年春节收假后,车间书记金进财组织我们开你的批斗会,我发言批判过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内疚。”从那一脸的歉疚上看得出他是真诚的,这倒让铁戈始料不及。
铁戈赶紧站起来说:“老吴,多少年前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你怎么到现在还记得?大可不必。我那个时候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成了众矢之的呀。当年你是自愿批判我的吗?如果你不批判我你怎么过得去?光一个同情阶级敌人的帽子就够你受的。你那是奉旨批判,你不批判我你自己也完了,在座的哥们儿你们说是不是?而且你还有四个孩子,为我的事牵连到你,他们将来怎么办?当年你批判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与其让大家跟着我一起受罪,还不如让我一个人承担。你是个老实人,你今天说出这话证明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你和柴成明、沈少卿不是一类人。老吴哇,你比我大二十岁,按理说我们应该是两代人,但我又是你的师傅,我们算扯平了。别的我都不记得,我记得七四年你爱人采了一些松树菇下面条给我吃,那是我第一次吃松树菇,味道好极了,这事我倒是记得,你刚才说批判我的事你要是不提起来我真的忘记了。但是像柴成明、沈少卿这些王为仁的狗腿子我是不会忘记的,那是些正宗的人渣,不提他们也罢,免得倒了大家的胃口。老吴,三十多年了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在一起喝酒,八十年代有句话叫理解万岁,我们应该相互理解。来,为了荒唐年代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干一杯!”
师徒俩怀着真诚的感情喝下了满满一杯。
饭后大家都散去了,铁戈想再看看那些令他魂牵梦萦的车间,于是张师傅和徐怀青陪着他到厂房去。
张师傅告诉他:“这个厂已经卖给一个私人老板了,我们平时都很难进去。这几天老板的代理人回武汉办事去了,徐怀青又被返聘当了厂里的质检员,有他带路应该不成问题。”
铁戈带上数码相机,跟着张师傅、徐怀青来到厂区。
办公大楼死一般的寂静,厂区一片荒凉,野树杂草肆无忌惮地傲然挺立着,野兔野鼠旁若无人地穿行在树丛和草棵之间。当年他和徐怀青等人种下的楠竹如今早已长成大片的竹林,已然占领了半个山腰。那满坡的迎春花的枝条密密匝匝,时至深秋仍有不少绿叶犹如直泻而下的绿色瀑布,似乎在诉说着昔日残存的辉煌。
他们走进那个六千三百平方米的车间——当年红州地区最大的厂房,昔日机声隆隆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不见了。这里曾是电机、工模、水机车间共用的厂房,原来存放电动机、发电机的地方,竟然长出了一人多高的茅草,虽已枯黄却依然挺立不倒。窗户上的玻璃所剩无几,木制的窗户早已朽烂不堪。当年引以为豪的五米立车、八米龙门刨和各种机械设备早已荡然无存。头顶上二十五吨的行车也没有了,巨大的行车梁居然成了麻雀的世界,到处是飞进飞出的麻雀,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倒给这死寂的车间带来些许生机。
穿过大车间他们又来到铸造车间,拉开大铁门车间里到处散乱地放着木模,铸造用的各种砂箱随意地扔在砂塘里,木模和砂箱上一片灰蒙蒙的浮尘。那座高大的冲天炉已是锈迹斑斑,一副饱经沧桑的模样。在破旧的工具柜里铁戈看见那柄特制的大铁锤静静的立在那里,他有一种久违的感觉,用手轻轻擦拭着上面的灰尘,随手把那大铁锤拿在手上试图举起来,可是没有成功。
他颓然叹道:“当年我拿它打铁就像玩似的,现在倒举不起来了,唉,年月催人,廉颇老矣。”
张师傅笑道:“还以为你是十八岁的小伙子?你现在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小心别闪了腰。”
徐怀青提醒铁戈:“你不是要拍照吗?现在这里没人赶快照,以后就没有这种机会了。”
铁戈拿起相机拍下了锈迹斑斑的冲天炉、造型的砂塘和那柄大铁锤。他做这些事实际上没有任何用处,唯一的作用就是留到将来老了走不动路时拿出来看看也算是个纪念。
铸造车间是由造型车间和木模车间组成的,铁戈提出要看看木模车间。
出了铸造车间的后门,三人又朝木模车间走去。这里原来是一片平整的开阔地,是炉工班堆放生铁和石灰石的场子,如今却被一片不知名的茂密的树林挡住了通往木模车间的去路。
三个人艰难地穿过树林子进了木模车间,只见一个工人正在专心地看图纸,他只是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却叫不上名字。
那人倒是叫了一声:“铁戈,你怎么来了?”
张师傅在一旁说道:“他叫程矢志,是余师傅的徒弟。”
铁戈恍然大悟:“喔,我记起来了,你是七五年底转业分来的退伍兵,我那时已经进了学习班,所以不太熟悉。”
程矢志笑道:“记得记得。我刚来就听说铸造车间楸出了一个大反革命名叫铁戈,我对你倒是很熟悉。”
听他这样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
铁戈问道:“怎么就你一个人 ?http://。”
程矢志叹了口气:“厂子垮了,工人们休的休了,死的死了,下岗的下岗了。”
“你还没退休吗?”
程矢志黯然叹道:“木模工不属于有毒工种,要到六十岁才能退休,我还差几年,熬吧。我算幸运的,木模车间就只留了我一个人,多少还有点工资。冷作车间有两个人在搞电焊,金工车间有三个人上班,厂办公大楼有一个会计和一个出纳,再加上一个门卫和徐怀青这个质检员,一共只有十个人上班。这里冷清得可怕,我一个人就像是个孤魂野鬼,但是不上班我一家吃什么?”
“你家还有什么人 ?http://。”铁戈问。
“一个老婆,一个儿子。老婆是农村的,儿子外出打工去了,到年底才回来。”说着拿出一种劣质香烟给铁戈抽。
铁戈接过烟,却把自己身上带的好烟给他抽。
程矢志一看,问道:“这种烟多少钱一包?”
“极品黄鹤楼,六十。”
“天哪,这一包烟是我跟我老婆一个星期的伙食费!”程时志叹道。
铁戈道:“人家武汉卷烟厂从津巴布韦进口的烟叶,味道绝对纯正,当然要这个价,你一抽就知道。”接着又问道:“你们夫妻一个星期六十块钱的生活费够吗?一天十块钱都不到,这怎么过日子呀?”
“我老婆在房前屋后种了一些菜,还养了几只鸡,勉强过得去。我今生真是投错了胎,你们当干部的多好,什么都不做一个月几千块钱,我们车间大概就你混得不错。”
徐怀青说:“人比人,气死人,这就是工人阶级目前的生活状况。”
铁戈嘲讽地笑道:“还工人阶级呢,你真拿自己当棵葱。当年我就说过我们国家不可能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因为我们国家一直是封建社会,也就是上海、天津有一些资本家,他们的生产总值占国民经济GDP的比重是多少?根本够不上一个阶级,顶多只能算是一个阶层,要不为什么文革时说旧社会我们国家连一颗螺丝钉都造不出来呢?连螺丝钉都造不出来哪来的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哪来的资本主义复辟?所谓复辟是指把原来的东西恢复到原位,本来就没有资产阶级你把什么东西恢复原位,你复什么辟?”
程矢志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国家没有资产阶级。”
徐怀青笑道:“七六年在车间批斗他时吴国之的发言就有这句话。”
程矢志叹道:“下辈子老子一定要投胎到富贵人家,今生算是白活了一辈子,你们看铁戈抽这么好的烟活得多潇洒。”
“我也潇洒不起来,一个月也就两千块钱工资,在城里过日子也是紧紧巴巴的。”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要不你还抽这么好的烟?”
“你呀真不懂我的心事,八二年我从设备厂调走到现在二十七年了,回来看看总要有拿得出手的烟,抠抠嗦嗦不是老爷们所为。来,照个相吧,天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铁戈跟大家合影后,又拿着相机到处拍照,他不知道这座曾经挥洒过他们这些第一代建设者青春和汗水的工厂,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多长时间?他要把这里的厂房、这里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都拍下来,留做永恒的纪念。
下午徐怀青上班去了,铁戈又拿着相机在宿舍区拍照。
厂里的工人宿舍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工人的宿舍还是原来老水校的教室,整个广播大楼现在也成了工人宿舍,而铸造车间的宿舍仍然是五八年做水库时的工棚,透着一股岁月的寒酸。
他来到当年五七农场的农具房,这是他从安保处转移到厂里来的第一个学习班的住处。耳畔似乎又响起当年学习班里批斗他的吼叫声。他按下快门拍下了这个破旧不堪摇摇欲坠的小屋,转过身来他又拍下了电机车间女工宿舍,那里是当年何田田住过的地方。
接着他来到竺彬和他自己住的那排宿舍,这里的房子年久失修,比当年还要破败。墙上青砖的表皮已成粉状,就像白蚁蛀蚀过一样。屋顶的黑色布瓦上长满了不知名的植物,在风中微微颤抖,更增添了一抹凄凉的况味。门前的空地上的所有的桃树全都被砍掉,变成了私人的菜地。几只老母鸡悠闲的四处觅食,一只大公鸡十分警惕地护卫着它成群的妻妾。听徐怀青说竺斌终于把他父亲的案子翻过来了,但竺彬本人一九八八年出差时在火车上突然中风死在外地。他把这栋房子也拍了照,然后又朝厂部的办公大楼走去。
他在大楼前寻找最佳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
冷不防背后有人大声喝问:“干什么的?”
他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正警惕地看着他。
他恶作剧似的故意反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那女人说:“我是厂里的会计,你在这里干什么?”那声音颇有点责任感,令人想起了大抓阶级斗争的岁月。
他掏出自己的检查证递给那女人看。
谁知那女人一看笑道:“原来你就是铁戈,我们厂鼎鼎有名的反革命,我小时候见过你,我爸爸叫杨奎。”她的语气一下子变得很友好。
铁戈也笑道:“我认识你爸爸,老水校的,是个好人。你爸还好吧?”
“去世了好几年。”
铁戈一听叹道:“真是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小杨,我怎么不认识你?”
“你去坐牢时我还在上小学,你怎么会认识我?我倒是认识你。你会打球,歌也唱得很好,那时我就是你的粉丝。”
“哎呀天哪,想不到我还会有粉丝?太抬举我了。我该不是你呕吐的对象吧?”铁戈大笑道。
小杨笑道:“没想到你还蛮前卫的嘛,连这种新潮的词儿都知道。你到这里拍照是为什么?”说完她把检查证还给铁戈。
“留着做个纪念呗。”
“这厂都垮了好多年了,这些破房子有什么好照的?”
“唉,怎么跟你说呢?我问你,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人生最美好的是什么?是失去了的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你不觉得失去了的才是最宝贵的吗?人生最美好的时段是青春。七零年我们盖这些厂房时,你在做什么?”
“七零年我刚上幼儿园。”
“这就怪不得了,因为你没有搞过基建,所以你对这个厂没有多少感情,我们就不一样。当年我们流血流汗好不容易盖起了这座工厂,在这里学徒、生产、生活、恋爱,有的人还在这里娶妻生子。我们从少年变成青年,走进中年,眼看着就要步入老年,好多人甚至把命都丢在这片土地上了,能没有感情吗?多好的一个厂啊,说垮就垮了。就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没了一样,你说我心里是个什么滋味?这厂垮了你怎么还到这里来?”
“我是厂里的会计,有事无事必须坐班,好歹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工资,比下岗的那些人强,不然怎么生活呀?”
“啊,是这么回事。你去上班吧,我拍完了就走。”
晚上九点多铁戈又到宿舍区走了一遍,他想找到当年晚上到何田田宿舍的感觉。现在宿舍区没有路灯黑黢黢的一片,完全没有当年的感觉。有几家人在看电视,大多数人早已熄灯睡觉了,而在大中城市里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这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反差。他鬼使神差地再一次走到办公大楼的院子跟前,却只见铁门紧闭,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
四周一片漆黑,小北风悠悠地刮着,厂区里不时传来阵阵狼狗的狂吠。他把脸贴在铁门那冰冷的铁栏杆浸人肌肤,突然间不禁悲从中来,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脸颊潸然而下,人到了怀旧的时候就老了。
他颓然回到旅馆里,恹恹地靠在床头默默地抽烟。
忽然手机响了,一个似曾相识的陌生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
“铁戈,你还好吗?”
“我还好。对不起,你是……”
“你猜猜我是谁?”手机里是带北方口音蹩足的红州话。
“抱歉,我真猜不出来。”
“我是何田田。”这才是他等了多少年的哈尔滨话。
铁戈大惊,提高嗓门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