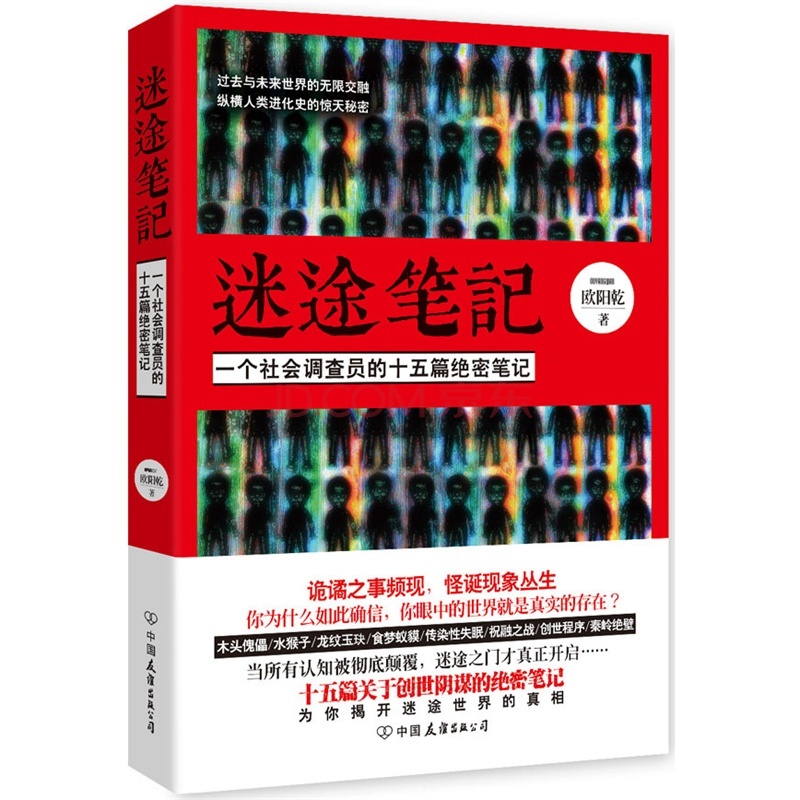死者迷途-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什么?”妞惊叫起来。
“二小姐听我说完,”我腹诽一遍,再说“可找来找去也没找着,我便索性来了大城。”
“恩恩恩。田哥是在疑虑还要不要再找?”
她满心期待,还是听见我说:“这样倒好了,前不久,我打听到门家的人还在冬——”
“什么!”
妞慌张了,“不行不行不行!田哥也不想吧?况且,况且还有妞呢。你走了,妞如何是好?”我吞吞唾沫,被盼嫁的娘子吓了一大跳,“二小姐,我就一个娘,绝不能忤逆她的遗愿……我们有缘无分,二小姐。”
“妞,妞不管……娘!”
妞哭哭啼啼的奔去后院,她这一哭,又闹成了赵家全体的事儿。
赵老爷子是个通晓事理的聪明人,虽明里放行,暗中定会差人去查。赵妈、赵大小姐留我多住,拖延时间,连不常晤面、在互市跑买卖的倒插门赵女婿也三番两次邀我喝酒谈心。而我,不紧不慢,不慌不忙,自在的度日,因心中了然,一个礼拜的时间不够打听远在南方的冬堂乡的消息。况且,以后还有的是机会见面!
至于妞……你要的是男人。男人的话,我还没及格呢。
天寒日短,风又刮了起来,剌着人脸生疼。花间巷独到的风,早间的第一拨,只因初作,尤其卖力。我窝在满园春窄道里,等待黎明。如此一声不吭走掉最好,不留泪,不留情,不知好歹,不晓虚实。只让他们明白,人走了,短时间回不来。
如今,我的欲望只是一碗热饭,一床安寝。奈何世间纷乱如麻缠身,等到大难临头,又死里逃生,又生不如死,活活受罪。像现在这般,继续苦心孤诣,期期艾艾,却还是无能为力,无法超生。都是男人害的。男人,你就是笨,从不开窍想想,那些逃开的,强扭的,真正见了面又何来顺畅可言,倒不如一拍两散,好聚好散。你有的爱,我也犯不着恨。
只是,你不放手,我哪里肯停留?
耳边嘎吱声响遂作,楼也颤,心也颤。
“呸,真他娘缺德!又撕了咱的红笺……”钟妈叫着,又骂门房:“你倒是多看着点!程老板都在催了,耽误了事你负责?诶——赶紧着,再写一张啊?!”
“是是是。”语罢,二人一前一后进了楼。
我一笑,自在的猫起身,却见红纸在腚下翻飞,上头只写着‘招工’二字。即便不招,我田妏砸锅卖铁也是要进这一楼,干这一行的。
敲开门,只说见工,便登堂入室。
不管怎样,先过钟妈一关。
籍贯姓名年龄一一报去,经验能力特长统统道来,一番考察,还不能定,上报程老板。女领导只扫了一眼。大概是因生意心烦气躁,见招工小事又来烦心,更大光其火,一脚便定锤,踢我至杂役房,两年约期,期间月俸三钱。吃住全包,生死相照。
带我的师傅叫付德顺,我先拜过,从钟妈手里过户,领了行头,又行至内院,又看姑娘楼,又识清楼上楼下,门前门后。
最后归寝,进了寝房。通铺上边卧满了人,棉被起伏,鼾声震天。
我早有觉悟,进屋轻手轻脚地铺好炕,小小心愿便在此动荡岁月中成形了。至于这屋子,我却一分钟也不肯多待。潮湿昏暗,臭气熏天,比福聚的住宿条件糟个千百倍。我出了门,瞟向天,秋意渐浓,兴许到了冬天就能好一点了。
安乐感上延,脑中便成堆成堆的冒人像,爸妈叔姨,鸢因宕妹,北家李家,统统都瞥我,这些指责与奚落如同闪着寒光,照在我□的、畸形的身体上,让我无处遁形,不得超生。
这般又苦恼起来,患得患失。
视线降低,映出门外方正的青石板院子。其左右对称着的是两栋二层姑娘楼,都教高墙围着,木门锁着,密不透风,暗无天日。左廊通厨房,右廊通外堂。要想上主楼、上姑娘楼,外堂旋梯请,不过,还请招呼一声程老板。
“程老板,”钟妈在喊,声音呦的一叫转过弯,觑向我,锁定我,“正好,你跟我来。”
“钟妈,这……”
接过笤帚簸箕,我一脸匪夷。
她魄力十足,不容质疑般,又高兴又焦虑又手忙脚乱,犹如换了个人。眼看她匆匆奔向外堂,我也只得尾随跟去。哪曾想,外堂早沸反盈天。姑娘丫鬟,笑闹成一团,硬是挤得旋梯水泄不通。钟妈扭捏着上了楼,见我杵在原地手足无措,又催促,又挤开挡路的丫头,又要拉我。一路来,耳畔全是女人的笑,咋呼声,闹腾腾,像有喜事可办。
莫非真有喜事?我不动声色,静观其变。行至两旋梯夹间的屋子,钟妈敲门得应,留我独守门外。
怎奈门扉虚掩,正容我窥其究竟。
“——城南的院子公子大可入住,无须客气。”只见门缝里,程老板挑着眉放下茶杯,极力挽留着,“还望公子给这个面子。”
对话的自然是个男人,就坐在飘飘摇摇的纱幔后,不清不楚……正待看清,他却站了起来,一袭棕袍熨帖于声,说话也掷地有声:“王某只是替令弟来传口信,无意惊扰,然已定了客栈,美意心领足矣——”
风起纱动,王筑这鬼祟男人的脸才显现出来。
他看了过来,我的窥视也戛然而止。
为何又是这个姓王的男人?简直是阴魂不散,罪大恶极!因他,我好端端的又把故人故事拿来想了一通,落差之大,即便再咀嚼消化,也徒劳无功,可恶!
头回见他,只觉得平平无奇。怎晓一经人栽培,受人抬举,便扶摇直上,出人头地。对于此人,却只能用神秘概括,尤其是他看凤招娣的眼神,我自始至终都未曾看透。他若是凤旖的旧相识,怎会久久不语。他敬的酒,他说的话,这般推敲下来又可疑之至。
烦这又要作甚?在‘现世’,我与他不过只有一面之缘,要脸面,何必来这种地方?
我眯了眼成缝,本本分分地躬身站好,又听见门内的声响。
“公子说的什么话,良寺的朋友,我良慈如若怠慢了,他可是要活剥了我的。公子可要体恤体恤,莫见人遭殃哟。”程老板三十七八,体态壮硕,说话办事精明简练,坏事损事无恶不作。就这会儿看来,又像别有居心,暗怀鬼胎。
空挡里,钟妈上前听候吩咐,须臾,便屏退而出。没得到准信,我心有不甘,却还是得跟着钟妈转至姑娘楼。
推开尽头的三间小屋,霉臭无孔不入,呛的钟妈猛咳。她怕熏臭了新围脖,嫌弃的退开,吩咐我让我把这里打扫干净,还要搬火盆来驱湿,火盆在哪,棉絮被褥哪领,都周到讲来,看她喜悦的,还并未冲昏头脑。
“敢问钟妈,这屋子……”
什么人要住进来呢?这么恶劣的地方。跟人一样,糟糕透顶,再掩饰也掩饰不了啊。我乍醒,眉拧成了几节,轮笤帚的手不觉又快了些。
“楼里的二当家要回来了,”钟妈继续捂鼻解释,“你才来,还没见过。到时候满园春又要热闹了,你先干,我去招呼招呼那些丫头,让客人见了还不丢了二爷的脸。”说罢,钟妈径自走开。
忙到中午,楼里渐渐冷清下来,肚皮却饿的咕咕叫。放下火盆,我揩拭了汗珠,揉着腰下楼去到炮房,翻找吃食。付师傅一早说过,暗门子的午饭都是申时才用,酉时开门迎客,三更陆续熄火,五更,即寅时才关门谢客。如此颠倒的作息,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窑子里来钱快,作龟奴的,愈是拿身体拿命在操在挣,脸面遭殃,还指不定惹上什么肺痨病祸。加上一通好找,却一无所获。我更加灰心了,靠墙根蹲了下去。
摸出一根卷烟。
想抽,冷锅冷灶,没火。
我猛然吸吸鼻子,裹紧了棉衣。决不能哭!哭一场也会染上感冒风寒的,所以,决不能多想!所以,就盯着卷烟吧!一直看,一直看,便能看到烟丝煋燃后的模样,闻到烟草的味道吧。光凭那味道,就能扯出光怪陆离的山川,扯出平坦的晒药材的筛子,扯出罕山那父女俩来。
罕山……已经是数月之前的事了呀。那父亲叫齐子广,女儿叫齐芳,就栖于这罕山上,以买山野草药为生。
那日被齐芳这村姑邀回家后,才发现她爹爹的本事。腿伤便是让这父女俩彻底治好的。小住罕山的时日,理应是最无邪的时日,可每每想起自己当初的见死不救,惭愧之情便攻心而来。不过好在又有‘福祸相依’这句话,才替自己解了围。
他们的院子是山的平台,晒满了一筛一筛的药,密密麻麻,好不惊艳。晒在角落的,经我发觉,才知那是烟草。
几经实验,才得到了眼前这一根粗糙的、却令人销魂的东西。我闻了闻,心头的痛仿佛被抚平,便像上了瘾般猛吸。饥饿也抵住了。羞耻心也淹没了。最后还是得站起来,投入工作,赚来热饭,赢得安寝。
——为了生活。
这么一说,我也无所谓什么羞不羞耻了,有命相见时再来探讨礼义廉耻吧!
——2010。01。28——
《死者迷途》廿某某 ˇ见习ˇ 最新更新:2010…02…03 09:09:09
自作孽,不可活!
夜来,人多的时候,我只能这样骂。
申时酉时,我如坐监,待众人一一招呼后,我才正式成为了满园春的‘杂役’。
窑子里的杂役一般分为堂子里端盘子、门子里震面子和巷子里跟腿子的这三类。各行要求不同。端盘子的嘴要甜,手脚麻利,会哄的客人多点菜;震面子的体要健,人高马大,能摄的客人少闹场;跟腿子的眼要尖,出楼入楼,定看的姑娘平平安安。楼里还有四位老鸨,皆由钟妈主管,姑娘二十余,当红的窑姐身边还跟着丫鬟,另外还有没主子的使唤丫头,厨子帮厨……
粗算下来,里外总共有几十号人呢。就打每人月钱以三钱为底,一三得三,二三得……啧啧啧,算不得,算不得,干这个行当,究竟月收入多少才能被称为‘削金窝’哟?
这不,天一黑,花间巷里的各大‘饭铺’便统统燃起了灯笼,一片酒红,蓄势待发。做买卖的小贩仍舍不得归家,继续倒腾着小物件,挣着今天最后一笔钱。卖小食,吹灯花,挑解酒茶的,也不惧怕沾上了胭脂酒味,回家不好受,都蹭在巷子里来往,叫卖,揽客。只有抬轿子的脚夫,规规矩矩地蹲在‘酒家’门口排成一队,例行公务般,等候差遣。
巷里的夜,自然与昼相隔天涯。
在‘家’,我就从没熬夜的劣习,来到这里,天黑闭眼也成了惯例。是呀,当初进楼的时候我就怕自己做不管、忍不了、藏不住,一项比一项可怖。但‘做不管’却首当其冲,硬伤不宜忽视。所以,比起身份、性别来,我对生理上的不适应还要担心上好几倍。
开张营业并不会因为我的胆小而延迟,酉时一过,我便忐忑地开始见工了。
付师傅先让我跟着他端盘子。怎样托盘,如何讲话,谁是谁,哪在哪,都细细交代,绝不贻误。我只能强记,比考四级英语那会儿还要努力。
“要看人说话,”付师傅夹着托盘,停步觑向楼下,“瞧见进门的人了吗?那是许季员外,他儿子刚中恩科。若是接下了,只说些讨喜的话,状元红,加官进爵(佛跳墙),步步高升(鸡腿),这几样菜便少不了。再叫来杜妈妈,祥珠姑娘今晚就有人翻牌子了。”
我哈腰点头,恭维道:“师傅真是灵通,什么消息都了如指掌。”
“干我们这行就是要消息灵通,田小子,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快下楼去吧,看看有什么细客,花生煮豆也给我好生招呼,师傅我这就去忙了,你小子万事留意。”付师傅塞给我托盘,又推我下楼,自己便恭敬地敲开了程老板的门。
看到程老板,我不禁又想起了王筑。事后我得知,他没有住下,这让我庆幸了好一阵,总算守住了一个不至于窒息的生存空间。
可是,即使是这样,我再怎么劝服自己,对他的敌意也不曾减少。
为何会这么突兀地仇视起王筑呢?想来想去,我也只能将此归罪于李岑格。因为,他与他,根本就如出一辙,都是心机颇深,城府渗人,靠面具掩人耳目的男人。不,不不不!李岑格更甚,他甚至从未摘下过他的面具,只晓得不断利用我,压榨我,替他自己消灾解难。
哼哼……只不过,他棋差一招,好端端的姻缘给阴阳两隔。又可惜,让我给想明白了。那夜的我,除了自悲,竟一无是处,更从未想过骂他,还……还像个□一样,抬着一张可耻的脸倒贴过去。他呢,甜言蜜语,照单全收。现在出事儿了,才说来找我、接我?哼!我看,这不过又是一层虚伪的、分文不值的面具。
对!一看到王筑,我就如同与带着面具的李岑格面对面,以前是,现在还是。
我之前不是就问过他“你当真叫‘王筑’”了吗,可他答的含糊其辞。绝对没错,他只是个攀龙附凤的俗人,光晓得自作聪明的给我献媚,引我注意,仅仅单纯的想借我上位。
凡夫俗子!
包括我。
在肮脏的地界上,又与臭男人同屋,又睡冰冷的炕、拉下九流的皮条,又点头哈腰、自称小人,还恬不知耻的听女人叫、男人吼。一夜如同数十载难熬,却只能忍气吞声,唯唯诺诺。我猜,我会‘死’在这里,犹如走卒,毫无良知。不,甚至更糟,甚至……变得跟李岑格,王筑他们别无二致。到时候,被这样的男人嘲笑,哪怕就一声,我便会羞愧而亡。
不对不对,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