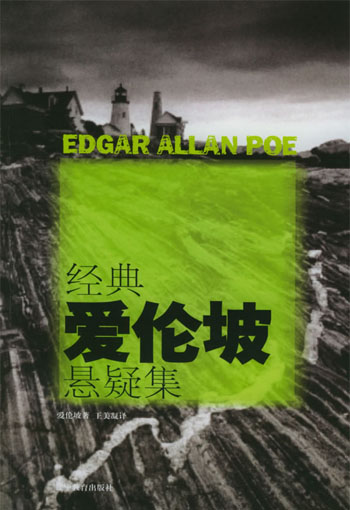爱伦坡经典悬疑集-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负着杀人的重担,我依然睡得很香甜。
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也过去了。带给我巨大痛苦的猫还是没出现。我这才重新自由呼
吸。哈!这怪物吓得逃之夭夭了!眼不见心不烦,我像是进入了极乐世界。杀害妻子的滔天
大罪居然只在心头泛起一丝涟漪。警察调查过几次,被我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他们甚至还来
搜了一次家,当然也没找出任何蛛丝马迹。我于是认为,将来的幸福有了保障。
不料,在我杀死妻子的第四天,家里开进了一队警察。他们又严密搜查了一番。藏尸的
地方隐蔽得超乎想像,我自然一点都不感到慌乱。警官命令我陪他们四处搜查,连旮旯缝隙
都没放过。搜到第三遍或是第四遍时,他们终于下了地窖。我连眼皮都没颤动一次,心跳平
静得如同睡眠者均匀的呼吸。我从地窖这头走到那头,双臂当胸而抱,简直是来回漫步。警
察完全对我放了心,都准备走了。我乐不自禁,为了表示得意,也为了让他们加倍相信我是
无罪的,我恨不得马上说些什么,哪怕就一句也行。
他们刚抬脚跨上台阶,我还是忍不住开了口:“先生们,承蒙你们不再那么怀疑我,在
下深感欣慰。祝各位身体健康。还望多多关照。对了,顺便说一句,这地窖非常坚固。”
(我越是想说轻松点,越不知道究竟说的是什么)“这地窖可以说建造得太好了。这几堵墙,
先生,要走了么?这几堵墙砌得很牢。”说到这里,我故作姿态起来,神经兮兮地抓起一根
藤条,冲着藏匿爱妻的砖墙使劲敲打。
主啊,把我从大恶魔的毒牙下拯救出来吧!敲击的回响尚未归于沉寂,就听得墓穴里传
来了回应。是啼哭声。哭声开头还瓮声瓮气,断断续续,像孩子的抽泣。随即迅速变成尖锐
的长啸,极为异常,惨绝人寰。这声声哀鸣,半是恐怖,半是得意,惟有地狱里受罪冤魂的
惨叫和魔鬼见到遭天罚者的欢呼交相呼应,才有这样的效果。
我当时的想法说来荒唐。我头脑昏沉,踉跄着走到对面那堵墙边。阶梯上的警察惊惧万
状,一时呆若木鸡。过了一会儿,才有十来条粗壮的胳膊挥舞着撞向墙壁。整堵墙全倒了。
那具尸首笔直地戳在大家眼前。尸首已腐烂不堪,凝满血块,头顶上,蹲伏着那只骇人的猫,
张着血盆大口,独眼里冒着火。原来是它捣的鬼。先诱使我杀了妻子,后用叫声报警,把我
送上绞刑架。我竟把这怪物砌进墓墙了!
(1843年)
厄榭府的崩塌(1 )
他的心儿是把悬挂的琴;轻轻一拨就铮铮有声。
——贝朗瑞那年秋天,一个阴沉、昏暗、岑寂的日子,乌云低垂,厚重地笼罩着大地。
整整一天,我孤零零地骑着马,驰过乡间一片无比萧索的旷野。暮色四合之际,令人忧伤的
厄榭府终于遥遥在望。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一瞥见那座建筑,心灵就充满难以忍受的忧
伤。说难以忍受,是因为往常即便到了荒蛮之所或可怕的惨境,遇到那种无比严苛的自然景
象,也难免有几分诗意,甚而生出几分喜悦;如今,这股忧伤的感觉却总是挥之不去。我愁
肠百结地望着眼前的景物。我望着孤单的府邸和庄园里单一的山水风貌,望着荒凉的垣墙、
空洞的眼睛一样的窗子、三五枝气味难闻的芦苇、几株枯木白花花的树干——心里真是愁苦
至极,愁苦得俗世的情感已无法比拟,只有与染阿芙蓉癖者梦回以后的感觉作比,才足够贴
切——苦痛流为日常,丑恶的面纱也摘除而去。我的心直翻腾,还冷冰冰地往下沉,凄凉得
无可救赎,任是再有刺激人的想像力,也难说这是心灵的升华。究竟的怎么了?我思忖起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在注目厄谢府时如此不能自控?这是个破解不了的谜。沉思间,模
糊的幻想涌满心头,却又无从捉摸。我只得退而求其次,自圆其说罢了——简单的自然景物
凑在一起,确实有左右人情绪的力量,但要剖析这种感染力,即便费尽心机,也是无迹可寻。
我思量道,这片景物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只消在细微处布置得稍有不同,带给人的那种
悲伤的感觉,可能就会减轻,或许会归于消泯。这种念头一起,我策马奔至山中小湖的险岸
边。小湖就傍着宅第,湖面泛着光泽,却一丝涟漪都没有,黑黢黢,阴森森,倒映出变形的
灰色芦苇、惨白树干、空洞眼睛一样的窗子。我俯视着湖面,浑身颤抖,比刚才的感觉还要
奇怪。
然而,目前我还是打算在这阴沉的府邸作几个星期的逗留。这座府邸的主人罗德里克。
厄谢是我儿时的好朋友。我们有好多年没见过面了。可最近,我收到了一封从本国一个遥远
的地方发来的信——是他写来的,信写得很急切,还非要我亲自去一趟。在他的亲笔信里,
显然透着股的神经不安的味道。他提到自己患有严重的疾病——是让他备受折磨的精神错乱,
还说,真的很想见到我这个最好的朋友、惟一的知己,能跟我快活地呆上一阵子,病情便会
减轻云云。全信如此这般说了很多。他的请求显然出于一片真心,让人片刻都不能犹豫。于
是,我马上就应邀动身了。来是来了,我却依然认为,他的召唤真是蹊跷得紧。
我们虽然是童年时代的密友,可我对这位朋友确实知之甚少。他总是有所保留,这都成
了他的习惯。不过我很清楚的是,很久以前,他的先祖就以多愁善感闻名。多少年来,这一
特点总是经由高贵的艺术品体现出来;最近,则表现为举办一次又一次慷慨却不张扬的慈善
活动,迷恋上音乐的复杂性,而不是热爱其一致公认、一听即懂的美。我也知道一个异乎寻
常的事实,厄谢家族虽历来受人尊敬,但却从未有过不衰的旁系子孙,换句话说就是,这个
家族属于一代单传,除了微乎其微、偶尔出现的例外,永远都是这样。想着这座房屋的特色
跟人们普遍认定的厄谢家族的性格极其吻合,想着好几百年来,房屋的特色有可能影响到厄
谢家族的性格,我不由认为,或许正是因为缺乏旁系支亲,才致使财产和姓氏总是祖孙相传,
世代相袭,最后财产和姓氏终于混而为一,庄园的名称渐渐消失,一个离奇而模棱两可的名
称——“厄谢府”,浮出了地表。庄稼人都用这个名称,在他们心里,这个名称似乎既包含
了这个家族,又包含了这座府邸。
我上面说过了,俯视湖水这一略带幼稚的举止,只是加剧了早先那种奇怪的忧伤。无疑,
这迅速弥漫的迷信感——何不就称之为迷信呢?——只会益发浓重。我早就晓得,惟有心里
胡思乱想,才会觉得恐怖。这是个荒谬的定律。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当我不再看那些水中倒
影,再度举目望着府邸时,我的心里就生出了奇怪的幻象。那幻象是那么荒谬,真的,我提
到它是想说明折磨人的种种思绪有着何其强大的威力。我这么胡思乱想着,竟然当真相信整
座府邸和整片庄园都弥散着一种气息,连同附近一带都沾染了这种气息。这气息与天空中的
大气迥然不同,而是从枯木、灰墙、死水中飘散而出,阴沉、迟滞、灰扑扑的模糊难辨,像
瘟疫一样不可思议。
我抖落掉心中那些只能说是梦幻的念头,更仔细地端详这座府邸的真正面貌。看来它的
主要特征,在于年代极为古远,时光的痕迹使它褪尽了鲜亮的颜色。墙上布满微小的真菌,
乱糟糟地挂在屋檐下,酷似蜘蛛网。不过倒也找不出破损得特别厉害的地方。没有一堵墙是
倒塌的。各部分配合完好,整齐划一,个别石头却碎裂了,看上去非常不协调。这使我不由
想起无人问津的地窖里那旧的木制品,多年来它们吹不到外面的一缕风,看似完整,实则早
已腐烂多年。不过厄谢府除了表面上的衰颓,整幢建筑看上去丝毫没有摇摇欲坠的迹象。如
果仔细观察,兴许能发现一条细微的裂缝,它就从正面屋顶上开始,曲曲弯弯顺墙而下,直
至消失在阴沉沉的湖水中。
我留意着这一切,沿着一条短短的堤道,骑马来到府邸门口。一个侍从接过马缰绳。我
跨进了哥特式的大厅拱门。一个蹑手蹑脚的男仆,无声地带我穿过一道道昏暗而曲折的回廊,
到主人的工作室去。不知为什么,一路上看到的景物,竟使我上面提及的那种含含糊糊的愁
绪,变本加厉了。周遭的一切——天花板上的雕刻、四壁黑色的帷幔、乌黑的地板、幻影似
的亦步亦趋发出“咔嗒咔嗒”声的纹章甲胄——我幼时就看惯了。我毫不犹疑地承认,一切
都很熟悉,可我还是很惊讶,这些普通的物件,怎么就激起了那么陌生的幻想!在一座楼梯
上,我遇见了他家的医生。他面露刁奸与困惑之色,他抖索着跟我搭了句话,便溜走了。这
时男仆突然打开门,引我到他主人面前。
我发现,房间极高,也很宽大,窗子狭长,尖尖地耸着,离漆黑的橡木地板老高,伸手
根本触不到。几缕微弱的红光,透过格子玻璃射进来,把四下里比较显眼的物件照得清清楚
楚。然而,房间远处的角落、雕花拱顶的凹陷处,却无论怎样都照射不到。墙壁上挂着深色
的帷幔。家具特别多,但几乎都不舒服,又过时破旧。四处散布着书籍和乐器,却并没有给
房间增添一分生机。我嗅到的只是悲伤的气息。周遭的一切都笼罩着阴沉、幽深、无可救赎
的忧郁之气。
厄谢正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见我进去,马上爬了起来,热情欢快地迎接我。我起初以
为这份热诚过了火,不过是这厌世者的做作之举,可瞥了一眼他的面容,确信是出于一片真
诚。我们坐了下来,有一阵子,他一语不发。我望着他,心里半是同情,半是敬畏。相信没
有一个人像罗德里克。厄谢那样,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变得那么厉害。我费了好大劲才认定
眼前这个人就是我幼年时代的伙伴。不过他的面部特征一直不同寻常。他面如死灰;眼睛大
而清澈,明亮得无与伦比;嘴唇有点薄,颜色暗淡,但轮廓绝顶漂亮;鼻子是精致的希伯莱
式样,鼻孔却大得离谱;下巴造型很好,但鲜有活力,并不引人注目;头发又软又薄,蛛网
一样稀稀拉拉;这样的五官,再配上太阳穴上面异常宽阔的天庭,那容貌真是令人过目不忘。
容颜上的显著特征,脸上一贯流露的神情,只消有一点夸张的地方,都会显得变化很大,如
今与厄谢同处一室,我却生出了对面不相识的感觉。眼前这苍白得可怕的肤色,明亮得出奇
的眼睛,尤其让我惊愕,它们甚至吓倒了我。那丝绸般柔滑的头发,也在不知不觉中,变长
了,蛛丝一样纷乱,与其说是披拂在脸上,倒不如说飘飘扬扬来得贴切。任我怎么努力,也
无法从这副怪异神情里,找出正常人的影子了。
我一开始就觉出了朋友的一举一动既不连贯,也不协调。很快我就发现,原来他的神经
极度紧张——他有着习惯性痉挛,他总想竭力克服这一点,却终是虚弱不堪,白费力气。其
实,对他这一特质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一是因为我看了他的信;二呢,我还记得他少年时代
的某些脾性;其次,从他独特的身体状况和精神气质上,也可以做出推断。他忽而精神高昂,
忽而落落寡欢;他的声音上一刻还优柔寡断,抖抖颤颤(此时听来全无生气),下一刻马上
就变得干脆有力。那生硬、滞重、空洞、不疾不徐的吐字,沉闷、镇定、运用自如的发音,
只能在沉湎酒香的醉汉或不可救药的烟鬼口中听到。他们受了烟酒的剧烈刺激后,就是这么
说话的。
他就那样谈着请我来的目的,说他如何诚心诚意地盼着我,希望我给他以慰藉。他还相
当详尽地谈到自以为得了什么病。他说,这是种先天性的疾病,是家族遗传,他已经绝望了,
不想再治疗了。他马上又补充一句,这只是神经上的毛病,一准不久就过去了。这种病的症
状,从他诸多反常的情绪中可以看得出。他一五一十全地告诉我了。尽管他的措辞和叙述方
式或许很有分量,但有些话我听了后,还是既感兴趣,又觉迷惑。神经过敏把他折磨得不轻。
只吃得下寡淡无味的饭菜;只能穿某种质地的料子做的衣服;所有鲜花的香味都难以忍受;
即便是微弱的光线,也会刺痛眼睛;惟有特殊的声音——弦乐,才不至于使他惊骇。
看得出,反常的恐惧已把他牢牢攫住。“我要死了,”他说,“我肯定是死在这可悲的
蠢病上。是的,就是这样死去,没有别的选择。我害怕将要发生的一切,怕是不是事情本身,
而是结果。一想到要出什么事儿,哪怕这事儿再微乎其微,也会使我精神不安,难以承受,
免不了就会瑟瑟发抖。说真的,我对危险并不憎恨,除了置身于它的绝对影响——恐怖之中。
在这精神不安的情况下——在这可怜的境地中,我觉得那样的时刻早晚都会到来,到时候,
我定会在与恐惧的卡怕幻觉中,丧失生命和理智。”
此外,我还不时从他断断续续、意义含混的暗示中,得知了他精神上的另一个怪状。他
摆脱不了对多年未敢擅离的住宅的迷信看法。他说,由于长期忍受,他家府邸的外表及实质
上的特点,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影响。他摆脱不了这种影响。灰墙和塔楼的样子,映出灰墙和
塔楼的暗沉沉的湖水,无不使影响到他的精神状态。在想像这一影响的感染力时,他用词太
模糊,我实在难以复述。
尽管一再踌躇,但他到底承认,追溯起来,如此折磨他的奇特的忧郁,多半来自一个更
自然也更明显的原因,那就是,他心爱的妹妹一直重病缠身——其实眼下她就要死了。多年
来,妹妹就是他惟一的伴儿,是他在这世上的仅有的最后一个亲人。“她一死,”他说,声
音痛楚得让我永远都忘不掉,“厄榭家族就只剩一个了无希望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