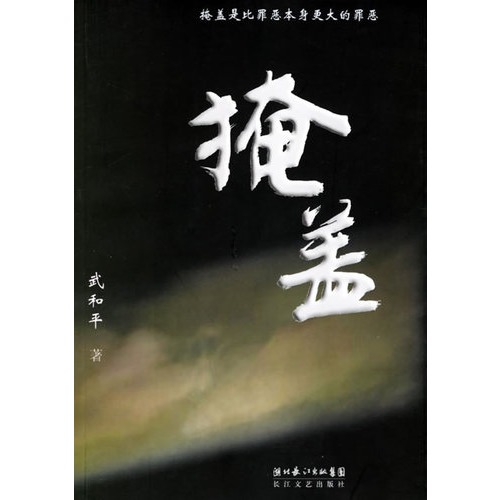掩盖-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经常代理老百姓打官司,天不怕地不怕,尤其不怕见官,省市领导的办公室他推门就进,遇到不平事他就告状反映,一张铁嘴得理不让人,区委书记区长也拿他没办法,这段快板八成是他给帮着编排的。
正说话间,从派出所门口走出一个矮个头宽脑门的民警,他走到张麦年面前帮助拎起塑料袋子,像碰上老熟人一样和他笑眯眯地搭话。就在这时,一辆北京吉普从派出所大门内开出,跳下来两个青年民警,架胳膊搂腰把张麦年连同编织袋子架上了汽车。不提防那袋子开了口,从里面滚落出了一本书和几个可口可乐瓶子,车上传出张麦年的呼喊:“俺的书,你们还俺的书!你们不能把俺拉到收容站,俺要告你们!”
严鸽注意到民警从地上捡起一本书,封面上印有《民告官手册》字样,随手就把它抛在了门旮旯里。那个宽脑门民警向围观的群众大声吆喝:“大家注意,时间就是金钱,该干啥干啥去,有事情到派出所的,抓紧时间办理,今天上午所里要开会学习,很快就要关门啦。”
不少人散开去,严鸽随着几个人进了大门,佯装询问暂住户口申报来到了户籍室,只听见对面会议室里传出讲话的声音,大概是宽脑门民警进去时没有把门关好,讲话人略带沙哑的口音不断传出来。
“要抓紧准备,首先是卫生,翟小莉你们几个‘坤角’可要听好了,戒指、耳坠统统给我去了,只准化淡妆,不能把嘴唇抹得跟吃了臭槟榔似的。你们几个和尚也不要笑,长头发、留胡子的今天立马坚壁清野、留短剃光。档案内勤负责把学习园地布置好,让写字漂亮的抄几份心得体会,警务制度、文明用语一律上墙,我说过多少次,户籍室要放上自动取水机和一次性口杯,群众来了得有个坐的地方。”
讲话人说到这儿起了身,大概发现身后的门开着,迅速关闭了房门。严鸽在那人转身的一瞬间,认出他就是当年分局刑警队的马晓庐,不知什么原因调到这里当所长了。
关了门,声音听不清楚了,严鸽不甘心,在院子里观察了一番,蓦地看到门后刚才民警扔下的那本书,她走过去捡的时候,发现靠房门后一扇窗户洞开着,隐隐传出了里边的讲话声。
“你们不要以为新局长是扎小辫的就不在乎,要知道人家可是吃过大盘子荆芥的,在咱们市干过刑警、法医,玩过技侦、外线,读过法学研究生,在刑法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讲话被一阵哄笑打断。有人插话,“所长,不是‘造纸’,是造诣。”“废话,别自作聪明,我是有意在考你们的。”
接下去还是马晓庐的声音:“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警服一穿就风度扁扁(翩翩〉的,不知自己吃几个摸、喝几碗汤了,我正式告诉你们,从今天起要严守警容风纪,随时做好迎接新局长视察的准备,谁胆敢砸了咱金岛所的牌子,我就敲了他的饭碗!”他突然有意把声音压低了,“你们有所不知,严鸽局长不仅是咱刘市长的夫人,还是和巨轮集团董事长孟船生光屁股长大,不对,是吃一个妈的奶长大的姐弟俩”
严鸽惊愕至极,没想到自己的正式任命还未下达,基层已经尽人皆知,而且这马晓庐对自己竟如此了如指掌,就连家庭隐私也一清二楚。
听到会议室散会的声音,严鸽才快步走出派出所大门,上了陈春凤的车子。现在轮到严鸽陷入了重重的心事,任出租车沿着金岛的环岛公路奔跑,她打开车窗,让清冷的海风灌进车内,吹打着自己的面庞。
远海处,少有的晴天使大海变得湛蓝,天空的白云像轻柔的棉絮飘动,和天际处星星点点的白帆融为了一体,由远至近的海潮,像一群欢笑的孩子列队而来,奔跑着,追逐着,在海岸边上化作了窃窃的絮语。
她眯上眼睛嗅着这熟悉的海腥味,眼前马上浮现出乳母那苍老而慈祥的面容,记起每次她到岛上来看望她时,老人总是给自己做她最爱吃的招潮蟹。她也最喜欢像小时候那样依偎在老人家的怀中,闻一闻那股熟悉而亲切的味道,看一看窗户前那棵粗大的皂角树和拴在树上的那艘破旧的老木船。那里是她的童年,也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一个部分,有多少次这种场景都那么清晰生动地浮现在她的梦中。
乳母的家就在前边不远路口,听说不久前被船生送到北京同仁医院做青光眼手术去了,这次调回沧海,以后孝敬老人家的机会也就多了。可转念一想,又多少生出了些禁忌,从刚才派出所所长的话里,分明暗示着她和孟家的特殊关系。看来船生如今在沧海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如何面对这个同乳兄弟,是她将要碰到的一个棘手难题。
时近中午,严鸽请陈春凤在路边小店吃了些便饭,告诉她要去看一家亲戚,待的时间要长一些,让陈春凤去先修一下车子。她独自一人走进了岛内的一个小巷子。巷子内很僻静,可以听得见海边鸥鸟的鸣叫,石块铺就的道旁飘着败叶,看来好长时间没人打扫了。推推门,竟是虚掩的,她走进院落,发现屋门大开,从门缝中向院落里边看,房门倒是开着,她喊了几声,还是无人答话。她诧异着走入房间,只见满是书柜的桌案边,一个矮个子干瘦老头儿正挥笔作画。一束明亮的阳光从窗间投下,把老人罩在一片有着极细浮物的光柱之中,对方正神凝气静,好像根本没有觉察有人进来。
宣纸上画的是一幅晚秋残荷图。只见老人用疏淡的墨色勾勒着参差不齐的叶茎,在肃杀的寒风中,几簇荷叶枝干焦枯,残叶凋零,但显得风骨犹存。尽管老人笔触笨拙,还真画出了点儿意境。
这人正是沧海市原公安局长孙加强。
接下去使严鸽大失所望。她本想通过老局长了解一下沧海的治安和局里的近况,不想对方给她来了个“莫谈国事”,反而大扯中国画黑白之间的玄机,谈什么初学者往往是黑白分明,到后来才知道黑中有白,白中有黑,而到了最高境界,则是知黑守白。末了,又将那幅残荷图送给严鸽,并要她挂在办公室揣摸欣赏。
从孙局长家告辞出来,已经是万家灯火了。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8
陈春凤已与严鸽相熟,从孙加强家驶向大船的路上,她告诉严鸽,自己要到医院看一下罗海,把她送到大船之后,8点钟准点返回来接她。并且告知了严鸽她的手机号码。
远远地,严鸽已经看到了孟船生的那件杰作。只见巨轮号在波光涟漪的海滨闪着迷离的光,巨大的远程射灯从老城方向朝这里滑动,船体在星光如织的夜空中显得蔚为壮观。
严鸽早就听说过有关这艘大船的种种传闻,依她对船生的了解,造这艘船是他由来已久的梦想。这个情同手足的弟弟从小跟着舅舅在海上打鱼,帮人修木船,做木工活,常常刻制大大小小的军舰和帆船,做梦都想当一名船长。如今,梦想成真,届时将在这里举行的盛大公益活动,这也当属民营企业给地方的一种回报。当然,船生此举肯定也包括着商业目的,诸如企业的形象包装、广告效应等等,但这些实在都无可厚非。
船生数学成绩出奇地好,其它功课却总不及格,因此屁股上没少挨乳母手中的鸡毛掸子。记得上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夏日,乳母给了他们姐弟俩一人5分钱买冰糕,严鸽的冰糕早吃完了,船生却只买了一个2分钱的冰棍,剩下的3分钱买了两个玻璃球,放了学和大一些的学生弹球赌博,一下子赢了2角钱,反过来又多给严鸽买了两个冰糕,惹得乳母好一阵审问,还以为是船生手脚不干净。现在看来,船生自幼就显露出经营的天赋。
金岛发现了金矿,船生的舅舅宋金元率先办起了乡镇企业采金选炼厂。船生跟着舅舅当助手,资产越做越大。舅甥俩致富不忘乡邻,这些年不断听说巨轮集团捐资助学、修桥铺路的好事。每每见到姐姐,船生总是拍着胸脯表示:自己决不会给干公安的姐姐惹什么麻烦。
严鸽信步走上了靠大船的环海堤,往日的海滩已砌起了整齐的护坡,环绕大船,铺成了平坦的水泥路面,临海一面的路边加上了护栏,间隔有序的地灯在一个个情侣椅边泛起淡黄色的柔光,像是给海岸镶嵌上了一串珠光宝气的项链。尽管天气转凉,这里还是有不少人在走动。严鸽有意避开人群,绕到船尾后的鲸背崖上,这里有一块延伸向大海的礁石,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船向海的一面。
这块礁石紧衔船尾,状如伸头的海龟,是块表面斑驳粗糙,背阴面布满藻类植物的硕大火成岩。严鸽攀爬上去,只见端下的海水已失去白日的柔媚光泽,显得昏晦如墨,一股股汹涌的暗流在黑暗中冲击着礁石,在深深的水底发出沉闷呜咽的声响,站在此处,严鸽方才看到了这艘巨大木船的背影,借着远程射灯移动的光柱,只见轮船向海的一面黯然无光,只有少数几个舱房亮着怪眼似的灯,对比另一面的灯火楼台,这一侧船体竟像月球的背面一样幽暗。严鸽闹不明白,这艘大船为什么造得如此表里不一,黑白各半。
此时,严鸽突然发现:大船的尾部有人影在闪动,影影绰绰可以看到几个人正在紧紧追赶着一个人,只见前面那个黑影飞快地攀上舰岛,爬上了高高的瞭望塔,追赶者也尾随而上。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之后,突然爆发出一声求救的呼喊,这声音在暗夜中显得声嘶力竭而又含混不清,像是被人突然扼住了喉咙。就在远程射灯又一次照亮船体时,只见高高的瞭望塔上,那个人影一晃,倒栽葱地跌落下来。光柱照在这人身上的一刹那,严鸽觉得那人像是被捆绑了手脚,并且头部向下垂直朝甲板上栽了下去!
没有片刻停顿,严鸽已经跳下礁石,绕向大船的进口处,冲上舷梯,登上甲板,有几个保安模样的人欲要拦挡,早被她拨拉到一边,并随手亮出了警务督察长的证件。这个证件正面是银白色的盾牌警徽,在夜间发出亮光,把几个保安顿时震住了。近处的灯光突然打亮,一个壮汉晃晃荡荡地走了过来,嘴里咕咕噜噜嚷嚷着:“谁也不行,没有请柬和招待券的一边儿待着去,少找不痛快。”
听着这个声音有点耳熟,严鸽借着灯光仔细一看,这人正是上午开悍马车跟陈春凤撞车的那个家伙。她便上前一步说:
“我找你们董事长孟船生。”
“嗬,敢这么大口气,董事长的名字是你叫的吗?”对方喷着酒气,把严鸽上下打最了一遍,腔调里带着淫邪的味道。
“我是公安厅的,姓严,马上喊你们董事长出来!”严鸽提高了嗓音。话未落音,船头的灯光突然大亮,照得前半部甲板像白昼一般,刺眼的光亮使处在黑暗中的严鸽一时看不清来人的脸,对方却无比惊喜地叫了一声:“鸽子姐!”
站在面前的正是巨轮公司董事长孟船生。
“欢迎欢迎,真想不到姐姐你会来,只听姐夫说这两天你就到任,咋也不让俺去接你一下?”船生说着就拉严鸽的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严鸽和孟船生握了一下手,和孟船生拉开距离。
“孟董事长,你的船上刚才发生打斗,有人喊救命,从船顶上摔下来了!”
“姐,怎么一见面你就来吓唬我?!”孟船生瞪圆了大眼,急得摇头摆手,“这里是全市文明高雅的场所,来的客人都是发请柬的,哪能出这种事儿?”他现在全然明白了严鸽登船的用意,话语里含着几丝委屈,回转身朝着躲在阴影中的那个壮汉大喊了一声:“咬子,你给我过来!”
咬子应声而到,先向严鸽鞠了个大躬,捏着嗓子说:“对不起,刚才确实误会了,我向领导请罪,下回再也不敢了!”
“胡说,瞎长对牛蛋眼,你看清楚了,公安厅督察长,是管警察的警察长,今儿成了咱沧海市的公安局长,这就是我常向你们说起的我那个最有出息的姐姐,知道不?!”
“对,严督督长,不,严局长。”咬子慌得战战兢兢,不知是出于对孟船生的惧怕还是对严鸽的敬畏,说话时两腿发颤,与上午撞车时那副恶煞神情判若两人。“严,严局长,刚才你说的事儿我担保没有,是不是有人闹着玩儿,还是大屏幕里演武打片儿传出来的声音”
严鸽没再理会咬子,径直快步向船尾走去,孟船生紧跑几步,回头向咬子丢了个眼色,忙给严鸽在前边引路,七八个保安打着雪亮的手电一齐朝刚才出事的地方走来。
在船尾瞭望塔的下边,绿色塑胶的甲板上,平平坦坦,空空如也。
严鸽伸手夺过一个强光手电,比照着与瞭望塔顶相垂直的地面,蹲下身子仔细查看,没有发现任何痕迹,这倒更引起了她的疑心:刚才的一幕她是不可能看错的。倘若那人是从七八米高的地方头朝下落地,一定会有脑组织或身上的体液溢出,而从自己登船到现在这段时间,对方就是清理现场也会留下拖扫的痕迹,可现在甲板上却纤尘俱无。
“嗨,严局长,你没看错,是有人掉下来!”咬子突然钻出来大喊,严鸽回过头,只见对方指定头顶的瞭望塔说:“这两天保安在这儿做攀登训练,八成是这帮小子们偷着练本事哩。”说完他拍了拍巴掌,顶上果然有人作答。
“你们都退出去!”严鸽继续沉着脸,一点儿也不理会咬子,要求孟船生等人都远远退到两边去,她立刻拨通了曲江河的电话,让对方火速派刑警支队的人员过来,并带上警犬。到了这一刻,她才觉得应该在沧海市浮出水面了。
不想曲江河那边接了电话,声音里却透着不快,一边揶揄着“不知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之类,一边不冷不热地说:“有那个必要大动干戈吗?那里可是警察的禁地,是刘副市长的重点工程啊。”严鸽心里明白,这是在抱怨她这个暗访者,全然没有把他这个副局长看在眼里,甚至在查他的小脚。好在曲江河是自己人,严鸽对此并未在意。不多时,现场勘查人员和警犬很快登了船,曲江河自己却没有来。
现场勘查很快结束,刑警们对甲板上的微量痕迹进行了吸附和检验,又让警犬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