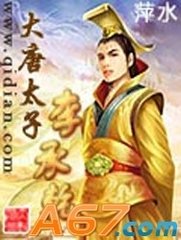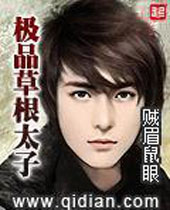太子为奴 by诸葛喧之(架空古代 宫廷侯爵 虐恋情深 强取豪夺 强强)-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那天起,正直善良的君王消失了,只剩一个整日饮酒作乐的昏君。薰妃的尸首不知被弃于何处,宫中所有与她相关的痕迹统统都被抹掉,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个女人似的。
就连逐渐长大的薰妃的儿子,都让君王无比痛苦。
他不想看到他,竭力地疏远他,到了年龄,便咬牙将公子送去了战场,这是他和她最后的羁绊,如果死在了战场上那么,一切都结束了。他对她的恨,对她的爱都结束了。
可是那个孩子却倔强地活了下来。
杀敌勇猛,建功立业。比所有的公子都要有魄力但他,却始终不愿意承认那个孩子。
他终究还是深爱着她的。哪怕那个女人曾经背叛于他。
每当夜色深沉,他还会梦到那天在刑场,喝下毒酒的薰妃,靠在他怀里,流着眼泪,笑得却那么轻松温柔,她对他说:“夫君,臣妾愿来世生于商国,不再与你为敌”
她是那么说的。
不舍。
不忍。
为什么要等到下辈子呢?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他想,如果她这辈子就能做他的臣民,不再是易北的棋子,只是他的薰妃,他最爱的女人,那该多好呢?
于是他在她命数将绝时,喂她服下了暗罗丹。
赐予她的毒酒,无药可解。可是暗罗丹可以吊住她的性命,让她像睡着了一般,陪在他身边。
她被他从地府夺了回来。
虽然她不能动,但她能听见他说话,听见他的爱意,他的苦恼,他的困顿和懊悔。
她就那么静静地,乖乖地听着。
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活死人,她的时间漫长的不像话。她知道自己开口说话,下地走路,便能结束这样的煎熬。便能魂飞魄散,不服受苦。
可是她终究还是没有动,就躺在永恒的时间里,一直一直,默默陪着那个孤独的男人。
这是她欠他的。
没有人知道薰妃还活着,除了王上,还有每日来给薰妃盘发梳洗的那个宫女。
王上喝醉了酒的时候,总会在她的病榻前哽咽着流泪,喃喃低语很久很久。
他对她说着他的痛苦,一遍一遍,一日,一月,一年她默默听着,却无法劝慰他,只能这样陪着他,陪他一辈子。
他们的孩子越长越俊俏,逐渐,薰妃的影子在他身上完全地重现了出来。
已经完全昏噩的父王,终于还是走出了最为人所不齿的一步。
他抱了那个孩子。
虽然强烈的愧疚感逼得他几乎要发疯,但每次看到那张似极了阿薰的脸庞,那样蓄意暧昧地诱惑着他,他就会中了邪一般,无可自拔地一错再错。
二十多年前那个沉稳正直的新君,已经和薰妃死在了秋风萧瑟的刑场。勤政爱民,慈父明君这些,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如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令人生厌的昏君。
纵使天打雷劈,亦是死不足惜。
“陛下每天,都必须要焚然致幻草,才能昏昏沉沉地睡去。”年迈的宫女坐在井边对苏越说,“他一直活在对自己强烈的厌弃中,也许他自己都没有发现,他身体里那个贤明的君王,从来都没有死去过,否则他也不会那么痛苦痛苦到,只能靠**活下去”
“殿下,您也许永远也不会原谅他。”老宫女说,“可我记得二十五年前,商国有个年轻有为的君王,他和薰妃都很爱你。”
这是老宫女投井自尽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作者有话要说:摸摸,不要鸟jj的翻页,昨天的更新原本就只有4000多字,的确是到苏越回头就完了,jj说的神马六千字是胡扯= =
我痛恨在下雨天出门,可是不得不出门= =晚上回来一起回帖~谢谢大家了~抱
45 苏醒
妖娆轻柔的桃花终归耐不住逐渐暖热的阳光,凋敝一地,零落成泥。
按照苏邪所说的,寻找到鹿峰草的解药到底不是难事。那枚玲珑小巧的丹药此刻就在苏越手心中静静躺着。
苏越坐在易洛迦榻边,凝望着沉睡的男人。
服下暗罗丹的人,心智意识都尚存在,能感知到外界发生的一切,却不得开口多言,亦不得下地走路。
他的母亲就是这样,孤独冷清地静卧在深宫之内,无人知晓,日复一日地煎熬着吗?
他用力闭了闭眼睛,这几日发生的事情已经让他心乱如麻,他几乎无法再清清楚楚地思考,干脆起身到了一杯水,将那粒小小的药丸投入水中,看着它缓慢地融化,逐渐将整杯水都染成淡淡的蓝色。
将易洛迦扶起来,杯沿贴着易洛迦枯槁的唇,把混合了解药的水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灌进他的口中。
做完这一切之后,苏越把杯子搁到旁边的桌几上,抱着易洛迦,安静地等着他苏醒过来。
不知是过了多久,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得几乎荒谬,他紧紧搂着怀里沉睡的男人,把脸贴在他温热的颊上。敞开的窗户洒进明朗晶莹的阳光,尘埃在光线下沉沉浮浮。
他恍惚又看见母亲在自己面前魂飞魄散的场景,细碎的齑粉泛着淡淡的光芒,前一刻还抚摸着自己脸庞的手指顷刻间消散无踪。
蓦然而生的恐惧感让苏越更加用力地抱紧了怀里的人,指甲几乎要卡断在易洛迦背部。
心跳在寂静古旧的小楼里显得那么突兀,口干舌燥的慌乱几乎逼得人喘不过气来。
漫长的仿佛没有尽头。
他失去了他的母亲,失去了二十多年那个温文慈祥的父王,失去了一颗良心,他曾经拥有的一切都流失殆尽了。
只剩一个易洛迦。
他再也不能失去他了。
怀里的人突然动弹了一下。极为轻微的动作,却让苏越整个人都僵凝住,甚至都不再敢呼吸,就这样屏着气,凝神听着。
“苏越”
手掌心里全是潮湿的汗水,他近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苏越”
他蓦然瞪大眼睛,低下头惶惶然看向怀里的男人。那个金发的贵族纤长浓密的睫毛轻颤了两下,随即缓缓舒开了眼眸,如同始解春水的透蓝眼底清冽地倒影出了苏越的脸庞。
贵族的嘴唇轻轻动了动:“苏越”
“”苏越想要出声唤他的名字,可是喉咙一哽,却是苦涩的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抱住他,眼泪流淌下了脸颊。
易洛迦虚弱地轻咳一声,久病的脸庞上露出一丝温和的笑意:“怎么了?哭什么?”
苏越用力摇了摇头,下巴抵在易洛迦肩窝,嘴唇都被自己咬出了血来。
易洛迦无奈而又宠溺叹了口气:“别哭了,这个样子哪里还有半点像你,快松手罢,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否极泰来,没料到易洛迦解毒的过程竟会这么顺利,没有出太多的意外。
易洛迦在客栈中休养了几天,整个人都逐渐精神起来,眼底的神采也愈发接近最初那个在易北舞会上风度翩翩的纯血统贵族。
只是醒来之后的易洛迦隐约发现了苏越的状态好像有些不对,总是精神恍惚的,有时一个人坐在窗前,望着那些浮沉的灰屑,可以发上很久很久的呆。易洛迦知道他的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苏越不说,他也不去过问。
他知道,把痛苦陈述给别人听,这并不是苏越会做的事情。而劝慰别人,也不是他的长项。
他便默不作声地坐在苏越身边,安安静静地陪他坐着,看着窗外的天空,直到獠牙穿日,茂盛的云层被绚烂的红色染成斑驳浓重的色调,瑰丽的深红,明亮的橙黄,绯色的云霞铺地整片大地都庄严辉煌起来。
他只会在苏越怔怔坐了很久之后,故作不经意地倒一杯温吞的茶水递给他:“喝吗?”
或者是替他批上一件外套,简单却细致地说一句:“起风了,披上衣服罢。”
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天。
易洛迦的身体已经痊愈,苏越却还是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易洛迦隐隐觉得,他是在等待着什么。
向苏越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坐在高高窗棱上的青年沉默了一会儿,目光投向远处层峦叠嶂的山峰。
“我在等那个人的葬礼。”
易洛迦一怔:“葬礼?谁的?”
苏越抿了抿唇,神色在辉煌的熟金色夕阳中显得那样令人捉摸不定:“我父王的葬礼。”
他说着,转过脸,逆光望着易洛迦。
“洛迦,再等等,国葬之后,我们便离开商国,好吗?”
那个男人对他而言,不知是怎样的存在。
父亲?仇人?还是,别的什么
他不知道。
只是那个男人死了之后,突然觉得心脏好像有某个地方空了出来,虽然并不疼痛,却非常的不适应。
他亲眼看见了那个男人的终结,如今,也想亲眼看他走完最后一程。
不是为了悼念,或是为了报复,只是想看着,棺材盖上,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统统关在黑暗里,和尸首一起慢慢腐烂。
从此以后,不论是多年前的那个他已经记不清了的温和慈父,还是后来恨到骨子里的昏庸君王。都不复存在了。
一切都结束了。
帝王崩殂的消息,因为许多原因被封存了多日。苏越不入王宫,也不知道情况究竟怎样了,每日窗下经过的百姓还是衣衫光鲜,谈笑风生,不知国君已逝。
苏越其实明白,父王这一走,他若不出现,新君之位必定是一场血雨腥风之争,苏睿和苏邪自然不必多说,连大权旁落的可能也不是没有。
可是这些,他虽心知肚明,却丝毫不想去管。
江山霸业说到底不过黄粱一梦,身死之后,照样一草一木也无法带走。又何必为了这样的虚幻之物争得头破血流。
空荡荡的浮华,他已经独守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的孤寂,是任何如画山河都弥补不来的。
几日后,遥远的边关传来了撤兵的消息,大约是林瑞哲将苏邪打得全无还手之地了,抑或是,苏邪接到了宫内的密诏。
这般风雨飘摇的时候,在外征战是极为危险的。
苏邪和林瑞哲,两个都是苏越无比熟悉的人,曾经那么重视,如今听到他们的名字,却如同隔了一层朦胧潮湿的冷雾,恍若隔世。
苏越有些疲倦了,所以的一切都该落下帷幕了,他那颗看似固若金汤的心其实早已被这些年来的凄风苦雨浸的残破不堪,再也没有力气多做纠缠。
只想着,守望完父王的葬礼,查明当年林瑞哲家人被杀害的真相,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弃下不管,和易洛迦同去一处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再也不问世事,直到终老。
他想,剩下的半辈子,应该会足够安逸祥和。
足够把他这二十多年淋上的血污洗尽,等到辞世而去的那日,或许就不会再像如今一样,有那么的痛恨和不甘,可以平静地离开。
平静地,作别这个流光溢彩,却又充斥着血腥和杀气的墟场。
商国国君的葬礼终于在晚春的时候来临,举国皆丧,白帛和凋落的春季残花一同飘零。
苏越和易洛迦一同去了山上,那里可以眺望见送葬的整条山路。易洛迦的金发在商国太过耀眼,就披着宽大的帽兜斗篷,淡褐色的衣料在风中被吹得哗哗作响,崖下一片山河锦绣。
葬仪队伍在远处划成一道蜿蜒洁白的河流,大风迷离了看客的眼,恍惚之间,便以为流淌过去的不是送葬的人群,而是商国先君的一生,那些温柔,安详,正直,肃穆,那些残暴,痛苦,丑恶,肮脏
所有的一切,在商国又一年的春风如沐中,悄然无声地化为一抔黄土。曾经执着的无法放下的爱恨,在满天飞舞的残花中,似乎都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了。
易洛迦望着商国波澜壮阔的宏伟景致,再侧眸瞥了一眼苏越。
那个少年静静立着,清俊消瘦的脸上全无半分表情,显得很冷很淡,说不上任何悲哀。
其实只要他站出来,这些风光如画,青山秀水,统统都是他的。万人称臣,独尊天下的地位也唾手可得。
然而那么多人寤寐以求的霸业荣光,身边的苏越却弃之如粪土。很多人都是这样,总以为高不可及的那个位置能驰骋御风了,纵览风光无限。其实等爬到那个位置,却发现那里只有凄惶的苍白一片,浮云遮去了目光,遍体生寒时,亦是无人为他披上一件冬衣。
王位,或许是一个有血有肉之人的坟冢。试问天下又有几人能真正把权位踩在脚下,而不是被责任和虚名压垮了脊梁,失去了本心呢?
易洛迦默默地伸出手,握住苏越垂在袖子中的单薄手掌。都说手薄的人,总是福源浅薄,苏越的这二十多年,忍受的苦痛,确实比他人多了太多太多。二十多岁的青年,本该是雄心未泯,壮志勃发的时候,可这个人的眼睛里,却已泯灭了所有的热忱和浮躁。
只剩下令人捉摸不透的深褐色,怎么也望不到底。
易洛迦轻声道:“如果你心里不舒服的话,可以跟我说说,有些话说出来会好受些”
苏越静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走罢。这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易洛迦望着他,眼底有一丝怜悯:“苏越”
“你以为我会难过吗?”苏越望了他一眼,“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如果不知道该怎么从黑暗里走出来,我十年前只怕就已经死了。自己选择的路,哪怕是跪着,哪怕是趴着,我也会没有一句抱怨地走下去,直到走出来,或者死去。我不会给任何人嘲笑我的机会。”
没想到苏越竟然会是这种反应,易洛迦愣了愣,漂亮的蓝色眼睛被阳光浸润成一种近乎于剔透的水晶色调,那种压抑过的欣慰在他脸庞上如同温暖的火光般点亮。
苏越抿了抿唇,反握住易洛迦的手,转身将大好山河抛在身后,竟是头也不回的决绝:“走罢,只剩最后一件事没有了断,随我一同前往问天崖,林瑞哲还在那里,我要去找他。若一切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那么,也即将在那个地方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