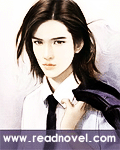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硖迳⒍丁R∫返奶秸盏乒夂雒骱霭担樟烈凰滞蜃吹难凵瘛�
学习中断了。年长一些的孩子被组织成后备军,每天参加射击、骑马、行军、防毒、救火等军事训练。年纪小的孩子则在老师的率领下,在宿舍和教室的窗户上贴上防止爆裂的“米”字条,在楼房的顶上昼夜值班,观察德寇飞机的空袭。
敌人逼近了莫斯科。
儿童院的孩子们被组织起来投入后方支援工作。男孩子们进入工厂,日夜不停地制造枪支、炮弹、燃烧瓶。女孩子们也到当地的服装厂、被服厂缝制军衣,到医院护理伤员。
大一点的男孩子们被派遣到莫斯科近郊修筑防御工事。每人的任务是每天挖一段长一米、宽三米、深三米的防坦克壕沟。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天气里,土地被冻得比石头还坚硬。一铁镐砸下去,地面只是迸出一个浅浅的豁口。孩子们的双手很快就被震裂了,手套被流出的血冻结在手上,摘掉时就像撕一层皮一样。孩子们嫌碍事,索性甩掉手套,赤手空拳地舞动锹镐。歇工时松开手,锹镐居然没有落下,手已经被一层血水牢牢地冻在木把上了。每天几个小时艰苦劳动,报酬却仅仅是一小块面包。不少人又累又饿,昏倒在工地上。
来自莫斯科的物资供应中断了。孩子们的生存陷入了困境。
可怜的一点黄油也没有了。每天三百克面包,只有拳头般大小。早饭是半片黑面包和一碗玉米面粥,中午和晚上是一两片面包,还有几个小土豆。孩子们大多十来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胃口如同无底洞一样。开饭的时间还没到,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守候在取饭的窗口前,心里不住地抱怨窗口怎么还不打开。吃饭的时候,孩子们总是用舌头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汤水。每次厨房洗菜做饭时,总有很多孩子在门口排上队。他们舍不得那些剥下的烂菜叶和果皮被扔进垃圾箱。
饥饿,是对这段可怕日子刻骨铭心的记忆。
刘爱琴回忆道:
“每天早上似醒非醒的时候,我总是似乎闻到了从前吃过的好东西的香味。蜷缩在被窝里不想睁开眼睛,唯恐香味会消失了。就这样一直等到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才忽然清醒过来。”⑥
第二章 烽火绿洲(4)
为了生存,孩子们开始学着自己种菜。
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把操场翻耕成了菜地,种下西红柿、胡萝卜、圆白菜。西红柿还青涩的时候,就被孩子们偷偷摘了下来,藏在枕头里等待它变红。圆白菜收割了,地下还留下冰冻的菜根。孩子们把它挖出来,如获至宝地捧到房间里,锁上房门就着冰碴狼吞虎咽。房间里顿时充满“嚓嚓”的咀嚼声,如同一群小白兔在会餐。
土豆是最主要的食粮。孩子们把土豆种下去。然后就每天蹲在地上,眼巴巴地看着淡绿色的小芽从地下拱出,数着一个叶,两个叶,直到枝繁叶茂。不等完全长成,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把土豆刨了出来,三把两把擦去表面的泥土,把土豆放到铁皮桶里,加水煮熟。不等冷却,孩子们就伸手从热水中抓出滚烫的土豆,一边在手指间掂着,一边敏捷地剥去皮,沾着盐大口大口地吞进肚里,然后从口中吐出大团大团的热气。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来自莫斯科的煤炭供应早就中断了。所有能烧的东西都烧了。教室和宿舍的墙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早晨醒来被子都冻在了墙上。孩子们的手脚都生了冻疮,手肿得像胡萝卜一样又红又亮。
儿童院要求孩子们行动起来,自己到树林里伐木,解决燃料问题,并且还定了任务,每人每天要完成一个立方米。
谁也没有伐过木。可是谁也没退缩。男孩子们一声呐喊,扛上斧头,就向着风雪的深处出发了。
一斧子砍下去,树干怦然战栗,树梢的积雪簌簌地坠下。一下,又一下,坚韧的树皮终于慢慢绽开。孩子们嘶叫着,疯狂地舞动斧头,仿佛在和巨大的敌人肉搏拼杀。帽子扔掉了,手套甩飞了,棉衣的扣子也全部解开了。汗水未及流下就冻结在发际,头发上、眉毛上、睫毛上都凝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洁白的雪花映衬着孩子们亢奋燃烧的瞳仁,一团团的热气在每个人的头顶蒸腾。夜幕降临的时候,孩子们满载着伐下的木块,唱着豪迈的战歌,如同骄傲的武士凯旋而归。
浓黑的夜色吞噬了万物。呼啸的风暴夹带着雪块与冰凌,如同一头暴虐的野兽,在空旷的原野上往来奔突。森林,田野,冰封的河流,在恶魔狂野的淫威下发出低沉的呜咽。暴风雪嗥叫着,扑打着门窗,抨击着墙壁,仿佛要将房子撕裂。然而国际儿童院依旧巍然屹立,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房间里,孩子们或搂着书,或抱着心爱的玩具酣然入睡。从窗口发散出点点柔黄的灯光,在冰晶中漫射开来,又交织在一起,如同一轮朦胧、圣洁的光环,笼罩着这一方生命的绿洲。
战争终于结束了。
陈祖涛'U1'和其他几个中国学生十年级毕业。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
按照规定,十年级毕业后,他们就算已经长大成人,不再由儿童院抚养。
刚刚经历战争严重创伤的苏联,物资极度匮乏。每天政府配给的口粮只有五百克黑面包,其中还搀杂了不少锯末。作为一年级大学生,每月从学校领到的助学金仅有二百七十卢布,只够在黑市上买四公斤的土豆。
为了填饱肚子,陈祖涛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就去莫斯科河的码头上帮人扛土豆。五十公斤重的麻袋落在稚嫩的肩头,压得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孩子们弓着腰,一路小跑,只为多赚回一些酬劳。深夜,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宿舍,煮熟土豆三口两口地吞下,赶紧躺下睡觉。明天还有功课和考试。
陈祖涛这样描述当时的窘境:
“苏联学生遇到困难,可以向家里伸手。我们真的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我们买不起新衣服。大学前三年身上穿的一直是离开儿童院前发的那两套衣服。我脚上的皮鞋也开了个大口子,脚趾头都露在外面。”⑦
艰苦,从来没有击垮青年们的生存意志。来自国际儿童院的教育告诉他们,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那样顽强地与困难斗争。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更有一个声音在回响: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等到回到祖国的那一天!
第二章 烽火绿洲(5)
就在学子们生活最窘迫的时候,祖国向他们伸出了温暖的手臂。
1947年,蔡畅同志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中途路过莫斯科。当她看到这群在莫斯科上大学的中国学生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呆了: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如同街上的叫花子一般。这个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前面不改色的坚强女性,把孩子们搂在怀里流下了眼泪:“我们把你们送到这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更安全稳定的环境,没想到你们过得这样苦。假如把你们留在延安,至少也能吃饱穿暖啊!”
情况很快有了转机。
蔡畅第二次到莫斯科的时候,给孩子们带来了几根金条,让他们换钱改善生活。为了既安全又能有个好价钱,同学们决定拿到首饰店去换钱。
头一次还挺顺利。第二次当陈祖涛到首饰店兑换黄金的时候,埋伏在周围的便衣一拥而上,把他押到警察局。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外国人,哪里来的那么多黄金?面对警察的讯问,陈祖涛坦言相告:“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后代,从国际儿童院出来在莫斯科读大学。因为生活困难,国内的亲人给我们带来一些黄金。如果想核实我们的身份,,可以询问联共中央领导。”警察部门的人一调查,发现事实果然如此,就把他放了。孩子们把黄金陆续换成了卢布后,终于换上了新衣服,吃饱肚子的问题也得到了根本解决。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好转,身在异乡的学子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来自故乡亲人的支持。1948年,中共东北局给中国学生们发来整整一车皮的食品和用品,有大米、火腿、皮蛋和白绸布。大米、火腿按需分配,随吃随拿;白绸布则每人一块,男同学用来做衬衣,女同学用来做裙子。礼物抵达莫斯科的那天,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赶来卸车,大家都喜气洋洋。面对苏联同学投来的艳羡的目光,大家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来自祖国的温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海外学子们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临了!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们欢聚在一起。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高喊“乌拉!”,激动的热泪肆意流淌。10月31日,新中国的第一任驻苏大使王稼祥抵达莫斯科的那一天,全体在莫斯科高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一个不少,都到火车站去迎接。那心情,就像迎接自己久别的亲人。
国民党的“大使馆”撤走了,克鲁泡特金大街十三号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从此,留学生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949年11月以后,使馆开始统一对留学生实行助学金补贴。孩子们的生活终于得到根本的改善。
1948年9月,前来苏联留学的谢绍明'U2'等一批青年学生,因暂时不能进入莫斯科就读,曾在伊万诺沃生活了一段时间。当他们进入国际儿童院的大门,眼前发生的事情令他们痛苦不堪。
操场上,有不少七八岁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孩子在追逐打闹。当谢绍明等用中文问候“你好,你叫什么?”时,孩子乌黑的瞳孔中顿时出现困惑的神情。他们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
年轻人们发现,这些在苏联出生和长大的孩子尽管在体貌上和自己别无两样,但是在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方面,已经和苏联人完全相同了。他们讲得一口地道的俄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汉语。他们对身边的一切了如指掌,却对自己的祖国一无所知。
随着中国教员的相继离开,在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失去了接触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机会,关于祖国的一切,在他们日新月异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这些孩子的父母,毅然投入艰难险恶的革命事业,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拥有一个强盛的祖国;而如今,他们自己的子女却失去了对故土的记忆。
1950年3月,年轻的留学生们由谢绍明执笔,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
“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批革命烈士子女和党的领导人子女去苏联留学。他们有的已经回国,有的已在莫斯科上大学。还有一些留在伊万诺沃念小学和中学。我们感觉苏联战后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生活条件艰苦,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有欠缺。这些孩子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对祖国也不了解。现在祖国已经解放,有条件让这批孩子回国接受教育。建议将他们送回祖国,待他们将来在国内学习有一定基础后,可再回苏联学习深造。”⑧
第二章 烽火绿洲(6)
1950年8月30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第一批三十名中国孩子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
如同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儿童院为每个孩子新做了大衣、帽子,还给每人发了一个新的小箱子,里面装满了书籍和玩具。每个孩子还获得了一大盒精巧的巧克力糖。
汽车徐徐开动了。孩子们把小脸紧紧贴在车窗上。他们看到,温柔的女教师们把脸深深埋在手掌中,双肩耸动;他们看到,小伙伴们追着汽车,奔跑、跌倒。他们睁大双眼,想凝刻下眼前的一切,可是视线模糊了;他们张大嘴巴,想最后呼唤一声亲爱的伙伴,可是喉咙哽咽了
再见了,这片养育了我的慷慨的土地!
再见了,这些在患难时刻救助了我的善良的人民!
再见了,我童年温暖美好的记忆!
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
回家的路是漫长的。
回家的心路更是艰难的。
当列车驶入中国大地的时候,孩子们看到的是战乱后满目疮痍的土地、凋敝落后的人民、各种各样“古怪”的民风民俗。一切和自己刚刚离开的那个国家竟是那么不同,竟有那么大的反差。孩子们惊讶地观察每一样事物,那感觉就像来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这些从国际儿童院归国的孩子们,在心理上都经历了痛苦的“闯三关”的过程。
首先是家庭关。
侯果力:
“列车到了北京。在站台上,我们站成一排,家长们也站成一排。先念学生的名字,被点名的人向前走几步。然后念家长的名字。两个出列的人,就这样对上了号,就这样相认了。现在想起来,就有点像认领东西似的,非常可笑。”⑨
有很多孩子,由于父母投身革命工作无暇照顾,一出生就成为“多余的人”,被送到儿童院抚养,因此对生身父母没有任何印象。就是大一些被送来的孩子,和父母也有十几年未曾谋面。如今,突然要对两个陌生的面孔叫爸爸妈妈,或者身边突然出现几个新的兄弟姐妹,即便血缘在召唤,心理上也一时难以接受。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还要承受来自亲人的异样的目光。所有这些,对于年纪尚幼的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
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孩子,从小形成了独特的家庭观念:院长就是父亲,女教师就是母亲,所有孩子不分种族肤色,都是兄弟姐妹,儿童院就是一个大家庭。如今,一下子要他们“背叛”自己的大家,加入一个个分散的小家,孩子们一时难以接受和适应。
其次是语言关。
这些孩子出生、成长在苏联的土地上,个个说得一口标准流利的俄语,汉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成了一群流着炎黄血液的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回到国内的家庭圈里,他们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也无法用汉语表达。语言的障碍造成心理的隔阂,很多孩子终日郁郁寡欢,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