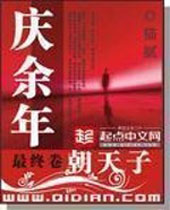����������-��34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Ƥ�������췴����
����������Ӽ�һ�������ɵñ����ˣ���ͷ���������Ե�Ҳ��������
�����������ڼ�����������ڶȰ������Ĵ�Ӫ������죬ȴ�������ˣ�����������۩�dz����ִ̿ͣ�С�����ȥ����žȻ�ȥ�ˣ���
����������Ӽ�һ������ը���ţ���е�����ԭ������ɽ�������ǾŽڶȵ����������������쳯�پ����潻ս��ֻ��ʹ�˷Ż������д̣���ʹЩ�����ĵ��ֶΣ������������ǹ���ɽ��ȴҲ������ˣ���
������������ͬ��ص���������ԭ����ڶ������˼����ﱻ�����˰������������������������������ͳ�ư��Դ����춪�ˣ���ڶ���ֻ�DZ����˼��������Ѿ��Ǹ��������컯���ˣ���
����������Ӽ�һ����һ���졪����ѽ�������⻰��ĥ����ô����ô����ζ���أ�������������Щ���������ӵ�����ֻ�����Ƶص��������ٿ��ǣ����ڶ�Ҫ������Ӫ����
�����������ڴ�ʱȴ����Ц�ݵ�������ڶ���Ҫ���ǣ���ȴ������ʹ���ã���
����������Ӽ����ˣ�б�������ںȵ������춼ͷ���Ҽ�������һ��������һ�������ĸ�����Ͻ��Ļ��ᣬ����㡣��ȴ�Ѳ������������ƣ��ٺ٣�ĪҪ��ڣ�������ֻ��˵һ�Ρ������ٿ��ǣ���
������������ҡͷ������ˡ�Ѵ�������
����������Ӽ�ŭ�����������۩���ص�СС��ͷ�����Υ�����ڶ�ʹ�ľ�����������ӷ�쭣�������ľ��������������������ܣ���ߵ����У���ǹꪶٵأ�һʱ��ɱ��������
�������������治��ɫ�����ݵ�������ڶȰ����ǵ�ͳ����˭���Ǹ�̫ξ���ĸ�������˭Ҳ��������������ƫƫ�������ˣ�������������Ƥ�ӵ��£��������̫ξ֪���ˣ������˼������죬�Һ����ֵܾ͵���ɳ�ŵ���һ�������û���ͷ���˭�Ե��ǿࣿ���������Σ������ֵ�ҲҪ���Ǵ̿ʹӳ����ѳ�������̫ξ��ǰ����ۿ����Ѿ�������˿���������۲�������æ����������ȴҪ���ǡ�����ʱ�������ҵģ���һ�̿ͻ��������������Ⱥ���ӳ���ȥ�������˼��ǽڶ�ʹ����̫ξ���������֣����ǿɵ�������ԩ��������
����������Ӽ���Ц���������Ǵ̿���ɱ���˵����ۣ�����Щ���۲����ּõ����£��ϻ���˵�������ӿ��ǣ����ӱ����Ǿ���ǿ����ץһ��СС�Ĵ̿ͣ��������ֵ���������
�����������ڶ�Ȼ��������ڶ���Ҫ�������ǿɲ��У������˼��Ѿ��ǽڶ�ʹ�ˣ�����ʣ������С���Ǻ��ˣ���һ��˵�����������ץ��ס�Ǹ��̿ͣ����������˼ҳ���ҲΪʱδ������
����������Ӽ�����Ҫ����ץס�˴̿ͺ�������ɽ��������һ��������Ȼ�Ǵ̿�Ҳδ��֪�飬���ܱ���������һ���ڵ�ǿ�������������������ģ����Dz������ţ���Ӽ�������ŭ�ˣ����´������ȵ�������С��������������ɫ���㵹����Ⱦ�����ˣ�����������ͭ�����������������������ٲ����ǣ����ӿɾ�Ҫ�����ˣ��������ǣ�
���������Ƚ����к����������������ε��顣ȴ��֪������Σ������»طֽ⡣
����ʮ���¡�������Ӽ�
��������һ����Ӽ�˵Ҫ���ǣ���ͷ����������ﶼ��һ����š�۩���سDz��ߣ��ز��������ϰ�����࣬�������ں�֮�ڣ��پ������Ĺ��ǣ�۩���ؾ�����һ��������
�������������ں����Ļ�ȴ�ô����ͷ������ڶȣ���Ҫ���ǣ�����۩���ޱ�û������˿��Ҳ�ֵ���ס�������ǣ���۩�ǵ����Ǵ��εijdzأ�����ڶȾ�Ȼ���������Ϊ�������������Թ�֪���ˣ���ڶȵ�����������ֻ����Щ�����ȱ㡣��
����������Ӽ�һʱ��ס�ˡ�ȷʵ����˵�ǹ��ǣ��������Ϲ��������������֣������Ծ�л������������������ܵĸ�������������һ���ţ��翪���ˣ�������۩�����ﵱ�һ��µ��������ڣ��������Ƕ�ͥ������ȸ��������Щ��lang�ģ���Ӽ��������찣����л�����һ�ء�
��������û�κΣ���Ӽ�ֻ����۩�ݳ���Ъ����ͬʱ�������ּۻ��ۡ���������ǿ���������ٴ���������۵�����ʲô�������������Ӽ�һ���е��������ǿ��Ӧץ���̿ͺ̿ͽ�����Ӽ����䡣
��������Ȼ�����ں������˳�¥��ߺ�����ĵ�ָ��������ץ���̿͡�ȥ�ˡ���ͷ��ֻ������СèС������ֻ��������ֽһ�㱡����
��������������һ�У�����֮�����ض�������۩�����������ܴ�Ķ����ϳ�ͷ��Ҳ����ס��Ӽ��ľ��棬�����ܷ���������������Ӽ������ɻ����������������գ�ܦ¥��ֻ�������Եذ��˼�������Щ��ηη�����ز�ʱ�����̽ͷ̽�ԣ���Ӽ����ŷ������ġ���������Ҳ�벻��������۩���Ѿ������˸���ij�͢��������������������ˡ�
�����������˰��죬ȴ�����к��������ģ����������½У����ֵ�һ����Ϳ�������ǣ��Ǹ������Ĵ̿;���û��һ˿����Ϣ��������
����������Ӽ��ȵü��ˣ�����ͷ��ȥ��������ߡ������ִ��˻���˵�����˿��ˣ�����ڶ��ٵȵȣ����мѱ�������ĥ���˴���죬�춼Ҫ���ˡ�
��������������һ�ޣ���Ӽ���ʿ�����۵ø�����һ��������Ҳ����ǰ������֪���Լҵ���ʳ����һ�ѻ����ˣ����������⼢���ĸо���������Ӽ�����һ������˵�Ѿ���פ�;�Ұ�ǵĸ�̫ξ��Ԯ�ˣ�������ڶ�ʹ���ֹۣ���Ҷ������Ž������ɵ�̬�ȡ�
����������ٴ������ʵ��̫���ˣ�ʿ����Ҳ���ĸ�̫ξ����������Щû����ʿ��������ʳ���ڣ�����������Ƥ�����ɵó�����
����������ʵ��Ӽ�Ҳ�����ƵĻ��ɣ����������������ܶ�ҡ���ģ�ֻ�ð���Щ����ѹ���ĵף�����װ�����Ұ�����������ο��ҡ���ϧ��װģ�����ı��±���������Ҫ��ö��ˣ����ּٴ�վ�������쵼�Ĵ�ᱨ�棬����ǧɽ��ˮ�����ų����еļ�ζ������
�����������Ǻܿ죬��Ӽ��ͷ��֣������ٰ��Լ��ӵı��ݽ��е����ˡ��������д�������������������
���������Ⲣ������Ӽ�һ�˵Ĵ������ܿ������µ�����Ҳ�о����ˣ�Ȼ����̽�������������˵�����Ӽ���ǰ�������ˣ����²����ˣ���һ������������������ɱ��������ŷ���������ɽ��������
�����������е���������¶����Ц�ݡ��������죬��û�д����㣬���Ȼ�Ѿȱ������ˣ�
������������������ɽ��ȷʵ������**��һ������������Ծ�֮�࣬���Ͼ���ʶ��۩�ǽ��оޱ䷢�������Ե������ϣ����Ƹ�ٴ�ĵ�һ���յ�����Ӽ���ͷ�ϡ�
������������ʮָ���������һָ���⿳���ٴ�ĵ�һ����Ҫ�ȶ�һ��������Ӽ���ָͷ������
�������������ָͷ����Ա��һ����˫ǹ����ƽ��һ����û������壬������������ǧ�������˶�����ɽ�����������컨�������������Ӽ����������������Ϯ��
���������������Ӽ����ݣ���������ס����Ӽ�������۩�ǵIJ�������Ӽ������۱��ڳdz�֮�⣬�����������Ķ�ҡ��ʿ��������������������ʱ����ʱ��ƽ����ĵ�ͱ�����ˡ�
�����������������Ӽ�����һ�����������Ŷ����ں�������˴��ҹ������������������б���������ɽ������֣�
����������ƽ�ų�˫ǹ��������һײֱ������ɽͷһ���߳�ͷ���ͷ�졣��ʱ������˫ǹ����ֻ���������������£�һ�������ݷ��ڣ��ٱ����ž��������ž�����ɱ��һ��Ѫ·��ֱ������Ӽ����������
����������Ӽ�������Ѫ������ɱ�������½����侪���ң����һ���������Լ����ױ�������ƽ����档�������У���Ա������ǹ����һ����������ʮ��ϣ�����δ��ʤ��������Ӽ��������ӡ�
��������������ʱ�����������û������塣�����뵽��������ս�پ��Ķ���������������һʯ��ֱȡ��Ӽ�Ҫ������Ӽ�ȫ���ע���붭ƽ��ֲ��£�ͻȻ����һ���磬��û��Ӧ�����������ϾͰ���һʯ�ӣ�ֻ��������������������������ұţ���������ǹ��������ͷ���Ҿ�����Ķ��ߡ�
����������ƽ���岻����������������ַ�һʯ��ֱ������Ӽ��ĺ��л��ľ��ϡ����R����һ����������Ӽ������������������Ǿþ�ս����ͽ�������ͨ��ɫ�ɱȣ���Ȼ���Կ�ͷ�����վ������̾�����ȵģ����Dz�����������
����������Ӽ������Ǻ���¤�Ҿ�ѡ�����ĺ�����Ҳ��ƥ�ѵõı������ԣ��ǵ�ɽ������ˮ����ʶ���⣬��ʱ�·�֪���������ѣ����ȷ�һ��ſ����������ƣ�����ƽ����Խ˦ԽԶ��
������������ʱ�����ﶼ����ɱ����������Ӽ��������ӣ��վ��������ƣ���������۩�dz�ǽת��С���Ȧ�ӣ�������ת�������š�
��������ȴ��һ�����죬һ��������·�ڿ���Ϊ��һԱ���᳤ֺǹ���������ޣ�ȴ�Dz�ξ������������������ǧ��Ϊ��ƽ����Ϻ�������ս����ȥ�����������ϱߵ�·�ϲ�������ðܾ������б��ڸ�ٴ��Ұ�����������������ˣ�Ҫ��ʰ���ǿɾ�û��ô�����ˡ�
����������Ӽ�һ�����˵�·�������ҽ��棬תͷ���ܣ�����ȴ���ϣ�ֻ������Ҫ��ɱ��Ҫ��©��֮��Ĺٱ���
����������ʱ����Ӽ���������·��������ţ��������ۣ�����̼��������ȹ�������һ�㣬ȴ����۩�dz�ͷ��һ�˸���ߺ�ȵ�������ڶ���Ҫ���ţ�����㿪�ǣ���ڶȿ���������
����������Ӽ���ϲ����ǿ̧�𱻴�������۩�����ų�ͷ����ȥ���ͼ��������������������Լ����ƴ�����ֽк���������Ӽ����Լ����к����˷�Ӧ������ϲ��ü�ң��еø��������ˡ�
��������һ���������������⣬ֱ��۩������ǰ������ʱ�ܱ����࣬������·��������ǰ��Ҳ�в��٣�������ͷ�Ͻк�Ҫ�����ţ��ܱ��Ǻ����ۣ���ӵ���ڳ�������Ѱ���������ĵ����������Ҳ�ж���ʮ���ˣ�ȴ����Ӽ������������ס�ˡ�
��������˭֪���ŵ��ŵĽ��䣬���ŵĿ�������ͷ��ͻȻһ�����죬�Ҽ������£�����ӵ����ǰ��Ķ���ʮ�Űܱ������䵹���������ںȵ�����Ҫ�������£�����ڶ����ߣ���һ��������ͷ���ɱ���ģ���
���������������ĵ�·�Ѿ���ͨ���裬��Ӽ���ϲ���ĵ�����������ȴ�Ǹ����ĵģ�������������Ҫ�����������۩���سǣ��һ�����ô����ɽ��������ǣ��ұ�Ӷ�����ˮ·��һ�����������������ĸ��ط��ϰ�����Ͷ����̫ξ���У���ʱ������������ѩǰ�ܣ���
�����������г���ϣ��������Ҳ���ڽ����˺��ʵĸ߶ȡ����ȵ�����ȫ��أ���Ӽ�һ��������ƥ���Ի��⣬����һ�ţ������Ѿ������˵��ţ�ֱ�����ڿ����ij��ų��˹�����
�������������Ӱ�������űߣ����ִ�У����ڶ�ʹ���˿��������Dz��������ˣ���
����������Ӽ�һ���������⣬������һ�������ֲ����Լҵ��ӵܱ���������Ҳ����û�й�ϵ���������ۡ�ֻ���Լ������������������ø�ٴ�Ĺ�ϵ�������ܰ�����ڶ�ʹ�����������ȥ������������ȥ��
�����������·Ż����٣��Ӱ뿪�����ij��ŷ���������ꡣ����һ�������ڶ�ʹ���˿�ҪС�ģ���
����������Ӽ�ֻ����ֻ�ǿ��������벻��Ϊ�⡣˭֪�Ự���������������ϵ����µĴ����ô�§ͷ�Ƕ���һ������Ӽ����¡�
�����������ڶ�������Ӽ������ڳ�ͷ�Ͽ��÷���������Ӽ�����һ���üף���Ҷ������Ҳ��֪���˶����ɽ����Ĺ�����ɣ��Լ����ӵ�һ������ȥ�������ܿ��˼ף�ֻ������Ҳ���в����������ˣ��վ��������ù���
�����������������������ӵ����س���ҵ���������DZ�����������������Ҳ��֪�õö�����������������������������һ�ó�͢�Ľڶ�ʹ�����ÿ�������Ӳ�����ǽڶ�ʹӲ��
��������һ�����£�����̩ɽѹ�ѣ���Ӽ������м�����������졣�������ˡ���һ���죬��һ��������Ӽ�ͷ�ϡ������ò�˵��Ӽ���ͷ���������ǹ�Ӳ�����ڴ��ֹ����쾭��������ʼ�ľ�Ʒ������һ����Ȼ����Ӽ���ͷ������÷��飬���Ƕ����ε�ͷ���������ε�ҧ��ס����֧�������ͷ�����벻�����������ݡ�
����������һ��������Ӽ������Ʋ�˥��б�϶��µĴ�ͷ��ɨ����Ӽ�ս�����Դ��ϣ������������һ����˻������һ�����������Ҳһ̲��һ��ˤ���˳������ͷ�ҳ���һ���ö��ϡ�
��������һ����˫�ף������кò����⡣ȴ������������������ᣬ������ܼ����������õ�һƥ��������ô��������������ˣ���
�����������ҵ�ʹ�죬���������⣬Ҳ�Ͳ��롰�����������ڼƽϣ�����ֻ�ǵ������ⲻ���ҵ��°�������ûʹ������ȫ����������Դ����ò���ʵ���в�ס�����������������Ӳһ�£�Ҳ�ܵ�����ģ�����ƥ�������������Ĺ����Dz����������𣿲��������Ҳ���㿴����ս���϶��������Ŀհ���������ȥ���ֵ�����ȥץ����ʮƥ��Т������磬�ø��һ����ʮһ�죬��������������
�����������������һ��������������Ӽ���ʬ��һ�������ɵ�һƲ�졣ԭ����Ӽ����Դ������ӣ�������һ���ҵ�ϡ�ã���İģ��������ŵõ������ǣ�����ͷ���ȴ��֪�Ӻθ���
�����������㡱��һ����������Թ��������㿴�㣬�Ҿ��ң��㲻�����������Ż������ع���һ�������ȴ������������ͷ�����ø��˸������������ȥ����ʱ�ǵ��¸����翹�Ĺٱ��DZ�֤����Ͷ����ʡ�����ǵ��˶����ֽš���
����������Ц���������ȴ�Ǵ���һ������Ϳһʱ����Ҫ��ҡ�ٱ�ս�ģ�������ͷҲ��������
��������˵��������Ӽ�ʬ�壬���˳�ͷ��Ѱ�����ӵ����������ڰ����������������Ӽ���ʬ�ڴˣ���
�������������̶����ڹٱ���æ�л�ͷ�����һ�������ɲ�����ͼ������������ݵ���Ӽ������������ţ�������һ�����ӵ��ƿڴ�һ�����ڳ�ͷ�ϣ�Ѫ�����ܵ��粻�ɸ���ģ����
�������������Щ�ٱ�����Ӽ��Զ�����ᣬ�Լ���ѵ������������������������Щʿ�����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