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逃台前发出的最后通缉令 薛家柱-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白玉婉紧握着话筒,一声也不吭,只是泪如雨下。十几年过去了,黄仲洲对她来说已成为一个遥远的回忆,一个淡化了的影子。她的身边已有一个活生生的伴侣,一个长期深爱着她,一直用关切的目光凝注她的人。而现在命运又如此捉弄人,又把她从他身边拉开,重新推回到快要遗忘的往事中去。“玉婉,你听见了吗?玉婉,你为什么不说话?”话筒里传来了石亦峰遥远的呼喊,“总机!总机,为什么没有声音?”
“亦峰,我听见了。”白玉婉只好用暗哑的声音回答,“一切等回来再说吧。”
她只能这么说。不是她不爱黄仲洲,而是他出现得太迟了。
第34章
在兰州公安招待所的食堂里,石亦峰叫了几个菜和一瓶汾酒,正与黄仲洲把杯话旧,突然几名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大步向黄仲洲走了过来。
黄仲洲一见他们,满脸露出惊惶神色,本能地站了起来,往角落里躲。
“不许动!黄仲洲,你为什么连夜逃跑?”
“我,我”黄仲洲见到公安人员就瑟瑟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又恢复了“疯子”的傻相,只会低头垂手,哭丧着脸苦笑。“嚓!”锃亮的手铐套上了他干瘦的手。
“走!跟我们回去。”
“同志,”石亦峰连忙上前,和颜悦色地说,“请把他的手铐去掉,他是我的客人。”
石亦峰并没穿警服,一个年轻的战士很不客气的喝道:“你是干什么的?
同这个犯人有什么关系?”
石亦峰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掏证件,一边用不失威严的语气沉稳地说:“我也是公安部门的,这次专程来兰州执行任务,会同甘肃省公安厅,把他带回家去。”
武装干警看了证件,知道面前同行不是一般干部,但又惊异:“这个逃犯,怎么会同这个公安干部一起吃饭?”
“他是坏分子,是从劳改场逃出来的。”
“他偷窃国家文物,私藏古钱币。”
一听到偷国家文物,黄仲洲立刻叫起来:“不,我没偷文物,那些古钱币是我从农民手中买的,我是保存国家文物。”
“对,”石亦峰笑着说,“这位黄先生是位爱国将领,他为保护国家文物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哦——”这些武装警察更加诧异了。
“你们知道吗?我们已找他有10多年了。我这次来,就帮他办理离场手续,为他恢复名誉。”
“原来如此。”领头的干警连忙解开黄仲洲的手铐,很友好地说:“黄同志,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黄仲洲百感交集地一句话也说不出。
“早说有什么用。”石亦峰苦笑一声,“这一切他能说清楚吗?”
是啊,人生有很多事,不是一说就清楚的,不到时候你说也无用,到了时候不说也一目了然。
自从离开了乞丐帮,黄仲洲没再厚着脸皮一个人上门乞付,他失去了带路的小乞哥们。他独自在甘肃的河西走廊流浪,饥一顿、饱一顿,风餐露宿。
几年生活的磨难,黄仲洲渐渐失去了身上那种书生气,变得又黑又瘦,一副老实巴交的农民样子。
有一天,黄仲洲与一帮人修水库挖土时,挖到几个黑黝黝的瓦罐。一个青年农民用锄头砸碎一个,从里面掉出不少铜钱。几个人围上去,争着往袋里塞、怀里揣。
“这些锈斑斑的小钱,有啥稀奇?”
“当废铜卖也好嘛。”
接着又欲砸第二、第三个罐子。
“别砸了,别砸了!”黄仲洲大喊起来,他定睛一看,原来这是秦代的古钱币,文物价值很高。他不由得一阵惊喜,伸出双手去拦阻其他人。
但这些愚昧的人根本不听他的劝告,噼哩叭啦地把罐子全砸了。乘他们砸抢的时候,黄仲洲像守门员扑球那样,用身子死死压住一只罐子,才使它免遭粉身碎骨的厄运。大家见他这样拼命,也不来和他争夺。
几个民工每人捞到一些古钱币,拿在手中数着,至于那些罐片,早已弃之乱石之中。
只有黄仲洲跪在乱石堆里,挖呀找啊,将那些碎片搜集起来,连牙齿那么小的碎片也不放过。他把身上的破衣服脱下来,光着上身,用衣服把碎片包起来,同他用生命保住的那个完整罐放在一起。他一边挖地,一边不时地瞥着他的宝贝。这天,他的工分只有2 分,但他很满足,其他民工说他傻瓜一个。
收工以后,那几个民工拿着古钱币到旧货店。掌秤的小姑娘似乎不收这破铜烂铁,用细嫩的纤手操起几个看了看,皱着眉毛,鼻孔翕动,朝他们翻了翻白眼,意思不言自明:这破东西,不收。几个民工好说贱卖,总算卖了半瓶酒钱。
黄仲洲知道后,立即赶到那家废品店,提着这堆古币说:“我我想要这个。”
“好吧!”小姑娘很干脆,手一摊,“拿钱来。”
“多少钱?”黄仲洲怯怯地说。
“刚才收的两元,总不能让我白收,3 元。”
一转手就涨了1 元。1 元钱对常人并不难,可对黄仲洲却是难倒了英雄汉。他听说是两元,就拿出所有带来的钱才1元5 角,还有1元5 上哪儿弄?
黄仲洲无计可施,便将身上衣服脱下,当破烂卖。小姑娘捂着鼻子:“这破烂,扎拖把也嫌不牢。”
这样才卖了8 角,还有7 角呢?只好把短裤也脱了吧。小姑娘动情了:
“算了,算了,把这东西拿去吧,等有了钱再还我。”
黄仲洲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半个月后,他从发下的生活费中拿出7角送给小姑娘。小姑娘也感动了:“想不到你这叫花子模样,还挺讲信用。上次我只是随便说说,谁稀罕这7毛钱,拿回去吧。”
修好水库,黄仲洲带着罐子和古币到兰州,准备送给博物馆。陶罐只要粘合一下,就能修复好。
他几次在博物馆门口徘徊,踯躅了半天,还是不敢进门。他怕引火烧身,担心人家追问他的来历和身份,而使南京的事东窗事发,结果收不了场。他这一身打扮谁会相信他?中午饿得肚皮贴着脊梁骨,只好进一家饮食店。见一个风度不俗的青年正在吃饭,剩下不少菜和大半盒饭。黄仲洲顾不得脸面,跪过去,结结巴巴说:“同志,你吃不完,能留给我吗?”
“好吧。”那人一见他,厌恶地站起来准备走,生怕染上肮脏。
黄仲洲急不可待地趴在桌子上狼吞虎咽吃起来。这青年一眼瞥见地上的破柳条筐,不由眼一亮,“啊——,老头,你这玩意哪弄的?”
黄仲洲心里明白,只顾吃,不作答。
“老头,我出100元,你把这玩意卖给我吧。”
这一说,引起四周用餐顾客的注意,纷纷围了过来。“什么东西值100元?”
黄仲洲早已风卷残云般扫荡完桌上的饭菜,提起篮子,拔腿想走,可哪走得了!早被人围住了。
“老头,若嫌少,我再加50!”
“不卖,多少钱也不卖。”黄仲洲被逼急了,冲口而出。周围人群中,顿时像油锅里放了把盐,炸开了。
“这老头,一只烂罐子,一堆破钱,人家给100元还不卖,真该讨饭。”
“嗨,一个穷叫花,见钱不要,真不知好歹。”
不料,这一来,惊动了对面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看筐里东西,硬说是从博物馆里偷的,并报了案。黄仲洲第二次被带进公安局。在审讯中,尽管黄仲洲句句真言,可一个叫花子话,谁相信呢?因此判定他为盗窃犯,偷国家文物。
这下黄仲洲有口难辩,心想:只要文物归国家,自己坐牢,总有出头之日。他默认了。几年来,他一直在祁连山下采石场改造。列车越过黄河,跨过长江,于凌晨5 时到达南京。
古城沐浴在黎明的晨光之中,黄仲洲在石亦峰陪同下,走出仍是解放前建造的下关老车站,乘上水文秀专程迎接的汽车。黄仲洲看到那宏伟的挹江门,那宽阔的林荫路,那巍巍耸立的紫金山,心中真如扬子江的激浪在奔涌。我回来了,这儿的每条道、每幢建筑、每株草木,都是那么熟悉、亲切,连风都带有一种亲切的甜香。在大西北流浪10年,满眼是无边的黄土、风沙,今天看到这葱茏的绿色,真想大哭一场。即便在草上打个滚,也是很痛快的事。
住进了原是A、B 大楼的军区招待所。石亦峰让黄仲洲洗个澡,又吃点饭,回到房间。石亦峰兴致勃勃地说:“走,我陪你去见一个人。”
“谁?”
“玉婉。”
“不不不,”黄仲洲顿时惊慌,连连摆手,“再也不必了,我永远对不起她。我欠她的太多了!”
“我已把你的情况告诉她了,她一直没结婚,在等着与你重逢。”
黄仲洲心中有说不出的复杂感情,既觉意外,又感欣喜。这么多年,他不知玉婉是死是活,凭他的处境,也无法与她联系,只能深埋在心底。这次回南京,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心里也想见她,没想到石亦峰已安排好了。
“亦峰——”他深深地握住了石亦峰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亦峰,一切我都明白了,你都不必再说了。”
“仲洲,只要你能谅解我们过去的误会,不再恨我就行了。”
“不不,”黄仲洲咽下一口唾液,“我怎么能恨你!只是不知怎样报答你才好。亦峰,没有你,我哪有今天?玉婉也不会有像现在这样的日子?我不想伤害她了,我只想看看那批文物,这样,我死也安心了。”
“仲洲,你别灰心丧气。”石亦峰竭力安慰他,“尽管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失去的东西太多太多,但在新中国的阳光下,你有权利得到你生活中应该得到的东西,重新获得幸福。”
“不不,一切太迟了!我看了文物就离开南京,如果玉婉问起我,你就说我暴病身亡。”
说到这儿,黄仲洲已满眼是泪。他不想再以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来搅乱白玉婉平静的心境。失去的岁月不可能再回来了。
“好吧!你再考虑考虑,我们慢慢再商量。”石亦峰觉得此事不可操之过急,“现在,你先好好休息一下,我到局里汇报工作去。”
黄仲洲感激涕零地送石亦峰走出房门,并一再说:“我钦佩共产党,钦佩亦峰兄的为人。”
“冬冬冬。”
“请进。”
门虚掩着,石亦峰推门进来,白玉婉正在屋中拖地板。
“玉婉,这下是大喜临门了。”
谁知,石亦峰刚一开头,白玉婉脸色大变,拖帚掉在铅桶里,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石亦峰去甘肃,她开头并未抱太大希望,10年不见音讯,现在凭一封信去登报找人,真是大海捞针。几天过去了,石亦峰没有一点消息,白玉婉以为大约不会成功了,这样石亦峰就会很快回来。他们从此可以一了百了,心里再也不会有憾意。
谁知,甘肃的长途电话传来了石亦峰激动的声音,让她大吃一惊,心里掀起强烈波澜,就像深古潭底搅起了泥水,再也不能平静。
她想起在这10年里,自己经历的大起大落。同时爱着两个男人。而这两个男人又同样爱着她,他们都有非凡的才能,理应成为事业的成功者。由于时代的悲剧,使他们历尽劫难,在生活激流中浮沉。
白玉婉只要有其中一个人便知足了,可命运捉弄她,两个人老是一前一后地出现在她身边。黄仲洲消失了10年,白玉婉整整等了10年。本应结束这等待,突然,黄仲洲又出现了。
当水文秀前来通知她,他们快到南京了,她激动得夜不能眠,不知下一步如何安排。实在无法想象,也不敢想。
清晨5 点钟,正是火车到的时刻。白玉婉便开始忙碌起来,今天是非同一般的日子,但她不知如何迎接它。她不敢相信自己有力量对付眼前的现实。
现在,石亦峰一个人进房来,白玉婉一下失去理智,搞得惊惶失措。
石亦峰似乎没事地拿起拖帚,帮她拖起地来:“他现在在招待所里。我先通风报信,等会儿他就来看你。”
“不!”白玉婉大声喊了起来,嗓音也变了,“他还来干什么?这么多年音无音讯,他心中还有我吗?”
“这能怪他吗?”石亦峰用双手扶定她颤抖的肩膀,像兄长那样关切地望着她,“他吃的苦少吗?心灵有深深的伤痕。作为妻子、作为老同学,不能再让他心的创口滴血了。”
这轻轻的几句话,随同石亦峰热切的目光,溶化了白玉婉心灵的冰壳。红艳艳的太阳挂在空中,巷口汽车喇叭响了。白玉婉竭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走到门口。
汽车停在门外,石亦峰和黄仲洲下了车,向小院缓步走来。白玉婉呆呆地望着他们,有点不知所措。
黄仲洲已换上了新的哔叽中山装,恢复了原来的风度。但脸上的皱纹和两鬓白发,掩不住岁月沧桑。一见白玉婉出现在门口,两人同时伸出双手:
“玉婉”
白玉婉迎上去,两只手各握住一个自己心爱的人。
第35章
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举行了重大文物案的开庭审判。主犯谢梦娇已畏罪自杀,从犯魏照暄、沈竹琴到庭接受审判。
当石亦峰、黄仲洲、白玉婉等人步入法庭前去列席旁听时,内心有说不出的感慨。这座灰色的建筑物,也就是当年国民党时代的法院,高高的穹顶,阴暗的光线,连白天都要打亮电灯。人一走进,四壁就发出嗡嗡的回声,给人一种庄严、肃穆感。
石亦峰等人坐在旁听席的木质长椅上。这些长椅都是硬木做的,显得非常粗笨、牢固。证人席上坐着水文秀,她特意换上了制服。正中的被告席栅栏内,站立着魏照暄和沈竹琴。这个一向自鸣不凡的魏照暄,今天耷拉着脑袋显得萎靡不振,头发又长又乱,像一蓬乱草,腮巴上也是黑碴碴的胡子。
倒是沈竹琴显得毫不在乎,漠无表情地东瞧西看,还用手肘捅捅丈夫,叫他振作一些,别让别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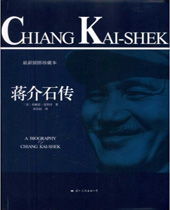
![两岸惊涛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者:[中]尹家民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5/2516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