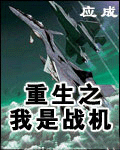我是个算命先生1-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今年年初母亲染了风寒,后来病情加重,发展成肺痨,每日咳血。看着母亲这样,我心如刀绞,只要能赚到钱,给母亲治病,让她吃上点好东西,受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说罢,又流泪了。
徐怀近紧紧把花月容搂在怀里,说:“不要怕,不要怕。你我萍水相逢,也是缘分。我会帮你的。”
花月容站起来,又为徐怀近满了一杯酒,自己也满了一杯,举起酒杯,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小女并非生性浪荡之人,即便是进了这青楼,也不是随意之人,所以才写了这副上联在门上,至少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小女才肯接纳,先前几个人对得乌七八糟,直到处长您来了,小女才倍感欣慰,徐处长文武双全,小女敬佩,我来敬您一杯。”
徐怀近开心地笑了,把花月容揽在怀里,痛痛快快地把酒喝了。随后,花月容又满了几杯,两人都一饮而尽。
几杯酒下肚,两人静静地偎依着。月色停留在柳梢,微风从窗子里吹进,院中的玉兰花香迎面扑来,抛去所有的阴谋和罪恶,此情此景就像一幅画,定格在温馨的爱情里。
三更时分,徐怀近解下花月容的外衫,花月容羞涩地捂着红肚兜,说:“徐处长,可否宽限小女两天?”
徐怀近不解,问:“为什么?”
花月容一脸惆怅地说:“我自幼体弱多病,母亲曾叫一位算命先生给我批过八字,说必须过了20岁生日,方可行房事,否则,必活不过22岁,还有两天就是我的生日了,因此,请处长……”
徐怀近一愣:“哦,这样啊,这么说,月儿姑娘还是处子之身?”
花月容脸一红,轻轻点了点头。
徐怀近温柔一笑,“呵呵,古人常说动若脱兔,静如处子,难怪月儿姑娘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沉稳与含蓄,呵呵,不急,不急。”
花月容赶忙行了个万福,说:“谢谢处长,这真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小女命苦,乃浮萍归海之人,却没曾想能在这烟花之地遇到处长这样有情有义的人!”
徐怀近高兴地笑了,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你刚才说,有个算命先生……”
花月容说:“嗯,这个人很厉害,曾是家父的旧交,他曾断家父中年有性命之忧,怎奈家父对此并不在意,家父是个倔脾气,常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出事那年,那个算命先生还专程到我家告知解灾方法,但家父忙于生意,并未接纳建议,结果当年冬天,家父就被仇人所害,从此家境败落,他还算出我的两个哥哥有灾……这一桩桩的事,后来都应验了,所以小女才很在意自己的圆房时间,小女并非惜命之人,只因母亲有病在身,我放不下她,无论如何我都要将母亲养老送终……可最近母亲病情越发严重,我不想顾及这些事情了,心想死就死吧,死前能让母亲吃上口东西,死了也值……”
没等花月容说完,徐怀近就打断她的话:“不要说傻话,一切都有解决的办法……”沉思了一下,又说,“你说的这个算命先生叫什么,何方人士?”
花月容说:“这个算命先生,人称铁版先生,据说是什么铁卜子道人的嫡系传人……”
徐怀近抢话说:“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个铁版先生吗?”
花月容笑着说:“小女非官非仕,哪懂得看报纸,不知处长说的是哪位。”
徐怀近说:“肯定是了,肯定是了,你还能找到他吗?”
花月容说:“他云游四海,行踪不定,这个不好说,但每年家父忌日,他都会赶来凭吊。”
徐怀近说:“令尊什么时候忌日?”
花月容说:“本月初七。”
徐怀近点点头,像是自言自语:“天助我也。”
花月容问:“处长说什么?”
徐怀近说:“没什么,没什么,下次,带我去看看你母亲吧。”
花月容说:“不劳处长了……”
徐怀近说:“要的,要的,一定要看望一下。”突然又问:“你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花月容答道:“大锥子胡同,28号,月初刚搬来的。”
徐怀近说:“好,下次你带我去。”
花月容说:“谢谢处长关心。我今夜不能陪处长入寐,就给处长唱一首昆曲吧。”说着又给徐怀近斟了一杯酒。
徐怀近笑着说:“好啊。”
花月容手抚三弦,唱了一段《点绛唇》,平仄回转,余音绕梁,听得徐怀近不停地抚掌助兴,唱到动情处,徐怀近竟身不由己地靠近花月容,将其搂在怀里。
此时有个小特务敲门进来,看来是催促徐怀近时间到了。徐怀近走到那个小特务跟前,低语了几句,那个小特务打了敬礼,退下了。
花月容说:“处长若有事,只管去忙,小女遇到了处长……心就……有所属了,处长只管去忙公事,月儿就在这里等,处长一日不来,月儿就等一日,处长一年不来,月儿就等一年,处长今生不来,月儿就等到下辈子。”
徐怀近愣愣地看着花月容,花月容痴痴地望着他,徐怀近轻轻地将花月容搂在怀里,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鸡叫三遍,东方泛红,很快日头跳了出来,徐怀近整理了一下衣装,对花月容说:“月儿姑娘,徐某两日后再来见姑娘。”
女阿宝爱上军统特务
徐怀近走后,花月容在屋里梳理了一下思绪,然后将楼下的一个姑娘喊来,密语了几句,然后自己换了身衣服,奔向大锥子胡同。约摸半个时辰,来到28号院门前,轻声叩门,喊:“妈?”
没多久,一个老妇人走了出来,额头上缠着白布,一副身染重病的样子,高兴地说:“女儿回来了?”然后开始剧烈地咳嗽。
没等花月容开口,老妇人就对她使了个眼色,眼角扫了扫墙外,大声说:“女儿啊,刚才有两个好心人来我们家,说是你的好友,问了问我的病情,还给我留了些钱,真是好心人啊。”
花月容心里咯噔一下,一边搀扶着老妇人进屋,一边说:“妈,什么好友啊?叫什么名字啊?”
老妇人说:“我问了,他们没留姓名,就说是你的朋友,说以后还会来看望我。”
花月容说:“噢,妈,下次他们来,您记得让他们留下名字。我也好知道是谁啊。”
老妇人叹口气,说:“对啊,对啊,我们娘儿俩算是遇到贵人了,你父亲死得早,两个哥哥也走了……”
花月容说:“妈,你提这些干什么,有女儿在,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两人走进屋里,把屋门关上,老妇人马上扯下头上的白布,花月容冲着老妇人诡秘地一笑,那老妇人将手指放在嘴边,“嘘——”示意花月容不要太放肆。
两人又在屋里娘啊闺女地对答了几句,花月容开始从院子里弄来干柴烧火做饭,炊烟顺着烟筒冒出,袅袅直上,一直散到高空。
其实,这期间,后墙外一直有徐怀近的特务监视偷听。昨晚,在花月容向徐怀近诉说身世时,徐怀近就准备摸一下花月容的底。快天亮时,那个小特务上楼来,徐怀近对他低语那几句,就是让小特务马上赶到大锥子胡同28号,看看究竟是否如花月容所言。
祖爷和张恩瑞这两个老手在布局时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提前安排一个年龄大的女阿宝,化了装,病怏怏地卧床在28号院里,随时恭候特务们的到来。
果然天刚蒙蒙亮,那老阿宝就听到有敲门声,她披上衣服,佯装病态,打开院门,一看是两个陌生人,心下早有准备了,一边把他们让进屋里,一边顺着对方的询问,唉声叹气地诉说自己的家事,与花月容说的一模一样,其间还不停地咳嗽,用手帕捂着嘴,似乎要把肺咳出来。咳了一阵,停下来,打开手帕,先前夹在手帕中的血泡破了,昏暗的屋子里,特务们以为她真吐血了。
那几个特务与老妇人交流了一会儿,没发现什么破绽,就依照徐怀近的吩咐留了些钱,然后溜到后墙外,开始蹲点。这些特务也真是狡诈,他们要看看花月容回来后,两人是个什么情况,结果花月容与老妇人将母女情结演绎得天衣无缝,两个特务也放心地回去汇报了。
花月容刚进门时之所以惊讶,是没想到徐怀近的特务会来得这么快,她甚至没有察觉徐怀近是什么时候告知特务们的。对于一个阿宝来讲,这是致命的失误,阿宝们是不能错过对手任何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的,花月容心下一阵迷茫,自言自语:“我这是怎么了?”
老妇人问:“什么怎么了?”
花月容一愣,“哦,没什么。”
夜里,花月容又回到凤鸣楼。这边的情况,花月容已让小脚告知了张恩瑞和祖爷,她要依照计划进行下一步的演练,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出千,怎么收网,所有环节一遍遍地在脑海中过着。再也没有嫖客敢上楼打她的主意了,因为徐怀近走前甩给老鸨一大笔钱,告诉她:“花姑娘,我包了。”
夜深了,花月容也累了,喝了几口茶,解下外衣躺在床上,想睡觉,又睡不着,只好静静地发呆。徐怀近的样子不停地在她眼前翻腾。徐怀近的确英俊伟岸,黄埔军校的高材生,笔直的腰板,彬彬有礼的举止,想着想着,花月容竟不由自主地笑了,突然又止住了,愁容代替了笑容。她清楚,她只是个阿宝,是个地地道道的骗子,徐怀近是她的狍子,是她的对手,这一切都是局,都是戏,终究要曲终人散。
第二天傍晚,花月容吃过晚饭,刚打扮好在闺房坐下,就听老鸨一声高叫:“哎——哟,长官来了,花姑娘在楼上等您呢!快进,快进!”
随后是一串军靴踏上楼梯的噔噔声,花月容忙打开屋门,徐怀近大踏步走过来,两情相见,如隔三秋,徐怀近微微一笑:“月儿姑娘。”
花月容含情脉脉地说:“处长。”
花月容正要把徐怀近让进屋里,徐怀近一摆手,“不急,月儿姑娘。”说着,一转身,摘下手套,伸手对身后的特务说:“拿来。”
一个特务将一束美丽的鲜花递到徐怀近手里,徐怀近双手将鲜花举到花月容的面前,眼睛望着花月容,深情地说:“月儿姑娘生日快乐,祝姑娘花容永驻,永远漂亮。”
花月容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辛亥革命后,尽管西学东渐,国民日益罗曼蒂克,但这种西式的浪漫之举,除了志摩、悲鸿之类的大才子玩玩,军统特务弄这个还真少见!花月容自幼贫苦,早年深陷梨园,从戏词中学的都是张生、莺莺之类的棋盘下隐涩之爱,哪经历过这轰轰烈烈的场面啊。
花月容眼睛竟然湿润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怯怯地接过那束鲜花,满脸绯红,低声说:“处长请进!”
徐怀近对身后的特务和老鸨说:“都退下吧,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打扰!”
进屋后,花月容一下投进徐怀近的怀抱,两人紧紧搂在一起。徐怀近又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后是一只雕有龙凤花纹的玉镯,他对花月容说:“这是我报考黄埔军校前,临行时母亲拿给我的,她告诉我要我送给她将来的儿媳,现在我已经找到了。”
花月容深情地望着徐怀近,“处长。”
徐怀近将花月容轻轻搂在怀里,说:“我已经派人去看望过你母亲了,以后,我会同你一起照顾她老人家。你再也不用为生活担忧了。”
花月容伏在徐怀近的肩头流下眼泪,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自己真的是一名妓女。
依照大师爸张恩瑞的安排,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花月容无需献身,她本可以依照计划,以父亲三年孝期未到为借口,躲过今晚的一劫,但她变卦了,她主动宽衣解带……
后来,花月容死后,张恩瑞派人清理她的遗物时,在她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是花月容亲手写的小楷书信,也算是花月容内心最深处的独白吧。她写道:
将军卿卿如晤:
妾身卑贱,生不逢时,意欲昏昏度日,了此一生,怎料上天怜妾,得与将军。将军雄姿英发,待妾恩重如山,妾得将军,云胡不喜?妾漂泊廿载,受尽苦累,无父无母,无牵无挂,自遇将军,方谙女儿之味!
妾乃九流骗子,深陷三途恶道,自遇将军始,遍施欺诈之伎,将军在局中,妾身在梦中,将军待妾之情日益一分,妾身心痛亦增一分,将军进,妾心碎。而今,将军还在局中,妾梦已醒,妾何尝不想久在梦中!
妾不怨天,不怨命,妾得将军之爱,此生足矣!从来鸳鸯多悲散,自古多情伤离别,妾将不久于人世矣!将军阳间为人,妾身阴间做鬼,自此阴阳相隔,各依天命。人如清风肉似泥,人死无情花落去,妾生前身不由己,死后魂安何处?妾惟恋将军,九死而不能忘!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望君伏惟珍摄,妾不尽依迟。
妾月容
丙辰日丑时
她称这个特务为将军,言辞中莫不是真情卓爱。这真是纱帐暖,红烛摇,一夜云雨百恨消;军统情,阿宝爱,真真假假已无碍。
她自己也知道,这终究是一封永远无法寄出的信,其实,她早就死了,死在自己的爱情里。
算命先生的美人局
依照计划,花月容要在自己“父亲祭日”,向徐怀近引荐祖爷。几天交欢,徐怀近和花月容已经无话不谈。花月容用小脚们提前准备的月经之布,也巧妙地成全了自己处女之身的谎言。
引荐之前,花月容一再叮嘱徐怀近:“千万不要说你是军官,因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正常情况下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军统高官的,如果让那位先生知道了我来青楼做妓,传到母亲耳朵里,母亲肯定会心痛!我一直对母亲说,我在一家饭馆做帮工,为了洗刷那些盘盘碗碗,我整夜都要加班。”
徐怀近点了点头,说:“我就说自己是个商人,是你父亲生前的一个朋友。”
这其实是个声东击西的套儿,只有徐怀近隐藏自己的身份,祖爷再将他的身份揭露出来,才显得祖爷道行高深呢!表面上看,花月容出此策,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其实是为了减少徐怀近的提防力。
徐怀近以茶商身份,在一所酒楼长袍大褂地和祖爷见面了。
刚落座,就听他谦卑地说:“久慕先生大名,今日得见,果真道骨仙风,名不虚传。”
祖爷呵呵一笑:“阁下过奖了,一介草民苟活乱世,何谈大名。”
徐怀近笑着说:“先生过谦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