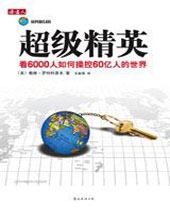蒲公英-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起气氛由热变凉,于是有意停顿了一下,以便寻找更适当的措辞。“接着说。”冯水新的目光中带着无限的期盼与鼓励。“我不想让他俩再干咱们这一行了。”他低着头说,声音细到连他自己都听不清楚。冯水新抽了一口烟,没有马上说话,他看了鲍福一眼,脸上掠过一丝笑意,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鲍福本以为他会说点什么,至少会问一句“为什么?”吧,可是他什么也没说。“也许他对我的反复无常太失望了。”鲍福想。可是从冯水新流露出的笑意来看,他丝毫都没有不高兴的情态,那挂在脸上的笑容是自然的,也是真实的,绝对没有半点儿伪装,而且那种笑容只有在他听到一个极好的消息时才会出现的。“大哥,我在想……”鲍福还想再做些解释。“兄弟。”冯水新制止了他后面的话,并用一种十分信任的口吻对他说:“我很理解你,就按你的意思办。”鲍福也很清楚,关于儿女情长的话题,在这样的气氛下不宜多说,于是,迅速把话题转到今天的事儿上来:“大哥,今儿我又跟那姓汪的干了一仗……他的话太噎人了。黄组长虽然也在场,但没有多说什么。看样子,以后的秧子还少不了。明儿他们肯定过来向你解释。”“鲍福兄弟,你也别替我操这份儿心了,你大哥不比前些年了,你也别怪大哥摆架子……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架子可摆……这次我狠了心了,只要有他姓汪的在,我决不会踏入俱乐部半步。”“大哥,只要咱老哥儿俩拧在一起,不信他姓汪的能翻了天?”“鲍福兄弟,不管你怎么说,我都是那句话,我决不会跟他姓汪的混在一起。别说现在他当了什么主任,要领导我,就是我俩换换位置,我也决不答应。我有言在先:‘宁可为君子牵马坠蹬,决不给小人当祖宗。’”鲍福实在扭不过,只好作罢。出了冯水新的家门,鲍福觉得脑子里更乱。这冯水新也太不识抬举了!兄弟我今儿弄得口干舌燥,还不都是为了你?可你老兄倒好……坐山观虎斗。他一气之下真想回过头去把冯水新骂个狗血喷头,又一想,算了,还是忍了罢。迎面传来一阵哼小曲儿的声音,不用问这准是二绕子晚饭后散心的情景。这老头儿活得倒潇洒,品行也不错,就是嘴贫了点儿,不过也挺有意思。心情不好的时候跟他聊聊天,还真能消愁解闷。不过今儿鲍福没心情跟他贫嘴,只能简单地打个招呼:“二哥,吃过了?”“哎呀,是鲍福兄弟呀!”二绕子显得很吃惊。“咋啦。二哥?”“借一步说话。”二绕子把他拉到一个僻静处。鲍福不知道他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便急着问:“二哥,有啥事儿?”二绕子神神秘秘地问:“兄弟,你吃晚饭了没?”“还没呢。到底有啥事儿?”“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就这事儿?”“嗯,就这事儿!”嘿!这老家伙!鲍福被他弄得哭笑不得。摔掉二绕子,鲍福继续赶路,当经过大队部门口时,发现有两个人影从里面晃晃悠悠地出来。鲍福一眼便断定一个是文圭汝,一个是冯保才。这两个老东西这么晚才回家,一定又在想什么歪主意吧?于是警惕起来。只见那两个黑影一路走着,似乎还在小声嘀咕着什么。鲍福停下脚步,想听个明白。谁知他们也像发现什么似的忽然警觉起来。哼,这两个坏东西要不是心里有鬼,怎么会这么提心吊胆?鲍福气不过,仍站着不动,却故意放开嗓子咳嗽了一声。两个黑影听到声音,立即分开,各回各的家去了。想到他们刚才鬼鬼祟祟的样子,鲍福又将思绪回到了汪清贤的身上。这小子除了文圭汝他还能依靠谁?我看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还能兴盛几天!等我上台以后,看怎么收拾你们!鲍福虽然这样想着,但心里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他妈的,真是欺人太甚!不行,得找昭珙说说去,不信安排俱乐部主任的事儿没经过他鲍昭珙点头?昭珙的大门始终都是虚掩着的。鲍福招呼没打就走了进去,刚踏过门槛,便想到了那张不冷不热的脸,于是又犹豫了。这种犹豫决不是害怕,他鲍福从来就没有害怕过谁,包括昭珙。他低着头,三步一指地挪,刚转过影壁,便停止了脚步。里面早已听到了动静,冲着外面喊:“谁啊?”是昭珙的声音。鲍福也不回答,转身便走。里面也不再追问。回到家里,桂晴和学智还在等着他一起吃饭。两个小的吃过饭又到老奶奶房里听故事去了。文氏吃过饭不知找哪位老太太说话去了。鲍福一屁股瘫痪在凳子上,浑身像散了架子似的。他把头埋在膝上许久,才慢慢地抬起来。他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学智:“我说儿子呀,我跟他狗日的斗了十几年,还是斗不过他,倒不如你小子三言两语干得痛快。我不如你呀,不如你!”“瞧你,这都给孩子灌输些什么呀?孩子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吗?”桂晴责怪道。“不说这些了。”鲍福拢一把松软的分发,精神一振,“小圣呀,我还是那句话,别管上面兴不兴考试,咱都得把功课学好它。只有你把功课学好了,我才有资格跟他们较真儿。另外你也别光热语文,不热其他的,常言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还是数理化重要啊。”“这话你都说了一百遍了,连我的耳朵都磨出茧子了,呶,先把嘴堵上。”桂晴递给他一个黄面馒头。饭罢,学智开始做功课,鲍福和桂晴饮羊。他们还没有走到羊圈里,就听到羊们饿得一个个乱叫。鲍福问:“下午怕是没喂它们吧?要不怎么会饿成这样?”“下午我哪有时间出门?学湘在咱家整整哭了一下午,我得劝着点儿;小圣说今天开校会,也回来得晚了些。”鲍福皱眉道:“正经事儿都让这帮窝囊废给耽误了。不行,得想法给它们弄点儿吃的去。”“到哪儿弄去?”“还能到哪儿?小树林呗。”“那可不行,刚开过会,要是被人发现了,你就不怕坐宣传车?”“顾不上那么多了,赶快跟我去。”“那咱可得小心点儿!”“怕什么?他们不会碰得这么巧。”饮完了羊,他们俩一个肩背篓筐,一个手拿钩竿,趁黑夜无人,悄悄走出家门。小树林拐弯儿即到,他们并不敢在此下手,得往里走走。鲍福天生有一种虎胆,而且又经历过无数次曲折,莫说弄几片树叶,就是搞他几棵大树,也毫不含糊。当然,那种偷鸡摸狗的勾当他鲍福从来都不干,不仅他不干,而且孩子们也绝对不准干。至于这点儿小事儿麻,他总觉得无伤大雅,也算不得偷窃。因为他爱羊如命,一旦草料吃紧,只好出此下策。眨眼工夫,他们已经折了一筐杨柳枝叶。桂晴催他赶快回家,他坚持说:“慌什么?既然出来了,就得多弄点儿,索性把明天的草料全准备好得了。”桂晴再要催时,忽听“咔嚓”一声,半棵柳树齐刷刷地给整下来了。桂晴急得直跺脚。这时从路上走来一个人,大声问:“谁?”还没等他们有所反应,一束强烈的手电光把他们的脸照亮。两人几乎吓懵了。来人忽然将手电熄灭,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转身便走。鲍福最先反应过来,他对着吓得筛糠似的桂晴耳语道:“是霍组长。”桂晴不听则已,一听吓得连腿都迈不动了。两人好歹回到家里,也顾不得喂羊,只一股脑儿躲在屋里判断凶吉……其实这凶吉早已判断出来了,那肯定是凶多吉少。……不过他们还是希望会有奇迹出现。“你说这如何是好?”桂晴这时全没了主见。“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大不了我成为第五个倒霉的人。”鲍福脖子一扬,摆出一副死活论堆的样子。“什么意思?”“霍组长已经抓住四个了,到我这儿不成为第五个了吗?”“你瞧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尽说这些没用的话?还不赶快想想办法?”“主动权在人家手里,我能有什么办法?”鲍福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那你也不能在家里干等着!要不,你到工作组主动认个错。”桂晴恳求道。“认个错?你以为认个错就没事儿了?谁像你一样好说话?告诉你吧,现在正在风头上,说什么都没有用。”“那可怎么办?”桂晴急得都快哭了。“听天由命吧。”鲍福板着脸说。“不行,你要不去,我去说,真要到了不可收场的地儿,连孩子都要被挂。大人的事儿小,孩子还早着呢。”说着就要出去。“你回来。”鲍福将她拦住,声音变得柔和起来,“桂晴,咱俩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你还不了解我吗?听我的话,沉住气,常言说:‘天无绝人之路。’‘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霍仰记也不完全是六亲不认,今天他既然撞上了,却没有马上带着咱们去工作组,这里面就大有文章,说不定这事儿会不了了之。退一步说,真把我搞到上宣传车的地步,那我什么也顾不得了,我下了宣传车就一个一个地找他们算账,到那时大家都别想干净,就是鲍昭珙那老狐狸也别想滑溜了;工作组在芦花村就更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了。”他越说越激动。“你小声点儿好不好?我求你了!”“没事儿的,宝贝儿。咱们现在就去喂羊,草料既然弄来了,而且又花费了那么大的代价,怎能不让咱的羊美美地吃上一顿呢?”“要喂你自己去喂,我懒得动弹。”桂晴一动不动地坐着。“我早就说过,你呀,女人就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你不想想,你就是在这里呆上一夜也没有用啊!一点儿小事儿就把你吓成这样,幸亏你还没随我出过远门呢,不然你早就吓死一百回了。”桂晴虽然心里安慰了许多,但还是很后悔:“都是你,我说不去罢,你偏要去。”“都怪我,这行了吧?”鲍福像哄小孩子似的哄着她,“别生气了,今儿晚我好好地陪你玩儿玩儿。”“去你的。”桂晴的脸上掠过一片红晕。“你放心,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桂晴瞅一眼鲍福那若无其事的样子,再想想他从前一次次逢凶化吉的情景,心中的惧怕顿时消除了一半。她坚强地站立起来,随他一步步朝羊圈里走去……第二天,桂晴一整天没有出门,鲍福照样四处忙碌,外面没有传来一点儿风声。第三天一大早,有人向鲍福传话:“霍组长叫你去呢。”桂晴听见,分明又是一声晴天霹雳。鲍福却安慰她说:“你在家好好地呆着,我去去就来。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不会有事儿的。”鲍福尽管嘴上这么说,但心里总在大鼓。一路上他想了很多,倒不是怕挨批受罚,而是不甘心让汪清贤那臭小子看笑话。他诚惶诚恐地捱到霍组长的办公室里,问:“霍组长,您找我?”霍组长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一份印有“中共曹川地委”字样的红头文件,听到问话声,诧异道:“没有啊。”看到鲍福就要离开,忽然叫道:“回来。”鲍福像听了纶音佛语一般,忙收住脚步。“哦,可能是黄组长在找你吧?刚才我好像听到他让谁给你传话去了。”说完,他又埋头阅读起来。鲍福心里虽然轻松了一下,但那块石头仍然没有落地。他在想,黄组长找我又要干什么?莫非前天的事儿霍组长交给他处理了?不管他!进去再说。想到这里,他清了清嗓子,站在黄组长的门前高声叫道:“黄组长一早传话,有何指示?”“哈哈哈,就你小子鬼名堂多。”黄组长笑着迎到门口,“还不进来说话!”听口气,不像呀!可是,黄组长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还没有用过的信笺纸和一支自来水笔是干什么的?按照鲍福的理解,这通常是工作人员在调查情况时安排的场面。鲍福心里不住地嘀咕:看来那事儿是瞎子见鬼……成真的啦。他虽然这样想,脸上却表现得非常平静。“鲍福,是这样……”黄组长刚要说话,却被一名工作人员叫去了。不知为什么,在这当儿,鲍福一点儿畏惧感也没了,他只有一种准备:把这两天来考虑好的话端出去就是了。黄组长很快就交代完事情,坐下客气道:“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是这样,上面急着要一份材料,是关于剧团的,我觉得你对这些事情比较清楚,所以一大早就把你给折腾起来了,你可别骂我惊了你的好梦啊。哈哈哈……”我的天哪,原来是这种破事儿,你老兄怎么不早说啊?鲍福心里埋怨着,嘴里却说:“就那档子事儿嘛,我多少还知道一点儿,但不知道你让我从哪儿说起?”“这个你不必着急,我问你答,最后我再把材料整理出来。现在咱们就开始,你回忆一下,四平腔这一剧种产生于什么年代?有什么背景?它的前身是什么?创始人有哪些?”“要说产生的年代嘛,恐怕是四几年吧?反正那时我还没有出世呢。据说创始人有十三位,名字我也说不很全,这十三位老师大部分在河南和山东,也有的在山西、河北、安徽,现在仍健在的就不太清楚了,他们过去大部分是唱花鼓戏的,也有的唱坠琴、梆子、豫剧,据说郭老师是唱京剧的。准确地说,它的前身是花鼓戏。因为当时兵荒马乱,这些老艺人为了躲避灾难,才聚到一块的,经过他们一撮合,这四平腔很快就开创出来了。”黄组长一边认真地听,一边迅速地整理道:四平腔,产生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三十多年前,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晋、冀、鲁、豫、皖等地的进步艺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高举“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旗帜。为进行广泛的文艺宣传,特别是鼓舞我人民军队坚持敌后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他们将原流传已久的花鼓戏进行了加工再创作,从而形成了四平腔这样一个崭新的地方剧种。该剧种在广泛吸取了京剧、豫剧、黄梅戏、坠琴、梆子等众多剧种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艺术氛围,并广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该剧的传唱区域已由开创时的鲁豫交界处扩展为整个中原大地,大有向全国各地曼延之趋势。黄组长接着问:“那么,解放以后,这四平腔剧团又演出过哪些剧目?影响怎样?”鲍福说:“解放后,上演过《玉堂春》、《陈三姐爬堂》、《白玉楼》、《十五贯》、《唐伯虎点秋香》……最有影响的就是《乌蓬记》。当时群众有句顺口溜:‘扒了房子卖了地,也得听芦花村的《乌蓬记》……”“传统戏就不要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