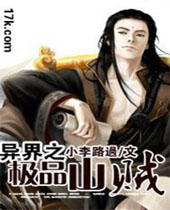盗美贼-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盒,往脸上涂了几笔,一点都没用。不管怎么弄,我还是那么苍白。脸是不听人指挥的:当我们忘记它时,它突然像黎明的旭日喷薄而出;当我们以为能控制它时,它却收缩了,起皱了。我逃到院子里:天太热了,暴风雨随时都会来临。医护车和警车接连不断。邦雅曼的离开使我。心里很烦,我失去了讲故事的人和故事的线索。
为了寻找安慰,我打电话给阿伊达。在把她送回到那群矿工当中去之前,我请一个女邻居照看她。这个小女孩是我三天来见到的惟一美好的东西。在电话里,我发现她惊恐不安。我告诉了她关于她奶奶的消息:老太太有精神错乱的预兆,加上主器官有些损坏,她必须隔离。事情显得很复杂:博埃尔迪厄夫人,这是她的名字,发现自己毁了,她在马莱的公寓多次被债权机构抵押。心理的混乱加速了经济的崩溃。扣押期临近了。我认识才24小时的阿伊达突然没有了家庭,没有了财产。她的亲人都死了,眼看要被送进慈善机构。在这令人窒息的8月,她突然遇到了这么一个奇迹。现在,她在电话里哭,求我把她奶奶还给她。医生和其他人一样,总是更喜欢悲痛者一些。但我已精疲力竭,无法同情她了。我已经老了200岁,我没有行善的义务。“对不起,阿伊达,别哭了,我帮不了你什么忙。”我答应明天去看她,然后便把电话挂了。
快到半夜的时候,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候诊室像一个凌乱的杂物堆。面黄肌瘦的小个子和破了产的坏女人发泄着对社会的仇恨,大骂警察;一个吸了毒的年轻人,瘦得非常可怕,由一个黑齿龈的女孩陪着,大声吼道:“我日你娘的,婊子,我吸你!”不知道这是请求还是威胁。一些不幸的人走投无路,过着所谓的生活;一些浑身鲜血的人伤口流着脓,吓坏了其他人。7个年轻的外国人手上持着手铐,被带进来照X光:他们被怀疑吞了藏在避孕套里的海洛因。外面,在圣母院的广场上,许多粗俗的女人躺在长凳上;对面,有个肮脏的老头,穿着衣服,衣不遮体,身体一半露在外面,正在跟天空聊天呢!一个女人围着他跳舞,掀起裙子,用手摇晃着几乎是黑色的内裤。在这乱七八糟的人群当中,警察们闻到了骚乱的味道,提高了警惕。今天下午,他们在主宫医院内部的监禁室关了一个受枪伤的无赖。红蓝两色的警灯在院子里闪着,穿着雨衣的内务警察在走廊里来来往往,对着“噼啪”作响的对讲机轻声说话。
我是为数不多的不感到害怕的人之一。这就是心理极度混乱的好处:它抑制了一般的感情,觉得把普通人吓得要死的东西非常可笑。恰恰相反,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情况不妙,所以大家都跟着我一起倒霉。如果有人对我说,有一帮精神失常的人往病人身上浇汽油,要把他们活活烧死,要刺死医生和护士,我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我会支持他们。半夜一点左右,收进来4个妓女,她们跟足球俱乐部的马德里支持者吵架,受了伤。这下可热闹了!她们进来时,一副好汉的样子,鞋跟“噼啪噼啪”地响,身上布满伤口和血肿。她们迈着骄傲的步伐,用自行车的链条绑住了企图逃跑的故人,并在他们身上挂着布满铅弹的仿造的男性生殖器。她们穿着极窄的短运动裤,挺着轻轻颤抖着的雪白胸脯。她们不像是女人,更像严肃的神灵和女巨人,只需一下就能要对手的命。我不无赞赏地望着她们,心想,自己为什么不从事这个职业,为什么不是吸满精子的妓女?所有的男人,不管年龄大小,条件好坏,都会趴在她们身上寻求痛快,发出公猪一般的嗥叫声。这些供人取乐的“女工”,要价不高,但绝对会让您痛快。在她们面前,治安警察也放松了戒备,把步枪斜挂在肩上。这些女人被消毒、缝合和包扎以后,想跟男护士们喝一杯酒。她们在长长的吸烟室尽头抽着美国烟,哈哈大笑,然后离开了医院。
夜尽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除了那几个挺着胸的妓女和一些神经紧张的病人。暴风雨终于来临了,淹没了我最后那点儿反抗的意愿。狂风暴雨袭击了斯德岛,地上水淋淋、白花花的,像啤酒一样。树木被打掉了叶子,有的烟囱和电视天线也被刮倒了,像拔离下巴的牙齿一样垂着。我在医院里闲逛,避开保安,总希望能在楼梯的拐角或门后突然听到我那个矮小的病人讲话,听到他细弱的声音。他背叛了我,这使我受到了伤害。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没有他的忏悔重要。48个小时来,我一直在想他的故事,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都比周围的人更让我感兴趣。我不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阿伊达不在,睡觉也没什么意思。天亮时,我走到六楼的外走廊,靠在栏杆上。走廊还湿湿的,下面就是花园,对面是莫贝尔和圣热内维埃夫山。屋顶层层叠叠,像是倾覆的船,闪闪发亮,退潮时被搁浅在沙滩上。天下着毛毛雨,气温下降了。雾中的艾菲尔铁塔像一个咖啡冰淇淋。我坐在楼梯上睡着了。一只肥大的雄猫走过来,靠在我身上。它眼睛亮晶晶的,布满片状的斑点。我们俩都需要友爱。
7点30分,我下班了。我去告别,当然,谁也不会舍不得我。让人恐慌到这种程度,我觉得自己挺可笑的。我可以马上去昂蒂布找费迪南,发一阵疯,当面跟他说一切都结束了。但我讨厌争吵。有些女人喜欢精神失常的人,她们爱的不是人本身,而是那种失常。她们玩弄那种不幸,从中得到满足。
我在被垃圾弄脏的广场上闲逛,夜里的那场大雨使排水沟里的水都溢出来了。我又沮丧,又慌张,精疲力竭,都忘了自己还活着了。我看起来一定像个流浪者,挎着一个一半敞开的小包,脸上化的妆已一塌糊涂。游客们守纪律地排成队,聚集在圣母院前。大家都那么听话,接连不断地在正面拍照。他们穿着短裤,坚决要来瞻仰这个圣地不可,手指按着照相机的快门,准备把上帝当场抓住。游客们非要把他们所见的东西变成胶卷才会相信,
我想在河边走一走。河堤上到处都是大小便。塞纳河,水黏黏稠稠的,拍打着桥拱,恶臭扑鼻,让人窒息。在巴黎,总有人大小便失禁,把粪便拉得让大家都看得见;水沟成了宝贝,城市管理部门发明了把粪便直接排入污水管的管道系统。我发现,那些睡在桥底下,睡在纸箱上或偶然得到被子的流浪汉到医院里来看过病。最终,我会想他们的。我上岸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要了一杯奶油咖啡和一个羊角面包。温暖的微风吹拂着皮肤,鸟儿用它们细小的喉咙发出难以置信的和谐的声音,树回应着它们的叫声。当鸟儿高兴起来时,它们也随之摇动。自动扫路机用猛烈的水龙头冲刷着地面,让人闻到一股湿漉漉的强烈的沥青味。
我在巴黎生活了8年,从未进过圣母院,对于我来说,它是属于导游们的陵墓,是世界大博物馆的一个部分。我不喜欢约定俗成的杰作。然而,那天上午,一个小小的细节使我对这个旧东西感到了兴趣:人们在清洗它,它的上半部分已消失在脚手架当中,脚手架的篷布被风刮得“噼啪”作响,具有一种戏剧的效果。这样包着,它显得特别脆弱,成了时间攻击的目标。妖魔鬼怪和檐槽喷口上的动物个个凶神恶煞,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但我在给人看病的每一天都能已到许多怪事,相比起来,那些东西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可今天,我不能一次都没进去过就离开斯德岛。
一跨进门槛,我就被吸引住了:圣母院里面就像地下小教堂一样黑乎乎的,我似乎走进了一座石柱的森林,那些柱子一根根又粗又高。我望着中殿、侧道和祭坛,听不到任阿声音。彩绘玻璃上的圆花饰似乎都是密码,每种颜色、每一根线条都象征着什么东西,但只有信徒们才看得懂。和我以前想像的恰恰相反,这地方并不庄严,但很隐秘,它由于巨大而保证了每个人的自由,众人的嘈杂声都被建筑本身给吸走了。我走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在中间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闭上眼睛,呼吸着潮湿的石头、古旧的木头和乳香的味道。一些虔诚的教徒围在燃烧着的蜡烛四周冥思,圣人的雕像在墙洞里向我发出心照不宣的信号。他们以为我就要倒下去了吗?先生们,别这么满怀热情地劝我入教。我到这儿来只不过是想放松放松。一些穿着黑衣的人正在祭坛四周忙着,撤掉花束和金色或银色的东西,把水倒进独脚盒中,有几个老太太在祈祷,双手捧着低垂的脑袋。我闭上眼睛,轻轻地呼吸着,试图忘掉晚上的一切不快。
就在这时,有人在我背后轻轻地说:
“阿亚基医生,请您别转身。”
我吓了一跳,以为是天使下凡:
“您是邦雅曼?”
“我正坐在您后面。”
“怎么……”
“今天早上,我看着您出医院、我一直跟到这里。”
“昨天您为什么不等我,为什么不告而别?”
“我心里很慌张,我说得太多了。我怕您向警察告发我。”
“警察?”
我感到愤怒起来:
“亏您想得出!”
“我觉得您很明确地反对我。”
“您完全错了。恰恰相反,我被您吸引住了。您为什么摘掉了面具?”
“我突然觉得没必要再戴了。跟您谈过话之后,我变了。”
“我可以看您吗?”
“暂时还不行。”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必须讲完我的故事。现在,我对您有了信任感。”
“听着,我不是任人操纵的木偶。我很累,我不知道能不能……”
“求您了,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不会占您很长时间的。留下吧,我们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的。”
他不容我反对,接着讲起了他的故事。
第二章 猎艳
于是,我离开了我的埃莱娜,独自和雷蒙来到巴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埃莱娜一直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一来到巴黎,我就病倒了。斯泰纳为我们临时找了个套间,在第十七区。房间阴森森的,走廊黑乎乎的。那地方很冷,也很简陋。房间太大,暖气太小。地板已经裂开,踩上去“咔咔”作响。我总是觉得冷。窗前挂着厚厚的窗帘,挡住了亮光,甚至在正午,房间里也一片漆黑。我因病卧床,连续三个星期与高烧、痉挛和腹痛作斗争。我躺在床上,情绪低落,处于衰竭之中,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那可怕的三天。在那三天里,我的生命失去了平衡,可怕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掉入了一个深渊之中,找不到出路。
我认出了雷蒙。他悉心照顾我,日夜守在我床头,毫不吝啬地给我买药水、药片,喂我喝汤。为了安全,他没有请医生。每天下午6点整,杰洛姆·斯泰纳准时用大哥大打电话来,向雷蒙发布命令,并告知关于埃莱娜的情况。我无权直接跟埃莱娜说话,但可以通过录音带联系:每个星期六,我都能收到埃莱娜的录音,但只有5分钟。反过来,我也寄给她5分钟的录音。我愉快地听着显然经过审查的录音,把她讲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埃莱娜甜蜜的声音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我根据她说话的语气和声凋来判断她是宁静还是失望。她住在“晾草架”的顶楼,关在一个没有窗、经过隔音处理的房间里。两天一次,天黑时她可以在木屋后面散步10分钟,由弗朗切西卡监视。照她的说法,她并不恨我,她在等着我回去。白天,她在房间看书。书是弗朗切西卡借给她的。比如,她这样对我说:
“我的邦雅曼,由于整天呆在床上,我发胖了。你会看到我变成一个胖乎乎的小女人了。我为你担心。我真恨自己给你惹了这样一个麻烦。你身体不好,我很挂念。我真想来到你身边,给你以温暖。”
她所有的书信都为我开脱。把她一个人扔在了那里,我感到羞愧。扔在冰雪之中的那个荒凉的高地上,任两个疯子随心所欲地折磨她,这都是我的错啊!我几次企图直接给她打电话,但每次都是斯泰纳或弗朗切西卡接电话,训我一通。我一定要埃莱娜来听电话,大喊大叫。
“邦雅曼,别孩子气了。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您想跟她说话,您得用录音机。”
雷蒙拿了埃莱娜的钥匙,去了她家,打开了信箱,听了录音电话,并模仿她的笔迹,把主要的账单都付了,免得让人怀疑她失踪。他还退掉了埃莱娜在马莱为我租的那套两居室,把我的东两搬到我存十九区偷偷留下的那个房间里。他知道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血型和社会安全号码。几个星期来,我一直密谋逃跑,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把埃莱娜从那两个魔鬼的爪子下解救出来。但我被锁在七楼的一个房间里,雷蒙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于是,我决定听天由命。除了屈服,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的身体一恢复,雷蒙就告诉了我等着我去做的事情:帮助他在巴黎找三个值得在“晾草架”经受考验的绝色女子;陪他去酒吧、饭店、夜总会等这类人聚集的公共场所,收集关于她们每个人的情况。我们采用了暗语:不能说“女人”,而要说“样品”,不再说“美”而要说“灾难”。
这是一项让人发疯的工作:侏儒和我在中午前后出门,我们手里拿着摄像机和照相机,就像游客一样,散着步,悄悄地拍下我们觉得漂亮的面孔。雷蒙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时间、地点,简单描述那个陌生女人的衣着、年龄和我们推测的职业。假如能捕捉到她谈话的碎言片语,他也一一记下。然后,我们回到漆黑的房间里放录像。他征求我的意见:我无法像给牲口盖印戳一样对那些人作出评判。雷蒙通过特快专递把候选人的照片寄给老板:老板作第一次选择,在照片边上标上记号寄回。我可以想像到那两个人戴着眼镜,在冰天雪地里,心醉神迷地检查每一张照片的情景。他们像考官一样给每一个女孩打分,要求下次选更多可爱的靓女。他们让雷蒙和我在第二轮选择中收集入围者的新材料。
我原先整天关在家里,现在成了猎人。这种变化是痛苦的。我日夜被派出去干活。下午,我们在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