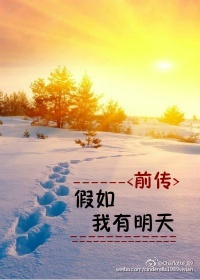假如明天来临-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哈罗,亲爱的。我是约瑟夫。罗马诺。您能帮我查查我的活期存款有多少吗?我的出生日是十月十四日。”
安东尼。奥萨蒂拿起了电话分机,过了一会儿,会计主任回到了电话机旁。
“抱歉,让您久等了,罗马诺先生。截止今天上午,您的活期存款是三十一万九百零五元三十二分。”
罗马诺的脸色一下变得煞白:“什么?”
“三十一万零九百零五——”
“你这只蠢猪!”他喊道,“我帐上没有这些钱,你弄错了。让我跟——”
他感到有人把话筒从他手里拿开,接着奥萨蒂把电话挂断了。“乔,这些钱是从哪里搞来的?”
罗马诺面无人色:“托尼,我向天发誓,关于这些钱的事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不知道?”
“您得相信我!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有人在陷害我。”
“那一定是位非常喜欢你的人。他给了你三十一万美元的送行礼物。”奥萨蒂重重地坐在一把绸面安乐椅上,盯着罗马诺看了很久,“一切都准备妥了,嗯?一张去里约的单程机票,崭新的皮箱……看来你在计划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了。”
“不!”乔。罗马诺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天哪,您是了解我的,托尼,我对您一向是忠心耿耿的。您待我就象是我的父亲。”
他满头是汗。有人敲了敲门,玛奇把头探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
“很抱歉,打扰你们了。罗马诺先生,这里有您一份电报,您得亲自签收。”
凭着落入陷阱的野兽的本能,罗马诺说:“等会儿,我正忙着呢。”
“给我看看。”奥萨蒂说。那女秘书还没关上门,他就离开了椅子。他不慌不忙地读着电文,然后把目光集中到罗马诺身上。
奥萨蒂的声音低极了,罗马诺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奥萨蒂说:“我念给你听听,乔。‘请证实您从九月一日,本周五起预定了我们的特等套间两个月。’署名是:”里约热内卢里约奥顿饭店经理S。蒙塔尔本德。‘这是你自己预定的,乔,但你现在用不着它了,对吗?“
13
安德烈。几烈安正在厨房里制做意大利粉、意大利式色拉和梨子馅饼,突然听到一阵很响的噗噗声,感到不妙。过了一会儿,中央空调器那令人舒畅的嗡嗡声消失了。
安德烈跺了一下脚说:“糟了!今天晚上还得玩牌呢。”
他急忙跑进安装着电器总开关的杂用房,把那些开关挨着个地按了一下,但毫无作用。
噢,波普先生会发怒的!安德烈知道他的主人是多么盼望每周五晚上的牌会,这已经是多年的传统了,参加者也总是那几个社会名流。没有空调,屋里会热得让人受不了!九月的新奥尔良的鬼天气只有那些大老粗才能忍受。即使在太阳落山以后,热度和湿度也和白天毫无区别。
安德烈回到厨房,看了一眼墙上的大钟,四点了。客人们将于八点到达。安德烈想给波普先生打个电话,把这事告诉他,但他突然想起这位律师说过,今天他要全天出庭。他太忙了,需要放松一下。真把人急死了!
安德烈从厨房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黑皮的袖珍电话号码本,找到号码,拨动了电话机。
铃响三遍以后,一个刺耳的声音说:“这是爱斯基摩空调服务公司,我们的维修人员现在没空。如果您能留下姓名、住址和简单的说明,我们将尽快赶去。请等候信号。”
真是活见鬼!只有在美国,你才不得不和机器说话。
安德烈听到话筒了传来一声令人厌烦的尖叫。他对着话筒说:“佩里。波普先生家,查尔斯街四十二号,我们的空调出了故障,请尽快派人来。要快!”
他砰地一声撂下电话。维修人员当然不会有空。这个该死的城市里的空调可能都坏光了。空调不可能斗得过这该死的天气。唉,但愿能快点儿来人。波普先生的脾气可大了,大得不得了。
在安德烈。几列安给这位律师当厨师的三年里,他深知他的主人是何等有势力,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再骄横的人在他面前都会变得低声下气。佩里。波普认识所有的人。只要他把手指啪地一捻,人们就会吓得跳起来。
安德烈。几列安感到屋里越来越热,如果不快点采取措施,屋里就要成蒸笼了。
安德烈一边切着意大利香肠和意大利熏干酪,心里一边嘀咕。他总有一种晚上要出事的可怕感觉。
三十分钟后,当门铃响起来的时候,安德烈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了,厨房热得象火炉。几列安赶忙跑去开门。
两名身穿工作服的工人站在门口,手里提着工具箱。一个是高个的黑人。另一个是白人,比他矮几英寸,脸上带着睡意和不耐烦的神情。在后面的车道上,停着他们的工作车。
“你们的空调出毛病了吗?”那黑人问。
“噢,谢天谢地,你们可来了。你们赶快把它修好,客人一会儿就要到了。”
那黑人走到炉子旁边,闻了一下正在烤着的馅饼说:“好香啊。”
“求求您,”几列安催促说,“快点吧!”
“让我们检查一下总开关,”那矮个子说,“在什么地方?”
“跟我来。”
安德烈带着他们匆忙穿过一条走廊,来到空调总开关所在的那间杂用房。
“这部分装置没问题,拉尔夫。”那黑人对他的同伴说。
“是的,爱尔。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装置了。”
“那它为什么不动了呢?”几列安问。
那两个人转过身来盯着他。
“你着什么急呀,”拉尔夫有点恼火地说。他跪着打开了机器下部的一道小门,取出手电筒,伸着脖子朝里面张望。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这儿没毛病。”
“那毛病在哪儿呢?”
“一定是在哪个输出口短路了。也许整个线路都短路了。你们有多少个空调送风口?”
“每间房都有一个。让我想想,至少有九个。”
“问题可能就在这里。送风量超过了负荷。让我们去看看。”
他们三个人穿过门厅,来到起居室。爱尔说:“波普先生住的地方真美啊。”
起居室布置得相当雅致,摆满了有专家签名留念的很贵重的古董,地板上铺着色调柔和的波斯地毯。起居室左边是一间很大的餐厅,右边是书房,书房中间摆着一张蒙着绿呢子的大号牌桌,屋角支起了一张准备吃晚饭用的圆桌子。那两个工人走进书房,爱尔打开手电,朝墙上端的空调出风口里照着。
“嗯,”他咕哝了一声,然后抬头望着牌桌上方的天花板问:“房顶上面是什么?”
“阁楼。”
“让我们瞧瞧。”
那两个工人跟着安德烈爬上阁楼。那是一间又长又矮的房间,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
爱尔走到安在墙上的电器箱前,查看了一下错综复杂的线路。“哈!”
“您发现什么了吗?”安德烈焦急地问。
“是电容器的问题。天气太潮了。这个星期已经有上百户人家找过我们。它短路了,得换一个电容器。”
“噢,天哪!需要很长时间吗?”
“很快。我们车上有一个新电容器。”
“那请你们快点儿,”安德烈请求道,“波普先生很快就要到家了。”
“你就放心吧。”爱尔说。
安德烈说:“我得去厨房把色拉的调料准备好。你们自己能从阁楼上下来吗?”
爱尔举起一只手。“别担心,伙计。你忙你的,我们忙我们的。”
“噢,谢谢,谢谢。”
安德烈看着这两个人走到工作车那里,提了两个大帆布袋回来。“如果你们需要什么东西,”他对他们说,“就招呼我一声。”
“放心吧!”
那两个人爬上楼梯,安德烈回到厨房。
拉尔夫和爱尔回到阁楼,打开帆布袋,拿出一张露营用的小折叠椅、一把钻头、一盘三明治、两罐啤酒、一个可以在暗光下观察远处物体的双筒望远镜和两只注射了四分之三微克乙酰普马辛的活仓鼠。
那两个人开始工作了。
“老欧内斯廷会为我感到自豪的。”爱尔大笑着说。
※※※
起初,爱尔死活不肯同意。
“你这娘们一定是疯了。我他妈的才不去惹那个佩里。波普呢。那个花花公子会把我整得永世不得翻身。”
“你不必担心他。他再也不会找别人麻烦了。”
他们俩正在一丝不挂地躺在欧内斯廷房间里那张安有电热装置的充水床上。
“亲爱的,这样做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爱尔问道。
“他是个混蛋。”
“宝贝儿,天下混蛋多的是,你总不能把一辈子都用在割掉他们的睾丸上吧?”
“告诉你,我是为了一个朋友干的。”
“特蕾西?”
“对。”
爱尔很喜欢特蕾西。在她出狱那天,他们三人曾在一起吃晚饭。
“她的确是个不错的姑娘,”爱尔承认说,“但我们为什么要为她找死呢?”
“因为如果我们不帮她,她只好去找一个连你一半都不如的人,如果她被逮着,他们就会把她送回监狱。”
爱尔在床上坐起来,吃惊地望着欧内斯廷:“宝贝儿,这事儿你真的看得那么重吗?”
“是的,亲爱的。”
她永远不能使他理解,但事实就是那么简单:一想到特蕾西要回到监狱里遭受大个子伯莎的蹂躏,欧内斯廷所关心的不只是特蕾西,而且也是她自己。她把自己看成是特蕾西的保护人,如果大个子伯莎的手再落到她身上,那就是欧内斯廷的失败。
所以,她现在只是说:“是的。这事儿对我很重要。亲爱的,你会去干吗?”
“我他妈的一个人可干不了。”爱尔嘟哝着说。
欧内斯廷知道她胜利了。她开始吻他那瘦长的身体。她喃喃地说:“拉尔夫不是已经出狱几天了吗?”
※※※
六点三十分,那两个人回到安德烈的厨房,满头是汗,浑身是土。
“修好了吗?”安德烈焦急地问。
“真他妈的难修,”爱尔说,“你看,这个电容器的交流电和直流电全断了,而且——”
“别管它了,”安德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你们修好了吗?”
“好了,全修好了。再过五分钟,我们就让它运转得象新的一样。”
“真把人吓坏了!请你们把帐单留在厨房的桌子上。”
拉尔夫摇了摇头:“不必操心,公司会把帐单寄给你们的。”
“这事儿多亏了你们二位。”
安德烈看着这两个人提着他们的帆布袋,从后门走到院子里,打开装有空调室外电路的箱子。拉尔夫打着手电筒,爱尔把他在一两个小时以前扯断的电线重新接上,空调马上运转起来。
爱尔把附在电容器标签上的电话号码抄了下来,过了一会儿,照这号码拨了电话。当他听到爱斯基摩空调服务公司的录音问话时,爱尔说:“这里是查尔街四十二号佩里。波普家的住宅。我们的空调现在运转得很好,不必派人来了。谢谢。”
※※※
每星期五晚上,在佩里。波普家里举行的牌会,是所有参加者都热切盼望的一件事情。牌友从来都是几个经过精心挑选的人:安东尼。奥萨蒂、乔。罗马诺、一个高级市政官、一个州参议员,当然还有他们的东道主。赌金高得吓人,食品异常精美,宾主权倾四方。
佩里。波普在寝室换上一条丝质白裤子和一件运动衣。他愉快地哼着歌,想着即将来到的晚上。他最近手气很好。事实上,我一生的运气都不错,他想。
在新奥尔良,如果有谁想得到法律的帮助,就得找佩里。波普律师。他的权势来自跟奥萨蒂一帮人的勾结。从违章驾驶的传票到贩卖毒品罪,以至谋杀罪,都属于他的权力范围。生活真是妙不可言。
当奥萨蒂到达时,他带来了一位客人。“乔。罗马诺不会再来玩牌了,”奥萨蒂宣布说,“纽豪斯督察是诸位的老相识。”
大家互相握了握手。
“先生们,饮料在食品柜上,”佩里。波普说,“今天开饭晚点儿。我们为什么不先来几把呢?”
大家按以往的位置围着书房的绿呢台布坐下来。奥萨蒂指着罗马诺过去的位置对纽豪斯督察说:“梅尔,今后这就是你的座位。”
其中一人打开一幅新牌,波普开始发筹码。他向纽豪斯督察解释道:“黑的代表五美元,红的代表十美元,蓝的代表五十美元,白的代表一百美元。每人先买价值五百美元的筹码。我们在桌面上投注,可以分三次注,由庄家决定。”
安东尼。奥萨蒂的心情很不好:“好啦,让我们开始吧。”他的声音低沉。这不是个好预兆。
佩里。波普很想知道罗马诺到底出了什么事,但他知道还是不涉及这件事为好。奥萨蒂到时自然会跟他提起的。
奥萨蒂的思绪很乱:我待乔。罗马诺就象父亲一样。我信任他,提拔他为我的第一副手。而这个婊子样的却在背后捅了我一刀。如果不是那个昏头昏脑的法国女人打来电话,他可能已经得逞了。是的,他再也跑不了啦。既然他那么精明,就让他跟那些犯人较量好了。
“托尼,您下不下注?”
奥萨蒂把他的注意力转回到牌上。赌桌上的输赢已有明显差距。奥萨蒂一输就火,但并不是因为钱。不管什么事,要他败在别人手下,他可忍受不了。他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胜者。只有胜者才能在现实生活中爬到他这样的地位。在过去的六个星期,佩里。波普不知为什么一直手气很好。今天晚上,奥萨蒂决心打个翻身仗。
今天是由庄家决定打法。但是,不管玩哪一种花样,奥萨蒂发现自己总是输。他开始加大赌注,不顾一切地想捞回本来。午夜时分,当他们暂时休战,去吃安德烈准备的晚饭时,奥萨蒂已经输了五万美元,而佩里。波普又成了大赢家。
食品精美异常。奥萨蒂通常非常欣赏这免费的夜宵,但今天晚上,他却急不可待地要回到牌桌上去。
“你还没吃东西呢,托尼。”佩里。波普说。
“我不饿。”奥萨蒂拿起身旁的银咖啡壶,往一只维多利亚式样的瓷杯子里注满咖啡,然后在牌桌旁坐了下来。他看着其他人吃饭,真希望他们能快点。他急于把钱捞回来。当他开始搅动咖啡的时候,仔细地看了一下,好象是泥灰。他抬头望了望天花板,又有什么东西掉到他的额头上。他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