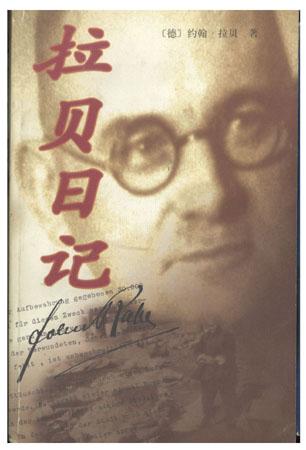阿达拉-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阿达拉》
序曲
法兰西从前在北美洲拥有一大片领地,从拉布拉多延展到佛罗里达,从大西洋沿岸一直到上加拿大的内湖区。
四条大河发源于同一条山脉,分割了这片辽阔的土地:圣洛朗河滚滚东流,注人同名的海湾;滔滔的西河水流入无名的海洋;波旁河由南向北冲来;倾人赫德森湾;而密西西比河则由北向南流去,直泻墨西哥湾。
一千多法里①长的密西西比河,浇灌着一片片美好的土地,美国称之为新伊甸园,而法国人则给它留下个路易斯安那的芳名。密西西比河的千百条支流,诸如密苏里河、伊利诺伊河、阿肯色河。俄亥俄河、沃巴什河、田纳西河等,以其淤泥肥沃,以其水流滋润这片土地。每逢冬季河水上涨,每当风暴刮倒森林的一片片树木,那些连根拔起的树木便汇集到源头;不久,树身结住污泥,缠满藤葛,杂草丛生,残骸终于板结起来,又被激流冲走,漂入密西西比河。这些残骸一旦落入大河的掌握之中,便被浪涛推涌,直至墨西哥湾,搁浅在沙滩上,从而分隔出更多的入海口。密西西比河奔流咆哮,穿越崇山峻岭,漫溢的河水围住森林的高树和印第安人的坟墓,赛似流经荒漠的尼罗河。然而,大自然的景象,优美和壮丽往往相辅相成:只见大河中流携带松树橡木的残骸奔向大海,而两侧的缓流,则漂着开满玲楼绣阁似黄花的绿萍睡莲岛,仿佛沿河岸溯流而上。还有那一条条绿蛇、幼鳄、一只只青鹭、红鹳,如同游客登上花船,迎风扬起金帆,在睡眠中驶向某处偏僻的河湾——
①1法里约合4公里。
密西西比河两岸的风光特别雄奇。西岸大草原一望无际,绿色波浪滚滚远逝,仿佛飞升并隐没在蓝天之中,但见茫茫草原上,游荡着三四千头野水牛,偶尔还能见到一只老野牛劈浪游向河中的荒岛,要在那高高的蒿草中宿眠。望着它那装饰两个弯月的额头、沾了污泥的苍须,您准以为那是河神,正满意地眺望浩浩河水和富饶的野岸。
西岸景色如此,对岸则是另一番景象,两岸相映成趣。东岸形形色色、芳香各异的树木,有的一簇簇从山岩垂悬在水流之上,有的散布在峡谷之中,交错混杂,一起生长,向高空攀援,看上去令人目眩。树脚下野葡萄、紫葳、药西瓜纷披盘绕,爬上枝头,由械树梢攀到郁金香,由郁金香攀到药蜀葵顶,构成千百个洞窟、拱顶和拱门。这些藤葛在树木间乱窜,往往越过河汉,架起一座座花桥。蕃茂的草木中,木兰树亭亭玉立,枝头开满大白花,高出整片森林,惟有邻近的那株轻摇碧扇的棕润可与之媲美。
造物主将大批鸟兽安置在这蛮荒之地,使之充满生机和魅力。只见在路径的尽头,黑熊饱餐了葡萄,醉醺醺的,倚在榆树的枝权上摇晃;野鹿在湖中洗浴;黑松鼠在繁枝茂叶中嬉戏;嘲鸫鸟、个头儿跟乌鸫一样大小的弗吉尼亚野鸽,飞落到由草莓染红的草地上;黄头绿鹦鹉、紫色啄木鸟、红雀,在柏树冠顶跳来跳去;蜂鸟在佛罗里达的茉莉花上闪亮,而捕鸟蛇咝咝叫着,倒挂在树梢儿摇曳,好似一条条藤蔓。
对岸的大草原一片宁静,这边则不然,无不在活动,无不在絮语:鸟喙啄橡木于的声响、动物在走动,吃草和咀嚼果核的声音、哗哗的波浪声、草虫的微吟、野牛的低吼、鹧鸪的轻啼,使荒野充满温良和犷野的和谐。每当刮起一阵风,这荒僻之地便活跃起来,摇动这些浮荡的物体,将这些雪白、碧蓝、翠绿、粉红的花团锦簇交混杂陈,揉合各种颜色,汇集各种声响,于是,这种和声便从密林深处传出,而眼前又展现这样奇妙的景物,我真想描绘出来,但是力不从心,不能让没有游历过的人领略这大自然的处女地。
自从马盖特神父①和不幸的拉萨勒②发现密西西比河之后,第一批移居到比洛克西和新奥尔良的法国人,就同当地强大的印第安部族纳切斯结成联盟。后来,纷争和嫉妒血染了这片好客的土地。在这些土著人里,有一位名叫夏克塔斯的老人,因其年长,明智而有阅历,当上了族长,受到荒原族人的爱戴。他同所有人一样,是用不幸的遭遇买来了德行。他不仅在新大陆的密林中屡遭磨难,而且磨难还一直追随他到了法兰西的岸边。他蒙受奇冤,在马赛身陷囹圄,被押上战舰服苦役,释放之后,他觐见了路易十四,还会见了当世的名人,出席过凡尔赛宫的庆典盛会,观赏过拉辛③的悲剧,聆听过博须埃④所做的悼词,总之,这个野蛮人见过大世面——
①雅克·马盖特(1637—1675),法国耶稣会教士,他于1673年发现密西西比河。
②卡夫利埃·拉萨勒(1643—1687),法国旅行家,他家看了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河流。
③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的伟大悲剧作家。
④博须埃(1627—1704),法国散文作家,大主教,布道演说家。
夏克塔斯返回本上多年,一直享受宁静的生活,不过老天也让他为这种恩惠付出高昂的代价:老人双目失明了。一位年轻姑娘陪伴他在密西西比河畔的山丘上游荡,犹如安提戈涅搀着俄狄浦斯①在锡得龙山流浪,又像玛尔维娜领着渥西恩②在莫尔旺的山岩上跋涉——
①俄狄浦斯:底比斯王,受命运的打击双目失明后,由女儿领着流落他乡。
②渥西恩:苏格兰传说中莫尔旺古国的王子,游吟诗人兼斗士,玛尔维娜是他的未婚妻。
夏克塔斯在法国虽有种种不公正的遭遇,但他还是很喜爱法国人,总记得曾接待过他的费纳龙①,想为那位德高望重者的同胞尽点儿力。终于有了这种机会。1725年,一个名叫勒内的法国人,在激情和不幸的驱使下,来到路易斯安那,他沿着密西西比河边溯流而上,一直走到纳切斯人的住地,恳求接纳他为这个部族的武士。经过盘问,夏克塔斯认为他的决心不可动摇,便收他为义子,将一位名叫赛吕塔的印第安姑娘许配给他。婚后不久,部族人就准备开投去猎海狸——
①费纳龙(1651—1715),法国散文作家,主教。
夏克塔斯深受族人的敬重,虽然双目失明,仍被萨尚①会议指定出面指挥这次远征。于是,开始祈祷和音戒:算卦者圆梦;大家求马尼杜神②显灵;献祭烟草;焚烧麋鹿的舌带,观其是否在火中发出声响,据此来判断神灵的意愿;最后,他们吃了圣狗肉,终于启程了。勒内也排在队列中。他们借潮水的推动,乘坐独木舟,沿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再拐进俄亥俄河。时值金秋,辽阔壮美的肯塔基荒原展现在这个法国青年的眼前,令他惊叹不已。一天夜晚,月光清亮,所有纳切斯人都在独木舟中安睡,这支印第安船队扬起皮帆,在微风中行驶。勒内单独和夏克塔斯在一起,请他讲一讲一生的险历。老人答应满足年轻人,同他坐在船尾,讲述了如下的故事——
①萨尚:老人或参谋——作者原注。
②马尼杜:北美印第安人信仰的神。
一 猎人
我亲爱的孩子,我们俩聚在一起,是一种奇特命运的安排。我看你是变成野蛮人的文明人,而你看我则是天意要变为文明人的野蛮人(是何意图,我也不得而知)。我们二人从两个极端进入人生,你到我的位置上来安歇,而我也曾坐过你的位置:因此,我们俩看待事物的观点,也势必截然相反。可是,对你我来说,这种地位的变动,究竟谁是最大的赢家,谁是最大的输家呢?只有神灵知道,因为最无知的神灵,也比所有人加在一起还聪明。
我母亲在密西西比河畔生下我,到下一个花月①,距今就有——
①即5月——作者原注。
七十三次降雪①了。那时,西班牙人刚在彭萨科拉湾落脚,还没有一个白人到路易斯安那定居。我刚刚数到十七次落叶②,就和父亲,乌塔利西武士一道出战,对抗佛罗里达强大的部落摩斯科格。我们和西班牙人结为同盟,在莫比尔河的一条支流上激战。然而,阿里斯古依③和马尼杜神不助我们。结果敌人获胜;我父亲战死,我在保卫他时两处负伤。唉!当时我怎么没有下到灵魂国④呢,也免得后来在世上屡遭不幸!可是神灵却另有安排:我被溃逃者带到圣奥古斯丁⑤——
①以降雪计年,即73岁——作者原注。
②以落叶计年,即17岁。
③即战神——作者原注。
④即地狱——作者原注。
⑤圣奥古斯丁:美国最早的城镇,由西班牙人始建于1565年。
来到西班牙人新建的这座城镇,我很有可能被抓走,送到墨西哥矿山。幸而,一位西班牙老人被我的年轻和淳朴所打动,收留了我,把我介绍给他胞姐。他名叫洛佩斯,是卡斯蒂利亚地区人,没有妻室,同胞姐一起生活。
两位老人待我十分亲热,精心培育我,给我请来各科的家庭教师。我在圣奥古斯丁住了三十个月,厌倦了城镇的生活,眼看着越来越委靡不振:我时而直愣愣的,一连几小时凝望远处的密林冠顶,时而坐在河边,凄苦地注视着流水。我想像着这波浪所流经的一片片树林,心灵便充满孤独之感。
我渴望重返荒原,再也忍不住了,一天早晨,便换上土著服装,一手拿着我的弓箭,一手托着欧洲人的衣裳,去见洛佩斯。我把那套衣服还给我的慷慨的保护人,扑倒在他脚下,不禁泪下如雨。我咒骂自己,谴责自己忘恩负义,我对他说:
“我的父亲啊,到头来,你本人也看明白了,我若是不重过印第安人的生活,就非死掉不可。”
洛佩斯非常诧异,他想打消我的念头,向我指出我会碰到的危险,可能会重又落入摩斯科格人的手中。然而,他见我义无反顾,便失声痛哭,紧紧搂住我,高声说道:
“走吧,自然之子!恢复你作为人的独立性吧,洛佩斯绝不想剥夺你的自由。我若是还年轻,就肯定陪同你去荒原(那里也有我的甜美回忆!),把你送回母亲的怀抱。回到森林之后,你有时也要念起收留过你的这个西班牙老人,而你要去爱人类的时候,记住你对人心的第一次体验,就完全有利于这种爱。”
最后,洛佩斯祈祷上帝保佑,尽管我拒绝信奉基督徒的上帝。接着,我们就挥泪而别。
我这样忘恩负义,不久便受到了惩罚。我缺乏经验,在树林中迷了路,正如洛佩斯所预言的那样,被一伙摩斯科格和西米诺尔人捉住。他们一看我的服装、头上插的羽毛,就认出我是纳切斯人。他们见我年轻,捆绑我时绳索勒得不太紧。那伙人的头领叫西马干,他问我的姓名,我回答道:
“我叫夏克塔斯,是乌塔利西的儿子,是削了一百多摩斯科格英雄头皮的密斯库的后裔!”
西马干对我说道:
“好啊,夏克塔斯,你这乌塔利西的儿子,你这密斯库的后裔,这回痛快了;一到大村子,就把你烧死。”
我接口说道:“那好极了。”随即就哼唱起我的挽歌。
我尽管被俘,头几天就禁不住赞赏起我的敌人。这些摩斯科格人,尤其他们的盟友西米诺尔人,都那么欢欢喜喜,洋溢着爱和满足。他们的步履轻捷,待人平和而胸怀坦荡。他们爱讲话,讲起来口若悬河,语言和谐优美而又明白易懂。那些尊长虽然上了年纪,也不减淳朴快乐的性情,好似林中的老鸟儿,一听见子孙唱起新歌,就要随声附和。
随队同行的妇女见我年纪轻轻,都表露出一种温存和悦的怜悯、一种善气迎人的好奇。她们问我有关我母亲和我幼年的情况,想知道我的苔藓摇篮是否吊在枫树的花枝上,是否由风儿推着在小鸟儿窝边摇摆;继而,又问我的心态,提出一大串问题,问我是否梦见过白鹿,秘谷中的树木是否教会我恋爱。我天真地回答这些母亲、妻子和女儿的问题,对她们说:
“你们是白天盛开的鲜花;黑夜就像清露一样爱你们。男人一离开母腹,就是要吮吸你们的rǔ头和嘴唇。你们的话有魔力,能抚慰所有痛苦。这就是生下我的人对我讲的,可是她再也见不到我啦!她还对我说,处女是神秘的鲜花,到僻静的地方才能找到。”
这些赞美深得这些女人的欢心,她们塞给我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给我送来核桃酱、枫糖、玉米糊、熊腿肉、海狸皮,以及用来装饰我的贝壳、为我垫着睡觉的苔藓。她们同我一起唱歌,欢笑,继而想到我要被烧死,又纷纷流下眼泪。
一天夜晚,摩斯科格人在一片森林边缘宿营。我坐在“战火”旁边,由一名猎人看守,忽然听见草上悉索的衣衫声音,只见一位半遮面纱的女子来到我身边坐下。她的睫毛下滚动着泪珠,而胸前一个小小的金十字架,在火光中闪闪发亮。她美得出奇,脸上透出一种说不出来的贞洁和激情的光彩,特别引人注目,具有无法抵御的魅力。她不但非常美,而且极其秀雅温柔,眼神里流露出锐感多情和极痛深悲;那粲然一笑,更是美妙绝伦。
我以为她是“临刑之爱的贞女”,即派到战俘身边给他坟墓施魔法的贞女。我一确信这一点,虽不惧火刑,心里也一阵慌乱,结结巴巴地对她说:
“贞女啊,您配得上初恋的爱情,生来不是为了临刑之爱的。一颗很快就要停止跳动的心,很难回应您的心声。怎么能将死和生结合起来。您会引得我苦苦留恋人生。但愿另一个人比我更幸运,但愿长长的拥抱将青藤和橡树结合起来!”
于是,少女对我说:
“我根本不是‘临刑之爱的贞女’。你是基督教徒吗?”
我回答说,我从未背叛过自己部落的神明。印第安姑娘听了我的答话,浑身不禁一抖,她对我说:
“真可怜,原来你是个地道的邪教徒。我母亲让我入了基督教。我叫阿达拉,父亲就是戴金手镯的西马干、这一部落武士的首领。我们正前往阿帕拉契克拉,到了那里你将被烧死。”
阿达拉说罢,便起身走开了。
(夏克塔斯讲到此处,不得不中断叙述。往事像潮水一般,冲入他的脑海,失明的眼睛涌出泪水,流到饱经风霜的面颊上,好似深藏地下的两股泉水,从乱石堆中渗透出来。)
(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