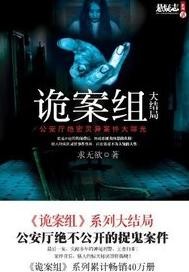荒岛夺命案-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每一次都朝了另一个方向拐去了。巴克斯在守护着我们呢。”他又解释说,“巴克斯是酒神。”
“和一个极好的作曲家。”
“那是巴赫。”
“对。”
“顺便提一下,我们这儿有音乐会,有时有歌剧。我可以把你加到我们的投递单中,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发现我们正朝那大木条复合体走。我说:“这太好了。酒,歌剧,好伙伴。我会把我的名片透过来。这会儿用光了。”
当我们朝酒厂走去时,我四下看看说:“我没看到你的房子。”
“我实际上不住这儿。在塔楼顶部我有一个位处,但我的房子得从这儿往南去。”
“在水上?”
“是的。”
“你用船吗?”
“偶尔。”
“帆还是机动?”
“机动。”
“戈登夫妇曾是你屋子里的客人?”
“是的,有几次。”
“他们乘船而来,我猜。”
“我相信他们来过一两次。”
“你乘自己的船去拜访过他们吗?”
“没有。”
我准备问他是否他有一辆白色“保时捷”,但有时还是不要问一些你能以其他途径发现答案的问题。问题会向人泄露秘密,会把他们吓着。弗雷德里克·托宾,像我说的,不是一个谋杀嫌疑犯,但我有一种印象:他隐藏了什么事情。
托宾先生领我穿过出口。他说:“如果有什么再需要我帮忙的,请通知我。”
“好的……啊,我今晚有个约会,我想买瓶葡萄酒。”
“试试我们的墨尔本红葡萄酒。九五年度的无与伦比。但价钱稍微高一点。”
“你为什么不给我看?我还有几件东西要包一下,不管怎样。”
他迟疑了片刻,然后领我进了礼品店。它连在一个宽敞的品酒厅旁。是一间非常漂亮的房间,有三十来尺长的橡木品酒吧台,另一边是半打售货亭,到处都是葡萄酒箱子,架子,染色玻璃窗,菱形玻璃瓦地板,等等。十多个爱喝葡萄酒的人在房间里漫步,评论商标,或在吧台旁咕嘟咕嘟地喝免费酒。与正在倒酒并努力微笑的年轻男人和女人作愚蠢的交谈。
托宾先生对其中一个倒酒者问了声好,她叫莎拉,一个漂亮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女子。我猜测弗雷德里克自己挑选的家具,他对漂亮干净的东西很有眼光。老板说:“莎拉,倒酒给……先生……”
“约翰。”
“给约翰倒一点九五年的墨尔本酒。”
她照办了,手很稳当。倒进一个小杯子里。
我晃了晃那酒,显示我很在行。我吸了一下,说:“香味很好。”又把它举到灯旁说,“好颜色。紫色。”
“还有优美的手指。”
“哪里?”
“它们推杯子的样子。”
“对。”我呷了一小口。
我想,还可以。那提炼出来的纯昧,其实和牛排一起吃应该不错。我说:“有葡萄昧,很友好。”
托宾先生热情地点着头。“是的,而且激烈。”
“非常激烈。”激烈?我说,“这比纳帕墨尔本昧儿更重更强劲—些。”
“实际上,是更淡一些。”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本应见好就收。“好。”我放下玻璃杯。
托宾先生对莎拉说:“倒九五年卡百纳酒。”
“这就够了。”
“我想让你看看有什么不同。”
她倒了,我尝了尝说:“好,不那么烈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托宾先生坚持要我再尝一种白葡萄酒。
他说:“这是我用夏敦埃和其他几种我不想透露名称的白酒混合而成的,色泽很美,我们管它叫秋日澄金。”
我尝了一口:“很宜人,但不太烈。”
他不回答。
我说:“你曾想到过要把你的酒命名为‘愤怒的葡萄’吗?”
“我会让我市场部的人采纳这个建议。”
我评论道:“好商标。”
托宾先生告诉我:“我所有的红葡萄酒都贴有波洛克派的艺术标签,我的白酒上标签是德库宁的。”
“是这样的吗?”
“你知道——杰克逊·波洛克和威廉姆·德库宁。他们都住在长岛,在这儿创作出他们的一些最佳作品。”
“哦,那些画家。对,波洛克是个角色。”
托宾先生没有答话,但膘了一眼他的手表,显然是厌倦了我。
我四周看看,发现一空货亭,远离倒酒的人和顾客。我说:“让我们到那儿坐一分钟。”
托宾先生不情愿地跟着,在货亭里和我相对面坐。我呷了一口卡百纳,对他说:“就几个标准问题。你认识戈登夫妇多久了?”
“哦,大约一年半。”
“他们和你谈论他们的工作吗?”
“不。”
“你说他们喜欢讲普拉姆岛的故事。”
“是的,哦,泛泛而谈。他们从不泄露任何政府秘密。”他微笑着。
“这就好。你知道他们是业余考亩学者吗?”
“哦,……是的,我知道。”
“你知道他们属于匹克尼克历史协会吗?”
“是的,事实上,这是我们认识的起因。”
“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一员。”
“协会大约有五百个成员。不是每个人都是。”
“但每个我遇到的人都好像是。这是不是像一个别的什么的掩护组织吗?”
“据我所知不是。但那样的话会很有趣。”
我们都微笑了。他看上去像是在思索什么;我可以判断出一个人是否在思索,而且我从不打断一个思索者。最后,他说:“事实上,匹克尼克历史协会星期六晚上要开个晚会。我在我的后草坪上做东。这个季节的最后一个露天晚会。如果天气允许的话,你为什么不来参加呢?”
我猜想现在戈登夫妇不能来,他就多出两个空位来了。我答道:“多谢。我尽量来。”实际上,我不会错过的。
他说:“麦克斯威尔警长可能来。他了解所有细节。”
“好极了。我能带上些东西吗?比如酒?”
他有礼貌地笑了。“只带上你自己。”
“和一个客人。”我提醒他。
“是的,一个客人。”
我问托宾先生:“你曾听到过什么……什么关于戈登夫妇的闲话吗?”
“比如说?”
“哦,比如说,性。”
“一个字也没听到过。”
“财政问题?”
“我不会知道的。”
一轮又一轮,我们又呆了十分钟。有时你会发现一个人在撤谎,有时不会,任何谎言,无论多么小,都是有意义的,准确地说,我并末抓住托宾在撒谎,但我非常肯定他关于戈登夫妇知道的比他透露出来的要密切得多。就事情本身而言,这不是很重要,我问托宾:“你能列举出随便哪一个戈登夫妇的朋友吗?”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好,我说过的,你的同事,麦克斯威尔警长,就是一个。”他又说了几个其它人的名字,但我不认识。
他说:“我真不大了解他们的朋友和职业合作者们。我说过……哦,让我直说吧——他们有点儿类似于食客。他们漂亮,谈吐不凡,又从事有趣的工作,又都是博士。你可以说我们都从这种安排中得到了些什么……我喜欢我周围聚集一些优雅又有意思的人。是的,这有点儿浅薄,但你会惊讶于这些有趣而美丽的人们是多么的浅薄。”他又补充道,“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我很难过,但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什么了。”
“你已经帮了很多了。托宾先生。我真的很感激你的时间,而且很欣赏你没有弄来一个律师把事情搞大。”
他不回答。
我快步走出货亭。他也一样。我说:“你会陪我一起走到我的车边吗?”“如果你乐意的话。”
我在一个柜台前停下来,那儿有许多关于酒的书,包括一些关于托宾葡萄园的小册子。我收集了一套,把它们扔进我的小包里。我说:“我是那些手册迷中的一个。我有从普拉姆岛上拿来的所有的册子——关于牛痘,糙皮病——反正,我从这件案子上受了—次真正的教育。”
他又一次不答话。
我请他帮我找到九五年墨尔本酒,这是他说过的。我顺便提一下那标签说;“杰克逊·波洛克。我从来没猜到。现在今晚约会时我有话可说了。”我把酒拿到出纳员处,如果我以为托宾先生准备把它归于好意而予以报销的话,我就错了。我付了全价,加上税。
我们走出来,走进阳光里。我说:“顺便提一下。我曾和你自己一样,是戈登夫妇的熟人。”
他停下来不走了,而我也停下来。他看着我。
我说:“约翰·柯里。”
“哦,……是的。我记不起这名字了。”
“柯里。约翰。”
“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你是那个受伤的警察。”
“对,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你不是一个纽约市的侦探吗?”
“是的,先生。被麦克斯威尔警长聘出来帮忙。”
“我明白了。”
“那么,戈登夫妇提到过我。”
“是的。”
“他们说了我什么好话吗?”
“当然他们说了,但我不怎么记得清了。”
“我们实际上见过一次。七月份。你在你那大房间里开了一次大的尝酒会。”
“哦,是的……”
“你穿一件紫色西服和一条饰有葡萄藤图案的领带。”
他瞟着我。“是的,我想我们确实见过面。”
“这是无疑的。”我向四周卵石地看去,评论道,“如今每个人都有四轮传动装置了。那边是我的。它说法语。”我解释说,当我遥控发动时。我问托宾先生,“你的白色‘保时捷’在那边吗?”
“是的,它在那边。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只是想它有可能是。你是一个‘保时捷’型的家伙。”我伸出手,我们握手。我说:“我可能会在你的晚会上看到你。”
“我希望你发现是谁干的。”
“哦,当然我会。我总是这样。Ciao①。Bonjour。②”
“Bonjour就是你好。”
“好的。Aurevoir。③”我们分手了。我们的脚步嘎吱嘎吱踩在硬石路上。朝相反的方向去。蜜蜂追我到车边。但我迅速钻进车里,开走了。
我想着弗雷德里克·托宾的事。这个业主,“保时捷”,所有美的事物的鉴赏者,当地的大腕,死者的熟人。
我的职业敏感告诉我他很滑溜。我不应该再花一分钟考虑他。关于戈登夫妇为什么被谋杀和谁是凶手,我已推出的理论没有一条符合托宾先生。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要继续跟踪这位绅士。
①意大利语,再见。
②法语,你好。
③法语,再见。
第17节
我沿着主干道向西开,一边试图读懂汽车驾驶手册。按了几下挡泥板的按钮,那边的“指示”框上便显示所有数据,百分之百的美国性能。这应该是坐在车子前座上能做到的最有趣的事。
当下我感觉技术上长进不少,于是拿自己的蜂窝式电话打通我的电话留言机。“我告诉你,要是那些人现在看到我们正驾车经过这些旧农庄和村落——”
这时留言机答道:“您有三条留言。”
有一条一定是贝思留的,但事实上是麦克斯。他重申我不要再管这案子,叫我回个电话,我可不愿意。第二条来自法纳利:“晴!约翰·柯里,听我说,如果你需要从那儿脱身出来,只管叫我。同时,我有一些关于开枪者的线索,所以我不想到处张扬,除非你需要帮助。为什么这么多人想杀死我的搭档?嗨,我和沃尔夫私下谈过了,他不相信电视上的人不是你,而且说有消息证实是你,要你接受他的质询。我建议他监听你的电话,现在就是了,可要少惹麻烦。”
“谢谢。”
最后一条也不是贝思的,正是我的顶头上司安德鲁·沃尔夫中尉。他只讲了句,“望你尽早回个电话给我。”事情不妙。
我怀疑纳什和沃尔夫是否真认识,但无疑纳什的确已告诉沃尔夫电视上的人就是约翰·柯里,而且正在疗养期间破一起凶杀案。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猜测沃尔夫正想从我这得到解释。我想自己能解释是怎么卷进这起案件的,但很难解释为什么沃尔夫中尉在约翰口中却成了个傻瓜。
前后思量了一番,看来最好是不回电话,也许应该找律师。没有做好事不受惩罚的,我是说,我在竭力做个好公民,丽说服我卷入案件的那家伙,我的伙伴麦克斯,窃取我的脑力劳动的成果,又让我同联邦特工搞可恶的竞争,甚至还把我的徽章取走了,事实上他从未给过我徽章。贝思还是没有电话。
我一直提醒自己做个英雄,但我确信遭到枪击不会是英雄行为。还是孩子的时候,只有向坏家伙开枪才是英雄,可眼下每个生病的,遭劫持或枪击的都成了英雄。可我如果能利用这次英雄事迹摆脱可恶的麻烦,我当然会做。问题是媒体创造的英雄只有大约九十天的短命,我在四月中旬遭枪击,也许该通知我的律师了。
现在我正从卡桥格村开往城区,如果你不注意我的车一下子就会开过去。这个村庄历史悠久,古雅干净,与大多数村庄一样繁荣,我猜部分原因在于葡萄酒生意。大街上拉着各式广告的横幅,比如每年一度的东区港海洋节,还有在霍顿角灯塔举行的伊索托普爵士舞专场音乐会。多的就不用说。
嗯,夏天正式结束了,对于当地居民和一小部分的游客来说秋季也有许多事可做。我总怀疑这儿每年十一月都要举行一场只对本地人开放的大型聚会,名字就叫“北福克居民庆祝游客滚蛋的狂欢节。”
就这样我一边慢速开车一边留心那幢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房屋,我记得在主干道附近。大路的南面是有村庄的绿化带,宣称坐落有纽约最古老的房子,标志上写着大约在一六四九年。这儿看上去不错,我驾车沿着一条窄道穿过绿化带,上面坐落着一些由老式隔板和木瓦砌成的建筑物,幸亏没有颈手枷、木桩、浸水凳或者其它早期美国人为受虐和施虐者准备的公共陈列物。
终于我看见离村庄绿地不远处有一间白色大房子,隔板制的,很像一间大楼,前面有几根高高的白梭子。草坪上竖着一块木制齐乎达尔风格的标志牌,写着“匹克尼克历史协会”几个字,下面写着“博物馆”和“礼品店”,“店”字拼成了两个“p”和一个“e”。我曾经赢过一次拼宇游戏,里面就有这个词。
由两条短链子悬着的另一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