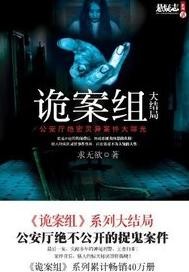荒岛夺命案-第6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一种自信——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推拉着我向托宾和奇德上校的藏宝地前进。我仿佛清楚地看见我和托宾还有那批财宝在一起,我们的周围全是死去的人——汤姆和未迪、墨菲夫妇和爱玛,还有奇德本人。
地势在上升,我也意识到自己正在一片开阔地的边缘。另一侧,在黑色地平线的映衬下我能认出是两幢小建筑。我知道那就是废弃了的特瑞要塞。
我在周围找了找标记,又发现一节绳子悬在树上,这是托宾从树林里出来的地方,也将是回来时进树林的路。显然,我脑子里惯有的导航系统运转良好。如果我现在是一只候鸟一直向南,一定能准确飞抵佛罗里达。
不必惊讶,托宾正在向特瑞要塞迸发,实际上普拉姆岛上所有路径都在那儿会合,而且在废弃的建筑群及附近的军事燃料库里可以找到数百个绝佳的藏身之处。
我知道如果等在这儿的话,在他回来时能够伏击他。可我现在宁愿做个潜步追踪猎物的猎手,也不想当个耐心的伏击手。
又过了几分钟,我想确信是否有人端着来福枪正在远处空地边等着我出现。从大多数战争片判断我知道不应该穿越空地——应该迂回前进。可我如果那样,要么会丢掉托宾,要么就会使自己迷路。我必须走他已经走过的路。雨现在越下越大,风速也正在上升,真是惨极了。我回过头,张开嘴,让雨水顺着脸庞流进喉咙,这样感觉好多了。
我走进空地,继续向南走。脚上的布衣服已被撕破,双脚不仅疼痛而且在流血。我不断提醒自己要比健步如飞的托宾坚强得多,而且现在我所需的只是一颗子弹和一把刀。
我走近开阔地的尽头,看到一条窄窄的林间小路将开阔地和广阔的特瑞要塞分开。我没有办法知道托宾往哪去了,现在不会再有路标,因为大楼现在就是他的路标。我能做的就是继续前进。
我曲曲折折地从一个楼房转向另一个楼房,寻找托宾的任何踪迹。过了大约十分钟,我发现眼前是过去的总部大楼,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托宾的踪迹。他可以从这儿去任何方向——向南到外围的海滩,向西到主大楼,或者向东上到猪排骨状的山坡。或许他可以伏在什么地方等着我走得更近些,甚至有可能无意之中和他错过去,就像在海上一样让他绕到我后面,那就不妙了。
我决定检查一下要塞里的其它建筑,于是低头弯腰,开始向教堂跑去。突然,我听到一声枪响,一下子扑倒在地。我一动不动,又是一声枪响,但都是零星的经过消音的枪声。没有清脆的声响,更没有任何东西从我头上呼啸而过,原来并不是对着我开的。
我全速冲到教堂挡板的一侧,朝枪响的方向望去,能看到50码开外的消防站,我忽然想到有人在那里开的枪,所以加上消音器。
我开始向消防站靠近,可是当头顶上的大门开始打开时又很快趴到地上。那门好像是左右摇晃着慢慢上去的,仿佛有人正拉着滑轮上的绳子打开它。我注意到这儿电力业已中断。可我看到楼上的窗户里有微弱的灯光——蜡烛或者是煤油灯。
还没等我决定下一步做什么时,不知怎么见一辆没有开车灯的大型消防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转弯上了公路,向东朝着岛屿狭窄的骨架地段开去,那儿是早已荒废的军火库。
消防车底盘很高,容易超越路上排排倒地的树木,不久就消失在黑暗中。
我赤脚以最快的速度跑向消防站,拔出左轮手枪,从敞开的车库门口冲进去,我能辨认出车库里有三辆消防卡车。
在雨里待了这么久,这里的干燥让我顿时足足有10秒钟不适应,但很快恢复过来。
当我的双眼习惯黑暗的环境后,我看到车库后面有根消防枝,楼上宿舍里的灯光从天花板的洞隙里渗透下来。消防技的左边是宽阔的楼梯,我举着手枪踏在上面,楼板吱吱嘎嘎地响。我知道不会有危险,也猜到将要看到的一切。
楼梯上去就是消防宿舍。里面点着煤油灯。借着灯光,我看到两个消防队员倒在床位上,不用近前观看就知道已经死了,这使得被托宾杀死的人上升到七个。我们绝对不必用老一套方法来算这些账。
鞋和袜子都放在每张床位的旁边,我坐在一张凳子上穿上一双厚袜子和一双电镀了的橡皮靴,正好合脚。墙的一面放了些上锁的小橱柜,另一面则是挂着雨衣和汗衫的钩子。我并不迷信,尽可能多地穿上了其中一个死人的衣服。
消防站宿舍的后面是个和船上类似的小厨房,柜台上有盒巧克力坚果,我拿一颗尝了尝。
我走下楼梯来到消防站前面的东西向大路上,接着向东沿着消防车的印迹上到地势上升的铺设的公路。残枝断柳挡在路上,消防车刚刚从上面驶了过去。
又走了约半英里,即使在黑夜里,我也能回忆起上次乘坐史蒂文斯的观光车经过的路线。雨瓢泼直下,风又不断地将树枝刮断。我不时地能听到像是来福枪的劈啪声,使我的心抨抨直跳,但这声音其实是枝叉从树上啪地一下断落下来时和树干碰撞发出来的。
铺设好的公路上水流泪泪,沿路的排水渠已有污水四处漫溢,我逆流上山,在滑下来的泥团和掉下来的树枝中间穿行。这肯定比我公寓门前的烂泥地更糟。自然真是令人敬畏,有时简直是要命。
不管怎样,我对前方并不加注意,因为当我抬头看时消防车就停在前面不过十五英里距离。我突然停止脚步,抽出手枪,单膝跪下。雨中我看到一棵大树倒在地上堵住车子去路。
消防车占据了狭窄路道的大部,我从左边侧身挤过去,从污水沟里漫出来的水齐膝深。我走到司机一边的车门口朝里偷看一眼,驾驶室里没有人。
我想使驾驶失灵,但是驾驶室的门被锁死,发动机罩也从里面锁上了。真该死!我爬到高高的底盘下面,独出刀子。我对汽车机械懂得不多,会撕扯衣服的杰克对汽车修理并不怎么会。我只好割破几个管子,结果流出来的是水。我另外切断几根电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破坏了发动机。于是我从下面爬了出来,上了公路继续前进。
此时我来到军事堡垒的中部,到处是大块的混凝土、石头和砖砌的废墟,上面长满了藤蔓和灌木丛,看上去很像我曾经在康昆城外热带雨林中见过的玛雅遗迹。事实上,那时我正在度蜜月,可现在不是,哪个也算不上我的真正蜜月。
虽然能见到左右两边有狭路和混凝土建的斜坡及阶梯,我仍然坚持走大路。显然托宾可能从这些路径中的任一条进入军事据点!我意识到很可能已找不到他的踪迹,便停下脚步,在与路紧邻的混凝土墙边蹲下来。我正打算回转,这时又听到远处有响声。我一边继续倾听,一边努力平息自己的沉重呼吸。接着又听到尖锐、鸣鸣的叫声,终于听出这是警报声。声音从很远处传来,在风雨中很难听到。方向是西面,先是长而尖利的声音,跟着一声短的汽笛声,然后又是长的声音。显然是个警报,很可能是从主大楼的电子喇叭里传来的。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已能辨认空袭警报,现在肯定不是。这既不是火警,也不是消防车或者警车的警报,也不会是辐射泄露的警报声,这些我曾经在警察训练的电影听到过。这样,随着声音的逐渐消失,一半因为我并不真笨,我知道——尽管以前我从未听过这种警报——我听到的乃是生物病菌泄露的警报。主耶酥啊——
这时岛上的供电已经中断,主大楼附近的备用发动机一定业已熄灭,而阴电气流泵和电子空气过滤器都已停转。圣母玛丽亚——
一个用电池供电的大型警报器此刻正在什么地方发布着坏消息,岛上所有值勤人员必须穿上反生物病毒的装备,等着警报过去。我没有这种装备,见鬼,我甚至连内裤都没有……圣父在上,阿门。
因为我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并没有慌乱。这就像上学的时候,在一片空袭警报的哀号中,假想着苏联的导弹正在向弗奥拉鲁高地飞速奔来,我们要很快钻进防空洞。
嗯,也许事情并没有那么糟。风由南向北一阵劲吹……不对7其实,风暴正在向北部运动,而大风是逆时针方向的,这样可以想见大风会把西南角的中心实验室散发出的任何东西吹到岛的东边。“真该死。”
我蹲在雨中,思考着各次凶杀案的前前后后,想到风雨中九死一生的历程以及在所有致命的愚蠢、无聊的自负、贪婪和欺骗一起上场之后,残酷的死神闯了进来,开始清扫战场,“噗嗤,”就像这样。
我心里清楚,如果发动机突然坏掉,那么整个实验室里面的东西都会向外泄露。“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这事会发生!”可是为什么偏偏在今天?偏偏在我来这个白痴岛的第二天?
不管怎样,我决定拼命地往回跑,到海滩那找到贝思,上到捕鲸船上,再驾驶克里斯游艇掉头离开普拉姆岛,那是最好不过的。至少我们会有机会活下来,可以让死神替我照顾托宾。
另一个想法又闪过脑际,但并不太妙——要是贝思听出警报声,乘坐捕鲸船跑到克里斯游艇上,然后驾船离开了呢?我琢磨了一会儿,认定能在风暴中和我一块跳到小船上的这个女人决不会现在丢下我不顾。可是……瘟疫有着比波涛汹涌的大海更为可怕的地方。
当我下坡向消防车跑去时,得出一些结论:首先我已经跑开太远;其次我不想看到贝思的决定;再者我得找到并杀死托宾。还有一点,我无论怎样都是个死人。我突然之间羞愧于自己的惊慌失措,于是回头走向要塞,去碰碰运气。警报继续在呼啸。
接近路的顶坡时,我看到一柬光亮——其实是一束射线在我右边扫过地平线,一闪即逝。
我搜索了路四周,发现一条狭窄的砖路,通往植物园。看得出最近有人走过这里,我奋力穿过丛生的灌木和掉在地上的树枝,最终来到一处地势下沉的庭院。穿过周围混凝土墙上的铁门可以到达地下弹药库。从那可以看到四周群山环绕,山顶有混凝士浇铸的军事炮台。我意识到上次访问这里曾站在炮台上面俯视过这个院子。
我还是蹲在灌木丛中,从大面积的混凝土裂口处向里注视了半天,没有任何动静,也没见亮灯。
我拔出左轮手枪,小心靠近院子,然后沿着逆时针方向做圆周运动,始终背对着长满苔藓的混凝土墙。
我走到第一个双层大铁门,门是关着的,但从铰链可以看出门是向外开的,而且从前面的瓦砾碎石看得出最近门没开过。
我继续绕着院子转圈子,意识到如果有人从护墙上俯看这里,我便成了只极易打中的鸭子,一只死鸭子,甚至是一只煮熟了的。第二处铁门和第一个一样——老而生锈的铁门显然都有几十年没有打开了。
但第三面也就是庭院南面墙上的一个双重门微微半开,地上的碎石被开门时扫到了一边。我朝四英寸宽的开口向里看,可是什么也没有听到或看到。
我又把门向怀里拉开几英寸,铰链嘎嘎作响,真该死。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仔细听了听,只有风声雨声和远处尖利的警报声,正在告诉每个人不可想像的事已经发生。
我深吸一口气从门口溜了进去。
足足有一分钟时间我站着没有动,想摸清这是个什么地方。和消防站一样,在这里可以得到避雨的待遇,可也知道这将是受到的最后的待遇。
这个地方很潮湿,好似从未进过阳光。
我向左悄悄跨了两大步,碰到了墙,身体感觉到混凝士墙面的起伏。我向对面跨了四步又碰到墙壁。我设想自己在一个地道里面,就像第一次旅行时我们在这儿见到的可以通往罗斯威尔外侨区或者纳粹实验室的那条地道。
可我没有时间去纳粹实验室,也对外侨区不感兴趣,只需要决定托宾是否已跑到这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来取宝藏吗?还是已经发现我想引我人圈套呢?只要他在这儿,我对他于什么都无所谓。
前面看不到电筒光,如同在地下室里一片黑暗。肉眼不可能适应这种黑暗,所以如果托宾在这儿,他得打开电筒向我开枪。可如果他那样做,我便会向他的电筒光径直开枪,这种情况下不会有第二枪。
我穿着救生衣向前走,雨衣和橡皮靴咯吱作响。肩挎时髦的皮枪套,牛仔裤下面没穿内裤。皮带上插着一把制革短刀,脚上穿着死人的羊毛袜,就这样我在漆黑的沟道里尽量往高处走,以避免碎石、瓦砾之类的东西。我想到了老鼠、蝙蝠、甲虫和蛇,但又把这些念头赶出脑海。这些东西对我都不是问题,真正问题乃是后面紧跑而来的空气中的炭疽病菌和前面黑暗之中的那个神经病。
万福玛利亚……其实,我总是很虞诚信教的,只是没事时想到和谈得不多而已。我是说,当我躺在阴沟里流血快死时,并不是因为有危险才呼唤上帝的。只是那一时刻没有其它事可做,正是最合适祈祷的时候……圣母……
这时右脚突然踩上什么滑腻的东西,险些失去平衡。我赶紧蹲下身,在脚的周围摸了摸。接触到一块冷冰冰的金属块,想把它移开,却纹丝不动。顺手摸过去才发觉是根埋在混凝土地板下的铁轨。这才记起史蒂文斯介绍过岛上曾有过一条短距离铁轨,用来把弹药从港湾里的船上运到军事炮台。显然,这是条通向弹药仓库的铁道沟。
我继续前进,脚一直碰着铁轨。几分钟后,我感觉到铁轨转向右边,又接触到什么粗糙的东西。我跪下来又摸了摸,这里有个岔道,铁轨分开来一左一右。就在思考托宾和我同时向终点靠近时,我看到路上有把该死的叉子。我依旧跪在地上注视两个方向的黑暗深处,可什么也看不到,听不见。我猛然想到,如果托宾认为只有他一个人,他一定会打开电筒,至少应该大踏步重重地向前走。
因为看不到也听不见他,我做出一个了不起的推断,那就是托宾知道并非就他一人在这里。或许他只是在前面离我太远,也可能他根本不在这里……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祈祷吧……
我站起来沿着铁轨向右走去,地道里水滴声越来越大,但空气好多了。
几分钟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