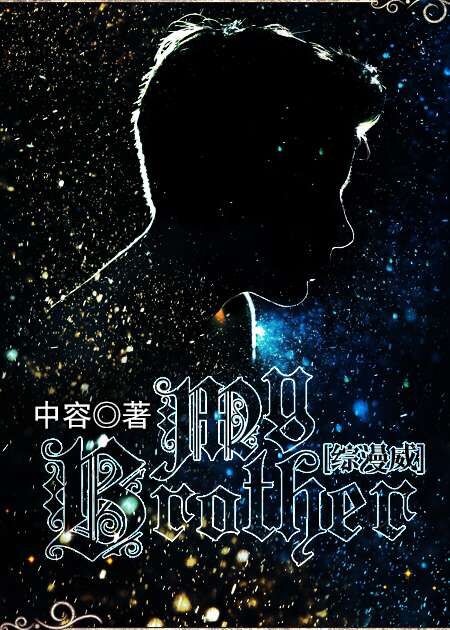听见 by战靖(听障攻vs双性受 美攻强受 互宠甜文)-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时候,台湾的工制还没实施周休二日,他从上班到开口请假这当下已有四个多月,几乎每个周日都自动自发来公司跟我一起加不打卡的没钱班,我扔什麽他就处理什麽,我若是大妈他就是三妈(注),也没听过他跟我喊累,说他吃不消,只是请个三天假去处理私事,确实不过份。
(注:大妈是妈祖林默娘,三妈是大妈的分灵修练得道的陈静。)
好。等红灯时,我朝转脸看我的范源进点点头,比了个ok的手势,又接著比:
要带南投的土产回来给我。
「好。」他又笑得眼弯唇翘,午後的阳光斜斜照进来,给他打上苹果光,衬得他格外好看。
第一次允他假的我,没想到我已然有些离他不得。不过三天,繁琐的小事就快把我惹毛成炸弹,少个他帮我接电话收文件,安排开会与应酬的时间,过滤上呈事务的轻重缓急,让我意识到他的重要性。
虽然我给范源进的薪水不算低,可还是掩不过我花一份工的钱,却让他干两人、甚至三人份工作量的事实。
他是总经理特别助理,也是总经理秘书,更是总经理司机兼翻译,还得出场帮我挡酒,替我说场面话,给我保续旧合约,争取新合约。
於是,周一他回来上班,跟我说早,我对他比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决定给你加薪。你想涨几成?
他愣了下,然後又笑了,我很喜欢他眼弯唇翘的模样,颇有几分可爱。
「我请假的时候,发生什麽事了?」他当我开他玩笑,回话还是谨守份际。
很多事,我都快被烦死了。我边比边说唇语,故做苦恼的望著他,然後,发生了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
不过才隔三天没见面,应该是看我看得很习惯,就差没有一见我就烦的大男人,竟然对著我脸红了?
作家的话:
补好了。。。。。。
第八回(听障攻VS双性受)
(八)
「咳、咳咳咳嗯,早会时间差不多了,我去看黄姊布置好了没。」
望著落荒而逃的背影,那抹迅速被范源进藏起的腼腆让我玩味许久。稍後坐在会议室里,我刻意将视线凝聚在他身上,看他故做不知,却是一身无法排遣的不自在气场,我心里开始隐有所感,却不确定。
学法四年,本科从业十一个月,我活得还不算长,可看过、听过、经手过的种种故事、型色八卦、各类案件,也让我生命的宽度不算窄了。
因为喜欢读杂书,热衷稗官野史胜过正史列传,所以我大学时期就知道魏晋南北朝曾出过一位男皇后,知道二战时期的纳粹战俘营怎麽对待性别倒错者,也看过猩猩群体里的雄性首领会鸡奸同性罗喽的行为研究。
所以,当时我归纳出的结论,是:同性之间的恋慕,不是近代才出现的现象,是人类本性里一种畸形的分化。大概,就跟我的耳疾一样,都是天性,都会遗传。
不过,知道归知道,推论归推论,无论二十一世纪後我曾多麽自豪我在大学时期就有这麽接近正确的同性恋观念,在我猜测范源进可能对我<心思不纯>的当下虽不至於觉得他龌龊,却是越想越觉不可思议,一方面一想到他若过来搂抱我,心理上便会生出难以接受的排斥感,一方面又想知道他为什麽会这样,会这样真的是天生的?
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未来的爱人拥有不逊於我的敏感直觉,因为他也算身障人士。这种不愿被人看轻、自矜自爱、自立自强、力保尊严的直觉在千千万万的身残志不残的斗士身上都能看得到,而他的强度,刚好也不输给我的。
於是,就在我开始留意不给他机会碰触我的同时,他也主动与我保持出比以往要更远的距离,不仅口气上全然公事化,变得很严肃都不笑,非不得已要引起我注意时他会拿文件在我眼前晃,少数几次走神叫不醒他不是请人来轻拍我,就是用纸张卷起来轻碰我的肩或手臂。
比方说,现在就是。
「对不起,总务处再送的下个月采买申请书修改好了,劳您再过目。」间接以文件夹的窄边搁上我前肘,把我的注意力从冥思里唤回来的男人垂下视线不看我,字条上跟他嘴上的沟通又以对不起当开头,从他休完假回来已经过了三个礼拜,每一天,每一次,一日复一日,一回又一回,皆是如此。
外出办事过马路,我听不见他的叫唤他索性也陪我在路旁枯站,任一个接一个的绿灯亮起又熄灭,也不再来拉我。
有一股很不舒服的情绪,在我心间迅速的累积成一种冲动,这份贴在我袖子上的文件夹成为冲垮堤防的最後一袭浪,不是最高,不是最强,却是最碍眼!
「你!」我摔开笔,用力拽住他的领带,迫他与我四目相对,以鼻尖相差鼻尖不出十五公分的距离:「想要,怎、样?」
他是第一次听见我说话,所以,嘴巴微张憋住气,愣愣望著我的反应显得有点傻,有些可笑,我却觉得很满意。
为什麽觉得很满意?发生那时不要问我,因为我也不知道。
後来他也曾调侃我,私下的,因为他知道我好面子,说我跟他会走到一起,根本是我去惹他,我主动诱惑他的。
我没有否认,他提一次我就吻他一回。有时兴致正高,我会直接将他就地正法,有时只是相视而笑,互拥一会,该干嘛还干嘛去。
这就是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劣根性,也是缘份吧。虽然没有多走多少冤枉路,可每每想起那时候的范源进,我便觉得愧疚。
「我没想要怎麽样。」被我拽住领带的男人咬著牙关低声说话,唇动得不明显,传进助听器的声音很模糊,我却将他说的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如果你觉得我不适任,我可以辞职,不用费心的与我保持距离。」
「」
「我以我的家人发誓,我对你,只有这份工作该有的想法,如有说谎,三日之内,横死街头,不得善终。」
作家的话:
老好人被乖僻少爷惹毛了
第九回(听障攻VS双性受)
(九)
这誓发得太重了,还把家人都捎带来背书,看得出范源进这阵子受我影响也不小,竟如此决绝的力持自己的清白。
可他越是费劲去撇清,我便莫名的越不能释怀,怒气被撩到少有的高度,几近失控的边缘!
还拽住他的领带,我想看他的脸,以另一手的食指去勾他的下颔,他头一偏,上身向後微仰开来,我只来得及感受到他脸颊下缘的触感。
虽是一擦而过,接触的时间连半秒都不满,不太扎手的细软胡根磨过我手指的瞬间却产生了微弱的电流,直把通向心脏的一串神经元刺激得突突直跳,好似细胞核全长出了小心脏,让我骇得一僵,心序立乱。
「不管你信不信,你的问题,我回答了。」他将脸转回来,抬起眼与我互视:「请你尊重我,放开,让我起来。」
隐忍的屈辱、怒气,还有另一些我解读不出的情绪在他眼里纠结翻腾,我脑里的理智与逻辑好似真被电得短路了,在他试图拉走领带的时候只一昧地命令手要扯紧,不可松开,眼睛更是眨也不眨的紧迫盯人,还能运作的少数脑细胞只告诉我:
这个人的眼睛,长得不算特别的好看,可他的眼神在每个流转之间,都在说话。
范源进瞳仁的颜色,似乎较平常人都要浅一些,很像母亲曾给我冲的爱心饮品。
我高中那时没有住校,校区跟家里相距将近三十公里,冬天需要上学的大清早出门搭车的时候,天总是还没亮。母亲几乎日日披衣而起,把摸黑出门的我拦在门前,用提袋装上一颗馒头夹蛋,配一杯阿华田,要我不准剩回来
见我板著脸瞪著他,手怎麽也不放,范源进再一次展现他的神力,以三根手指头叩在领带活结上防领圈缩小勒伤自己,腰上使力将上身挺直,不过是两脚各往後退了一小步,就将我拉离椅面紧靠桌面的拖行了半公尺之多!
我使用的办公桌也是父亲当初订制的,一体成型,杉木的材质十分地沉,宽大的桌面气派得像单人床,我骨头重、身高算高,看起来不胖不壮却有七、八十公斤,可范源进单靠套在他脖子上的一根领带就把这两者加起来可能超过一百五十公斤的死物活物,轻松愉快的都拖离了原来的位置。
「放、手!!」范源进的脸虽没关圣帝君的红,但凭较方才更加强硬的语气与咬字,也看得出他是真的动气了。
不可以辞职,我的理智总算醒了几分,站起来松开他的领带後摇了摇头又摆摆手,用唇语说了辞职,再做拿笔写字状说合约,提醒他试用期结束的隔天就签给我两年卖身契的事实,最後说了二十,那是他两年未到就辞职的违约金,是以他已领薪资的总额下去算的,二十倍。
范源进应该看明白我的意思,暂时也不回我话,就是还回瞪我,胸口不停迅速起伏。
我知道了,对不起,是我误会你,请你不要生我的气。
我比得很快,重复比了两遍,脸上尽量摆出诚恳的表情,那是我在律师事务所学习的期间,对著镜子练上好一阵子才练成的职业面具之一。
虽然还是没回应,见他呼吸渐趋和缓,我知道他多少被我安抚下来了。
「对--不、起。」主动握手求和,我尚且有点顾忌,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还是选择自曝其短,认命地再开金口,以示诚意:「请,原谅,我。」
共事这麽久,他也将我性子摸得七七八八,猜得到我不愿被人笑话,所以才不出声讲话。
「这次,我可以不计较,不要再有下次了。」被上司暴力相对,他的喉咙跟自尊都受伤了,说话的声音哑哑的,涩涩的。
这是我第一次扯他领带,也是最恶意的一次,我曾以为他这麽轻易原谅了我又是因为他天生的好脾气,後来才知道还有其他因素。
他真的是个灵魂会发光的大善人。能得佳人如他与我相伴馀生,我很幸运;能得家人如他关照生活起居,我很幸福。
就因我一时冲动,管不住脾气,范源进对我的态度从寒流过境的亚热带冬季,直接进入永不融雪的冰河期。
面对我的时候,他也成了聋哑人士,文字上的往返成了我跟他唯一能沟通的渠道。灰色的思惟迅速地统治了我,这样的状态让我罹患职业倦怠,常常觉得活著只为了偿清亲恩,我这一生其实贫乏至极,其实生无可恋。
其实,我不过是陷入情网,而不自知;不过是渴望范源进再对我撤除心防,眼弯唇翘的笑;在过马路的时候,愿意再拉著我的手过;在我带著撒娇意味对他抱怨的时候,他能情不自禁的再对著我,露出情难自制的神情。
这些,当时那个自以为是的我,没察觉自己喜欢上范源进的我,全不自知。
於是,作茧自缚的把自己困在他是不是同性恋,是不是该与他保持距离这份上,一困又是将近两个月。
直到攒够了盈利,足以填补贷款资金不足的缺口,停止生产的那一半厂区也搬空机台空出来等著我去日本亲自将机台买回来的时机来临,我与范源进的破冰之旅,才见曙光。
作家的话:
第十回(听障攻VS双性受)
(十)
自动化碾米设备的日商有驻台服务处,没有驻台厂房,想看机台实际生产的情形与产能,会有业务专员领著去已经自动化的其他同业厂里观摩。要是交涉得宜,同业够大方,也会有让准客户摸几把面版、短暂操作一番的机会。
范源进开车载我四处趴趴走细细看,四、五家厂商带著我们台湾头跑到台湾尾的看过不下十几种机型,就这样考虑经费考虑占地大小考虑最高产能考虑耗电等等云云的,自己一再推翻自己不下十馀次,我终於选定两家厂商的次新型机台做谈价砍价上的PK战。
彰化厂厂区挺大的,半条生产线就能放六、七台,选择次新型,买十台的钱拿去买最新型只能买八台,产能上十台次的不比八台最新型少。
再说这两型次新的,一个十一(步骤)合一(台),一个十合一,看似差了一个步骤,其实效能完全相同,毕竟是同一时期的设计,两家的技术也在伯仲之间,差得并不远。
十一合一那家牌子名气没十合一的大,单台售价上稍微便宜个零头,总价上业务则暗示有5%的弹性空间。当时大概是因为我心里实在太烦,又想折腾人,结果谈著谈著都快谈拢了,回头我又写字条要范源进去安排一趟关西商务之旅,决定去十合一那家的日本总厂再仔细的<看看>。
除了回过来一句:请问日期?人数?他再没有多馀的表示。
连我回他两个人,就他跟我去,他也没有推举他人的意思。
隔天,那家十一合一的业务却又上门了,明明说定了让我考虑一周的。
我在范源进给业务上过茶坐下来帮我做沟通的时候几乎全程都定定地望著他,他一开始只用眼尾馀光扫过我,多数时候视线都在业务身上,後来业务也以眼神请他来求我,他这才避无可避的与我四目相对。
关东关西之间交通很方便,可以两家都去看。我只用手语,唇皮不掀,我想让十一合一的业务觉得我难以捉模,不好搞定。
越难缠的客户越能得到好的服务品质,爱吵会闹的孩子总是有糖吃,这是息事宁人的人性天性,更是不争的事实。
送笑容快要掩不住无奈的业务离开办公室时,我看见范源进深吸一口气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