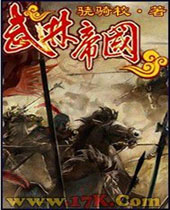武林画卷-第4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标成一线,唐表根本没有躲闪这个选择。但是棋子穿过唐表的身体就变了轨迹,是“随杏所欲”这个法门起的作用?这小子被杀伤的时候还有余力搞这手段,保护金寒窗?倘若抛去金寒窗这个因素,唐表是不是还会中子?莫非适才那一株“七宝树”的破绽是诱自己出来的饵?
看着那个男人的背影,一系列的想法在星罗棋布的脑子里闪过,但是这个过程已经不重要了。
他知结果已定。
于是,星罗棋布倏然踏前一步。他与唐表的距离并不算近,一个在院心,一个在院角,金寒窗则在小院的另一角。
以对峙双方的层级来说,这点距离根本影响不到他俩暗器的杀伤控制,所以重要的不是当前距离,而是方向。
星罗棋布这一步偏向踏出,向着金寒窗。方向代表着意图。点燃战火,这一踏就够了。他要逼迫唐表先出手,而唐表一出手势必要先扳转背身这个不利的局面,星罗棋布不会给唐表这个机会,这个先机他站定了。
毫无预兆,唐表竟冲天而起。
没有转身,没有向前拉开距离。
而是向天。
天意高不可问,唐表一跃问天,一跃破了局,又立了局,这一步棋没有落在星罗棋布估算的棋盘之上,而是落在了虚空。
星罗棋布手托的棋盘骤然旋转了起来,棋盘旋成混沌模糊的光影,由方正变弧圆,看去如同一颗暗青色的飞旋大星。棋盘上的黑白余子飞射而出,棋子与天上的金枝银叶或穿掠错过,或与其对撞成碎片。“杏在天”凌空而下金枝亦极其强悍,金光即使撞成了残片,也粉身碎骨霸道的攻了下来。
半空中溅起了无数的小小星芒,夜风过处,更吹落星如雨。强劲的星雨扫射着地面上的鬼魅身形,星罗棋布于荒草中游走,似乎总能在最后时刻跨出一步,避开天上的暗器,而且凡是被他那飞旋棋盘接住了的暗器都反射了回去。
星罗棋布走出一个迅疾的之字路线,身形剧停,两枚“杏叶”当即切进他的后背,而他依旧纹丝不动,占住了唐表的落地点。
飞得再高的鸟也有歇息的时候。星罗棋布就站在了鸟儿要栖息的树枝上。
唐表的双脚挂着一勾弯月,飞返而来,一掌印下。
这一掌轻柔飘忽,掌含微光,像是暗夜中的天启。
星罗棋布一见那光,立即单手托举棋盘,掠起迎上了唐表。
光华一掌正印在那青色棋盘之上,飞旋如大星般的棋盘瞬间静止了下来,双方对撼的一点泵射出无数厉芒,宛如一轮月亮湮碎在了星辰之中。
这一瞬间,两人只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但无法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做到。因为两人的出手均快到让对方无法精确地去判断。
人影交错。
光辉散尽。
金寒窗看见唐表一落地,双脚就如暗器般扎住了地面,笔直立着。那边的星罗棋布冲出几步也停了下来。
星罗棋布左手托着的一局残棋没了棋子,唯有右手二指挟着一枚黑子。他看着黑子上滴淌的鲜血,面上没有什么表情,竟似感知不到自身亦有十数道伤口在流血,那每一处伤口都嵌着一枚独特的枝叶。
金寒窗见两人都不怎么动,他也不敢动。心脏在金寒窗的胸腔猛烈地锤击,他看不清两人具体的交手过程,但他隐约觉得经了适才那一博,场中似乎分出了胜负,甚至更可能断了生死!
只是现在场中两人都不动,背对而立,却不知是谁胜谁负,谁生谁死。
金寒窗依唐表之言退在墙角。因为唐棠算是唐表半个授业老师,他从小就与唐表熟稔,他深知即使在人才济济的唐门,唐表也是天才人物。唐表十六岁练成“七宝树”,十八岁习得“九魂花”,二十岁“九魂花”即破了七瓣之数,这种天资比之当年唐棠亦不遑多让,看多了唐表的锋芒,金寒窗对其的信心可谓根深蒂固。但此时,他感觉唐表伶仃寂寞的侧影有些单薄,看着那高傲的头颅慢慢低垂,看着那愤怒的拳头逐渐舒缓,金寒窗心中生出了不详的预感。
动一下啊,唐表!
场中寂静,听不到心声的澎湃。金寒窗的企盼只唤来了一阵夜风,那风越墙而来,拂动唐表的衣袖,宽短衣袖边缘起了花样的纹澜,像是第一次的盛放也是最后一次的凋谢,笔挺的人突然倒下。
这一眼情景异常突然却又清晰缓慢,将金寒窗心中的不祥演绎的如此决绝。唐表的倒下如同一记刀斩,毫不留情割裂了金寒窗。少年刹那一分为二,一个是嘶吼的疯子,一个是干巴无言的泥塑。金寒窗不知道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的是那个自己,抑或这个世界都不是真实的?
星罗棋布蓦然转身,阴鸷的盯着金寒窗,哑声说道:“可惜看不到‘花’,不过没关系,只要我抓了你,不愁从唐棠那儿得不到。”星罗棋布的语音有着兴奋,亦有着失望。他费尽心机伏杀唐表,结果只见树木不见花朵,与垂死的唐表一搏,竟也被未施展开的“七宝树”伤的不轻,唐门的四大秘就像四座大山,牢牢地把他压死。他知道若不破了四大秘,他永远难在唐门面前真正翻身。
他眼光扫过像是得了失心疯一样的金寒窗,如看囊中之物,然后向倒下的唐表走去。星罗棋布非常谨慎,他偷袭的第一击凝聚了全身功力,理应在那时就断了唐表的生机,可是这个男人竟然还能在最后时刻勉强发动“七宝树”,他必须查验一下这个大敌是不是真的倒下了。
金寒窗散开的瞳孔逐渐聚拢,仇恨的怒火能溶透身躯,唐表事先交代的话语被他抛到一边,他吼叫着不惜一切代价扑向星罗棋布,忽然间一枚黑色棋子如同从黑暗中分离出来一般,无视距离,骤然间打在他的气海。金寒窗腹部淤痛,站立不能,双膝软跪了下去。
离得那唐表越近,星罗棋布就愈发明确这人的生命已无。强敌殁亡,万事尽在掌握,胜利的感觉自然而生。唐表倒下的地方不远,还卧着一名女子。星罗棋布淡褐色眼珠微微转动,捕捉着那女子虚弱的气息,他盘算着是否要将那女子也杀了。
容曼芙是相爷府的人,他这次来暮望的第一联系人是容曼芙,有了相府这层关系网,星罗棋布根本不屑与栾照打交道,暮望计划已经变动,栾照由棋子变成弃子,没有什么价值。于是,他玉荷楼上坐看同心街一刺,冷看“一家亲”覆灭,并亲手断了李纯一江记绸缎铺这条后路,又顺道用复梦派与恨愁帮试探了金寒窗的底细。“一家亲”之事,星罗棋布做得很绝,这其中有大罗教与“一家亲”不和的缘故,另外还有复杂因素。李纯一越来越被西北王倚重,固然因为武功高绝,出手无情,但是李纯一与西北王的血缘关系才是根本。李纯一属岑玉柴民间遗子,此乃西北的一件私密,明眼人猜得出来,可大多讳言此事,岑玉柴一直暗中培养着这个私生子,近年来尤其留意。而与“一家亲”争宠相抵的大罗教则结好恭王府的大世子岑文海。
嫡庶之争,古来难免。
岑文海对这个私生子弟弟是轻蔑其出身,嫉妒其才能,总觉受到威胁,他借机定要李纯一死在暮望,即算坏了青州之事也在所不惜,岑玉柴要的是天下,而他岑文海只要凉州一隅就足够了。
这些秘事,容曼芙知晓一二,为了取得这女子的信任,星罗棋布也不得不给予一些信息,他更知道以这个女子的聪慧,有了一二便能猜得到八九,只有连容曼芙也杀了,青州之事才算干净利落。西北王与相府一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也非就是一条船上的渡客,当今天下,应各行其道,今夜这么乱,正是做事的好机会,随便栽赃给那个势力都说得通。
譬如说:那两个杀手。
星罗棋布嗜杀成性,念想间心意已决,就准备给地上的两人各补上一击,不留下一个活口。
那两个人卧在荒草中,寂寂长眠。时节近夏。青州的天候还没有完全转暖,荒草中的小野花大多还打着蓓蕾,但是总有些提早盛开的,这些耐不住寂寞的花儿开的娇羞了些,姿态说不上端庄也不够上狂野。
这里却还有着例外。
早开的花中有一朵最美。
它开在风中,无根无叶,肃穆而飞,小花冉冉浮空犹如魂魄,自由自在的四片花瓣并不完整,但简洁之美压过了残缺的遗憾,它寂静的从唐表衣袖起航,径向场中唯一行动的星罗棋布翱翔而去。
风在吹,草在动,月倾斜,星在天。
如果说动起来的事物像是吸引它的磁铁,那么为何它却只向人去?莫非因为一切变化皆是因心动?
星罗棋布的表情冻结在惊悚的一刻,当他感应到那“花”时,场面已然不可控!也不见膝盖弯曲,星罗棋布就如惊风般狂掠退走。他电般倒掠,那花却似来自幽冥一般,以更加不可思议的速度追上了星罗棋布。
小花燃烧一般的追击,狂欢一样的怒放。
这怒放如最残暴的黎明挟着千万缕曙光杀进黑暗,开到那里就摧毁切割到那里,无止尽的追袭引动它的身影。星罗棋布整个人蜷缩在棋盘之后,发出破了音的惨嘶,他像是一只无头苍蝇于院墙生生地撞出一个大洞,逃了出去。那一声惨嘶拉长拉远,藏着万分的恐惧与怨念,如同来自幽深炼狱。
院内人静,漫漫荒草倒伏了许多,尤其是破洞院墙前的区域,那里像被巨大蝗虫群啃食过一般,泥土倒翻,寸草未留。院中依旧有大片草植在风中摇曳,仿佛并不在乎谁在这里撒过野,荒草间光芒闪烁,金枝银叶几乎遍插院心。
跪立的金寒窗伸手极力探向唐表的方向,终于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他的下肢淤麻无力,就靠着两手趴泥抓草的爬行。荒草涩涩的拽在手中,像是扭成一团写满恨意的乱麻,好比一把扎进心头的芒刺,金寒窗眼中的天是红色的,仿佛天际的星星一齐滴着鲜血。唐表的侧面已在近前,泪水从金寒窗易容的老眼中沥沥淌下,那触手可及的血色俊颜面朝着暮望的南方,没有了神采,但双目透过荒草野花,穿越重楼层阁,似乎无法忘却这有情世间。
小院的柴屋中无声无息出现了两个男子,两人从地道钻出,显得有些狼狈,其中的魁梧汉子望见了金寒窗,就要上前,旁边持着短剑的男子却探手挡了他一下,环扫四周环境,隐含伤悲道:“高兄,让他放肆的哭一场吧。”
暮望城外不远有着一片杨树林,林内停着不少马匹车辆,停留在林内过夜的都是些商旅,暮望封城事出突然,这些商旅本是赶着日落时分抵达,他们平常与门官交好,晚个几刻也能进城,不想今遭却被声词严厉的堵在门外。
夜已深了,林内还留着几点残余灯火。有些人还未安睡,正于树林旁边商议着什么,短短几言,卖方就痛快的递上银子,高兴的牵出一辆破旧马车,购得马车的两个少年人扶着一个受伤女子上了车,然后一言不发的扬鞭而去。
马车慢悠悠的起了速度,车头少年仔细的控制着缰绳,生怕颠簸了车内的女子。车厢的后帘被女子卷起,女子伤势沉疴,做完这件事就斜靠着垫子,匀长的喘息。她痴痴望着北方,不一会儿,那片树林远了,灯火远了,暮望也远了,不知怎地,伊像是伤体难敌夜凉风重,杏目轻阖,落下了几滴泪珠,泪珠晶莹剔透,如那官道衰兰上凝结的夜露一般。
卷三西北望
第三二章鹰眼峡(上)
龙门关东接雁岭,西临玉虚山,雄踞甘凉两州之界,号称西北第一大关。
西离此关,便是塞外凉州。
初出塞外,迎接旅客的是无边戈壁荒漠,而非那传说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奇美景致。这里常年风沙蔽日,晨昏日午间寒暑交替,熬人极苦,然而一旦挨过这片四百余里死亡地带,富庶的塞外江南跃然眼前。这片大好平原依托着从天脉大雪山蜿蜒流淌而下的清冽香河,得天独厚,香河冲击出肥沃的土壤,携着孕育生命的气息,它的九曲回肠亦载满了历代中原王朝拓边的荣光。纵死犹闻侠骨香,马革何曾裹尸还,自两百年前的龙门大捷之后,北漠部落的骁骑退回了远方的大草原,中央王朝新辟的这片疆土就以凉州为名,历经风霜与铁血直至今日。
凉州有七大城,两大关,十二连环屯军营,在此之上还有一个王。
藩王第一的西北王。
本朝虽册封了几个外姓王,但都是只封城不裂疆,这些藩王仅能作用于一城而已,对中央的集权威胁并不大。中原皇下十五州,其中的燕州、凉州是抵御北漠的两道重要屏障,两州卫疆捍边,享有些许不一样的特权,恭王岑玉柴占据着凉州中心大城平朔城,实力雄强影响着整个凉州局势。西北王有着保荐其他六城城主的不成文惯例,执行起来几乎与其亲手选派无异,并且大战时期可以便宜行事,调动整个凉州的军马,岑玉柴实际上将这塞外宝地都纳入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能够做到独霸凉州,西北王的确有不可替代的功勋。凉州的北边疆界原先一直和北漠的势力范围重合,双方缠战不休,西北王利用北漠内争之机突进三百里,占据了墨梦山、九烟峡谷、古海等天险,连修十二连环屯军营,一举定边。七大城中的襄城、云野城就是分别坐落于墨梦山下和古海一畔,两城新建不过十年,当初筑城、迁民所消耗的巨资有七成出自平朔城,固然这两座新城的财政大权被平朔城方面顺手把持,但是两座边城对凉州的繁荣起着巨大贡献,愈见成为凉州的商贸集中地。岑玉柴曾说,凉州的一切是孤奠定的,他有这个资格,而凉州的民心亦趋附之。
西北的这片天空属于西北王。
黄沙扫过这片寸草难生的戈壁,掠向远处隐约的山峰。滚烫的沙砾随风抽打着偶尔出现的行者与商旅,教人压低了身躯几乎无法抬头。
一列走镖的队伍正艰难的行进在荒野之中。放眼望去,十七名镖师骑手护着五辆马车,外加六十六名趟子手,没有一个无用之人,这阵仗已然不小,大镖局倾巢全出也不过如此了。队伍只插了一面镖旗,插在队伍中间的马车厢旁。这一杆黑旗被风沙刮得猎猎作响,上面绣着四个金字“远威威远”。
赶车的马夫用布条缠着头脸,遮挡风沙,露出两只略显疲劳但仍专注精炯的眼睛。这一趟镖自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