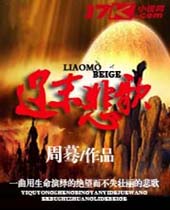辽末悲歌-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摹0Γ豢商驹劾铣捎姓馍仙舷孪拢侠仙偕僖晃炎拥募胰送侠郏蝗灰菜媪肆轿恍值芤豢槎チ耍癫豢煸铡!�
李长风眼中一阵酸胀,左边伤腿一软,便要单膝跪下去。
老成赶紧扶住,不住声的嘱咐少年仆从道:
“你务必要把这两位先生送到地头,安排的妥当再回来一—”
走了通宵也未曾吭声的仆儿连连点着头,仍无言语,也不知是天生木讷,还真是个哑子。两人敬谢了半响,老成连声说不碍事的,只催着赶紧上路,这一片是金辽接壤的所在,不定哪会儿就有兵士骑马胡乱窜上一通,说不准随时都有可能生出什么事体来。
李长风瘸瘸拐拐的走出一段路,回过头来看见成老大仍站在那里,眺望着向这边摇手。想着自己从平洲而出,一直觅了小路,夜行昼伏的,及至口粮断了,落得两日三夜都不曾有粮果腹,这才冒了大险,投奔这个在途中听说的成大哥而来,才闲话了几句,就被他看出了饥寒交迫的底子,立马让请到了后堂,先饱饱的吃了一顿热粥,又备下客房被褥,美美的睡了一场,连下两日来大碗斟酒,大块吃肉,虽不是什么丰希佳肴,但足见了殷实诚恳。到了前一日黄昏,见二人急于赶路,便又亲自来送一一李长风深深的庆幸自己自己履历劫难之躯,在最是困难的时候,居然无意中结识了这么一位慷慨仗义的奇男子。史传孟尝君疏财好义,广邀天下贤士,门客三千而不论出身贵贱,似成大哥如此作为也丝毫不遑多让。只可惜,竟到了分手之时,才通下了姓名。虽然是迫于形势,但也很显得自家的小气。…
“长风”王毅唤了一声发痴的李长风“我们快些走吧。”
李长风抬头见那仆儿已闷着头行出了老远,忙忙跛起腿与王毅赶着向前去。
由于连年里金、宋、辽三朝间不停掠战,各国都不曾常在这里站住了脚跟,走马灯似的换着统治,使人民苦到难以聊生,一路上不但少见行人过客,就是山农村夫也没见几个,李长风心中感慨万千。
“前些年随父亲做些买卖,也时常经过这里,道上从来都是熙熙攘攘的很是热闹,曾几何时,竟萧条成了这般样了。”
王毅点点头,他常年在这一带游走,感触更深。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屠苏一一曹松的这首诗尽道了战争之苦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天下最最苦的就是老百姓了。
王毅苦笑,“咱们现在更苦,已是无家可归了哦。”
两人一路的磋叹,心事重重地随在那小仆后面前行。李长风还好,虽然受了伤,但有心中存的这口意气,虽苦尤盛,拿“天将降大任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一一”;的一套道理激励自己,可王毅却不同,这一注下得有点儿大,千辛万苦不说,每日还提心吊胆,有心半途而废,可又不舍得搭进去这许多本钱白白瞎了。只好坚持,心中暗做打算,待把李长风送到地头儿,自己就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依旧做回老本行,静待这骰子的点数摇到最大,自己才来收本取利。
又走了有二十几里,有一标人马沿途而来,将他们拦了下来,李长风望向那十几个军士都是圆领窄袖的短襦着装,额头脑后留了三季长发,飘荡荡的分明就是大辽的打扮,心头不觉大热,招呼着迎上前去,伤了的左腿,此时也感觉不像方才一样太疼了。
把来意述了一个大概,领兵的将佐打量着二人又详细的诘问一番,才拱手道:
“某是平洲国事帐下步军都尉赵勤,二位即是历险而来的义士,就请随我一起进关,见过我家将军,在做计较。’’
当下叫过兵士匀出两匹战马,大家同乘着,一路进了神山县,街道上也并无太多的闲人,想是这四面的战事把这一城的百姓也惊住了,都各自的躲在家里不肯出门。
到底是马比人快,只一时便到了县衙,李长风见过了那位腮鬆如戟,面目熏黑,犹如张翼德转世的关东将军,想起这些日子以来的苦难艰辛,心中不由得一酸,泪水险些不争气的落下来。
一番短暂地介绍寒暄过后,关将军招呼手下士兵排摆桌凳,让受着伤的李长风坐下稍息,“早听闻平州有一干不服金贼管束的勇士昂然起义,两位老弟能亲临其会,够豪气。”关将军待扈从上罢茶盏,端起来抿了一抿“可惜我们知道的有些晚了,没能及时赶过去接应一二”
“只恨谋事不密,这干人里出了叛徒,把我们起义的消息泄露给了金国的驻府兵一一”李长风仇恨里带着些悲切,“除了我二人侥幸逃了出来,其他的都就义了…”
“就是死,也不能服了他娘的金狗管制!”关东大声道“来人,准备酒菜,我要与两位义士洗尘压惊。”
军中的伙食材料充分,兵卒们的手头倒也利落,不一会儿功夫,杯盘碗著就排布了上来,关将军两手分挽了李长风和王毅共进到桌案之前,随手便将几只如百姓家寻常惯用的小酒杯子划拉到桌角边,高声笑骂:
“用这么个窄底薄沿的鸟杯岂能喝得痛快,快换大碗来一—”
正文 第十二节
更新时间:12…11 4:04:04 本章字数:4006
顺墙一溜儿加摆着几张檀木的太师椅,便显得有些局促了,椅子上坐着的大多是文官服饰,间或有两三个武官,甲胄半解,露出了里面新旧不一的衬袍,大家心思不一,都忽闪着眼睛望向堂中间端坐着的大难未死的韩可孤。
看着大家都在等着自己开口,微微咳了一声,韩可孤刚要讲话,忽听见外面马蹄“得得”,一会儿又没了动静,只有马銮铃偶尔“铃铃”的响上几声,像是到了府前停了下来。
大家都把头拧向了堂门,韩可孤眼光也注视向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起,萧驴子带了一个满身风尘的汉子进来,那汉子看向室内众人,也不搭话,只双手四下里一拱,便越过去,径直走到主位的韩大人面前,轻声说了什么。
韩可孤面色一肃,点了点头,向众人道:
“请众位稍待片刻,可孤去去就来”,便带了那汉子一同出门转向后衙。
一众人面面相视,一时间都不知所谓,韩大人本来是召集大家来此议事的,看刚刚韩大人闻了来人言后的表情,想来又出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了。大家窃窃的私语起来。
现任平洲府同事李民,看到萧驴子从内室中退出来,便迎了上去,萧驴子知道这位李大人与自家老爷关系匪浅,平日里最是倚重,便来到身边悄悄的贴近身边说:
“刚从上京快马过来的…”
李民一愣,这么匆忙的从上京赶过来,神色又不对,恐怕…,心中隐隐生出一丝不祥。
这时,庭中众人正把话头扯到日前韩可孤落崖不死的事情上,七嘴八舌的议论,都道是神迹显现,很是感叹。
“想一想,几百米高的大崖头,栽下去竟不死,如要说没有神仙护佑谁能又给我们解释是什么原因?”
“而且,落地的旁边就是一座土地小庙,这不明眼就是土地爷救了大人的嘛!”
“那个地方常年不见人迹,哪那么巧那天就有几个避难的躲了进去?”
“天佑,就是天佑,别的都不用说了。”
大家哄哄的众说纷纭。
李民手抚着那几根生的稀稀拉拉的胡须听了一阵,见众人的声音略不杂乱了,才轻咳一声,笑了笑。
“众位说得固然神奇,可更神奇的还在后面,不知有没有人听过?”
这胃口吊得可够高的。人本来就对不可知的事情充满着强烈的欲知情绪,听了这句话,果然动容,纷纷请求李大人快给大家讲来听听。
李民望了望一直守在房门前的萧驴子,拉了拉嗓子,缓过声调说:
“这第一等神奇,大家该问一问韩大人的这位长随,他是如何受了可孤大人的差遣,身怀刺史大印,从北安府单骑准备赴上京交印,却偏偏鬼使神差的绕到了骆驼山下,主仆二人得以相逢的。”
这一段,大家果然是未曾道听途说的,便起着哄让萧驴子把一番经历叙说叙说。
这简直就是在为难天生木讷的萧驴子,他把那张铁青的脸涨得紫黑,前言不搭后语的讲了一通,最后更加手舞足蹈的比划,也没让众人听出个所以然来。
大家伙儿看到他急的出汗,倒觉得可爱,李民“呵呵”一声接过了话头。
“驴儿勇力卓绝,天生便有神力,只是说话上确实是勉强不来的,各位就别为难他了,还是让学生代叙吧!”
李民不紧不慢的讲起萧驴子的这番经历,述说的条理分明,有声有色,颇有些坊间茶社说书人的手段,把在座诸人的心吊得高高的,连当事人的萧驴子都听得入了神,随着李民这一出一段的叙述,时而眉飞,时而色舞,紧急处竟然拍起了桌子。从心里对李民的口才佩服起来,就这把死人都能说活过来的本事,就难怪自家老爷这么器重他了。
那日韩可孤自锅撑子山的崖头一跃而下,飘忽间巧无再巧的就刮擦到了那几株突兀而出的的老松,他在死心乍起之时,新袍换了旧朝服,衣宽布厚,被松枝树杈不断地刮蹭,便起了些缓冲的作用,之后更把袍衣上的纽襻撕扯开裂,袍襟四张兜起了风来,使下降的速度更缓了许多,而跌落的沟底处又因为少有人际,常年落松荒草早天然铺成了一层绵软的厚垫子,所以韩可孤从上面落下去,身躯竟并不曾受到大碍,只是头晕晕的昏迷了过去,而当时沟中恰好又有几个附近村庄的的百姓躲祸正藏在里面,认得是救苦救难的韩大人,便群拥而上救了下来,出山时不敢走上山官道,便出骆驼山奔西京而走,至于那个失足跌落的高军的兵士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被一身的铁甲缠着,重量自然要大的许多,垂直落下去撞到突出的石头上,便左抛右撞的来回翻个儿,大头儿着了地,只好在劫难逃了。萧驴子自府衙骑马而出一路向东奔驰,刚过了会仙石远远就见前面蜂拥着一排大帐,,营帐前旗帜高悬,也认不得上面写的什么,想来也是高永昌的队伍,没能全数进到城中,就在山上安下的营帐。有大人交代的重任在身,萧驴子自忖也没有打杀群狼的手段,无奈之下,只好乘着还没被发现便拨转了马头向回转过,觅了向东北方向的山野小道绕道而行。这样的一来一回便耽误了好些时间,又在这山村的小径中东绕西绕的来回觅径穿行,又要观察着也不知潜踪哪里的高军斥候,还幸亏这些年随大人来到北安后,无事时常自己上山打些野味才不至于迷了方向。
急得满头大汗之时,终于进了官道,远远就看见几个人鬼鬼祟祟的从骆驼山的沟子里爬出来向这边张望,还以为是高军的斥候发现了自己,便拍马直冲上去准备杀人灭口,却不料里面裹着自家大人。此时,行走上已经没有大碍了,只是袍服破烂,脸上手上到处是划破的血口子,很是狼狈,萧驴子一见大惊,不觉得泪流了下来。
主仆二人见面犹如隔世重逢,心中自然感慨良多,几个陪过来的百姓也是唏嘘不已,倒也知道此时再随韩大人而行就是累赘了,便把韩大人交付给萧驴子服侍,大家分散逃命去了。在那种情况下救下了韩大人可是让人非常长脸的事情,几个逃命之人自然要到处大肆喧耀,于是韩可孤大人大难不死的这条消息不日便传播了开来。俗话说“三人成虎”尤其是这种让人好奇的消息一传开来,添油加醋的人就多了,百人传百耳越传越悬。于是,便演绎成了韩可孤跃崖头而不死是因为有仙人扶拥缓缓而落,如踏步走下台阶一样,不疾不徐,自然不会摔伤摔死。更有好事人说那几个救起他的人曾看到土地爷显灵,自沟中小庙腾起一道红光将韩可孤轻轻托住而缓缓落下…总之,各种传说层出不尽,总之,都与怪力乱神好人好报相关。
这些奇谈怪论传到了韩可孤耳中,让他不禁发笑,自家的事自家清楚,哪来的那么玄乎,李民却深以为然,另生出一番见解。“大人,可还记得《书林记事》中东晋王献之书艺神授的故事?”
东晋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均是书法大家,史称“二王”,但当时羲之己是声名远播,尽善尽美,其维王逸少平察详古今,研精隶书。大家对其子献之的作品却多有贬义,然不过多时,民间便出传闻“献之年二十四时,隐于林下,遇一巨鸟人,左手持纸,右手执笔,挥毫书就五百七十九字相赠献之,献之如获至宝,每日照此临摹,不得一周所书,便于赠书,仿佛尽得神韵。于是神仙授艺的故事便传播开来。坊间“胜父论”多出,评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拟笑其布施媚如明珠漓陆,笔迹流铎宛转研媚,乃欲过之…”之后大受称赞,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从此声名鹊起,一时胜过乃父。
韩可孤哪里会不明白李民话中的深意,不觉微微一笑“这故事倒也有些借鉴之处,只是到了我这越传越神,未免让人不太好意思了。”
“大人此言差矣,想那王献之是自说自话,而大人您确实街头所传,非是自我标榜,何来难堪。况且,这也正反应出了人心向背,多少古人正是托了神迹仙传而成其大事的,学生倒觉得这段故事传的越神越远才对,与我大辽中兴越是有利。”
韩可孤一笑置之,再不在此事上多做纠缠,李民却只要逮到机会就会大大的谈论上一番,颇加上了些传奇色彩。
萧驴在旁听得百爪挠心的,忍不住又不停插上几句,众人正听得兴起,却被他打扰了听讲,便忍不住笑骂,李民和他处得久了,倒能从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里分析出十之**,便止了大家笑骂,接着说下去:
“不知各位是否也曾听说过,韩公乡里的那座二郎担山,那一年韩公诞辰之日有一只青牛,自那里穿过去,投到了韩公家中,恰那时韩公落地,但见满院子的红光耀眼,人都说韩公是青牛转世,是先祖派下来佑我大辽的,自然有各路神仙保佑,哪会轻易地被摔死—一”
众人接了话便纷纷议论起来。
众人磋叹不已,利民县同知陈敬抚掌道:
“韩公的这桩奇事,很是感染人的,本县治蹑的许多百姓多在传言,韩公诚能感招,乃上祖遣来佑我大辽中兴的仙家来朝。所以,这段时日来,投军效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