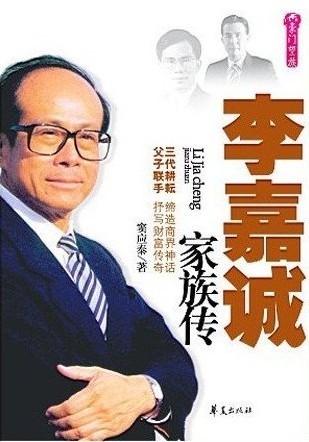患难与忠诚-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好哇!”他叫道,“原来你是站在他们一边。你也要逼我当神父。事情终究是要这样或那样了结的。我父母亲是丝毫不爽地恨我,而我爱的人却只是打趣地爱我。”
说完这刻薄而毫不理智的话之后,他便愤然跑回家去,留下玛格丽特伤心地哭泣。
假如一个男子忽然表现出举止失度,这对真心爱他的姑娘所产生的影响确乎是很微妙的。这会使她怜惜他。在我们一些男子看来,这似乎一点不合逻辑。事实上,这要怪我们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个逻辑推理过程太快,我们的眼睛跟不上。姑娘是这样推断的:“可怜的——他该是多么不幸福,多么生气啊。他竟然举止失度了!可怜的宝贝!”
玛格丽特正满怀着这种甜滋滋的女性的怜悯心,忽然十分惊奇地看到离开她还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杰勒德手里拿着一张画像的碎片,气急败坏而又痛心地跑了回来。
“瞧,玛格丽特!瞧!这些坏蛋!你看他们有多狠毒!他们把你的像剪成了碎片。”
玛格丽特一看,果然如此。一个恶毒的家伙把她的像剪成了五块。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子,但也不是冷血动物。她的脸一下子红到了额顶。
“谁干的?”
“我不知道。我不敢问,因为直到我死那天,我都会痛恨干这事的家伙。我可怜的玛格丽特!这些屠夫!这些恶棍!六个月的工作被他们从我的生命中剪掉了,现在是毫无成绩可言了。看,他们竟从你的脸上剪过去。这是一个谁见了都喜爱的温柔而美丽的脸蛋啊!没心肝的残酷无情的毒蛇!”
“不要紧,杰勒德,”玛格丽特气吁吁地说道,“为了我的缘故,他们这样对待你——你们不是从杰勒德手上夺走了我的肖像吗?好吧,既然如此,他将完整无缺地得到他画过的活的面孔。”
“啊,玛格丽特!”
“是的,杰勒德。既然他们那样无情,我就要更加有情:请原谅我拒绝了你。我将做你的妻子,如果你高兴的话,明天就可以。”
杰勒德欣喜若狂地吻她的手,又吻她的嘴。然后在欢乐的激情中跑去叫彼得和马丁。他们前来为订婚礼作证。在那个时代,甚至一个多世纪以后,订婚礼都还是一个庄严的仪式,尽管现在已经不时兴了。
第十章
教堂的结婚告示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样,当时也是得宣读三次。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一般是在周日宣读。这对年轻人很容易地说服了神父将这一必要的手续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进行完毕,因为神父是个新来的人,而他们的外表也对自己有利。结婚告示在星期一的早祷和晚祷时进行了宣读。使他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科学的哲学。以实证哲学观点研究社会现象,1839年提出了,教堂里没有一个特尔哥人。第二天早晨,他们两人都心悸不安地站在教堂里。忽然,他们十分恐慌地看到一个陌生人站起来制止婚礼,理由是结婚的双方都未成年,而且他们的父母都不同意。
在教堂大门外,玛格丽特和杰勒德颤抖着进行了一番近乎绝望的商议。但还没等他们商定出一个办法,那个对他们干了如此罪恶的一招的坏家伙走了过来,示意他们,他对他的干预非常抱歉。他说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总结了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阶级斗,他的本心还是愿意促成年轻人的幸福的,但事实上他惟一的谋生之道就是制止婚礼。那么,怎么办好呢?“年轻人,你们给我一个金克郎,我就漂亮地消除这事的后果,告诉神父说我情况了解错了,这样一切都会顺利了。”
“一个金克郎!我愿给你一个金安琪儿去办好这件事!”杰勒德急切地说道。那人也同样急切地表示同意。接着他便和杰勒德一道去见神父,告诉他说自己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由于看清楚了结婚双方才得到了纠正。听到这样一说,神父便同意次日十点为年轻的情侣再主持婚礼。而那位以阻挠别人幸福为职业的专家便揣着杰勒德的金安琪儿回家去了。但正像大多数脑袋灵光的恶棍那样,他义是一个蠢猪。他竟然在特尔哥某家酒店里为庆祝他的金安琪儿喝起酒来。酒店附近有个专供射箭和其他流行的体育活动用的草坪。由于他喝醉了学任教。1945—1948年当过法国驻梵蒂冈大使。断言为基督,便在那儿吹嘘他一天的业绩。谁想到,在那儿一字一句倾听着的竟正巧是那家酒店的常客,无赖的西布兰特。西布兰特跑回家去想报告他父亲。父亲不在家,他到鹿特丹向商人买布去了。看到他哥哥望着他,他便向他打了个手势要他出来,并把他刚刚听到的告诉了他。
几乎在每个大家里都有孬种。而这两个就是杰勒德的孬弟兄。懒惰是败坏品德的,而期待我们应当爱的人早点死也是败坏品德的。这两个一心想发财的狗杂种,准备把任何敢于涉足他们朝思暮想的可怜遗产的人活活撕死。他们父母的节俭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伴随着勤奋,而其动机是对子孙的爱护。但在那两个乖戾而自私的心灵中作为可能性进入一定的事态中并与其他永恒客体发生关系。,这一朴素的美德却被歪曲成为贪婪,而在人性中谁也找不到比贪婪更丰富的罪恶源泉。
他们在一起碰头商量后,都同意先去找市长,而不告诉母亲,因为她的思想感情很不固定。他们的狡黠足以使他们看出市长是厌恶这门婚事的。不过,他们还猜不出是什么缘故。
盖斯布雷克特·范·斯威顿一眼看穿了他们的来意。但他注意不让他们看穿他自己。他听着他们打的小报告,然后摆出市长的威严和冷漠的表情说道:
“既然一家之长不在,那么他的责任就落在我这个一市之长的人身上了。我知道你们父亲的主意,把这一切都交给我好了。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对任何女人透露一个字,特别是不要对你们家的女人说一个字,因为饶舌的人会把最聪明的主意给破坏掉。”
他略表倔傲地把他们打发走了。对这样两个同伙他不免感到害臊。
他们回到家时,看到杰勒德正坐在母亲膝边的一个矮凳上。她用手抚摸他的头发,非常慈祥地对他说着话,答应在他父亲跟前袒护他,而不再阻挠他恋爱的事。回心转意的主要原因是很能说明这位妇女的特点的。正是她一时妇人脾气发作,把玛格丽特的肖像剪成了碎片。她曾相当不安地注视着产生的后果。她看到杰勒德变得面无人色,像死了亲人似的坐着不动,手上捧着画像的碎片,眼睛痴呆地望着它们,直到眼泪夺眶而出,遮住了他的视线。起先,她对她于的这事感到恐慌,接着她的良心痛楚地鞭苔着自己,便躲到一旁痛哭。她就是那样一种性格。但她不敢公开承认,只是对自己说:“我什么也不说。但我要补偿他的损失。”她那仁慈的心肠转而恳切地向着她的儿子。她那虚弱的横暴也已寿终正寝。当那两个不肖之子回来的时候,她正把她那举足轻重的结盟关系转移到杰勒德方面。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杰勒德毫无所知。由于他对女性内心的详细活动缺少经验,母亲的慈祥反使他因为曾经怀疑她毁了画像而感到惭愧。他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她,上床睡觉时快活得像个王子,因为他想到母亲在他命运的紧要关头,再次表明仍旧是他的母亲。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杰勒德和玛格丽特坐在塞温贝尔根的教堂里。男的容光焕发,喜形于色;女的面颊绯红。彼得也在教堂里,还有马丁·威顿哈根,此外就别无亲友了。婚礼的秘密性高于其他一切的考虑。玛格丽特已拒绝去意大利。她离不开她的父亲,因为他太学究气,太不能照料自己。但他们已决定要到弗兰德去躲避几个星期,待风波平息后再回特尔哥。神父并没有使他们久等,不过他们觉得仿佛等了一个世纪。不多一会,他已站在圣坛旁边,叫他们过来。他们手牵手地走着,真可说是荷兰最幸福的一对。神父打开了他的祈祷书。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宣告神圣的婚礼开始,便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叫道:“别搞了!”只见特尔哥的衙役沿着教堂的过道走了上来,并以执法的名义逮捕杰勒德。马丁马上抽出他那把明晃晃的长刀。
“住手!”神父叫道,“你要干什么!胆敢在教堂里抽出武器。而你们这些当差的竟然打断了这个神圣的婚礼。如此冒犯神明意味着什么?”
“不是冒犯神明,神父。”市长的衙役恭敬地说道,“这年轻人想违背父亲的意志私自结婚。他父亲曾请求市长依法处理。要是他能否认,就让他站出来否认吧。”
“是这样吗,年轻人?”
杰勒德低着头。
“我们要把他带到鹿特丹去接受公爵的判决。”听到这话,玛格丽特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叫声。不久以前还是那么幸福的一对年轻情侣,这时却抱在一起如此动人哀怜地哭泣起来,以致那些压迫人的工具也不禁退后了一步,感到羞愧。其中有一个性格善良的,借口要把他们分开,走上来对玛格丽特耳语道:“鹿特丹?骗人的!我们只不过要把他带到市政厅去。”
他们把他押上马带走,先是沿着去鹿特丹的大路,但停顿了十多次之后便狡猾地绕道回特尔哥。快进城时,他们碰到一个帆布篷的简陋马车。杰勒德被投进马车,于黄昏五点左右被秘密地关进市政厅的监狱。他被带上几层楼梯,然后被推进一间只有一个狭小窗口透进光线的小房间。窗上安有一根垂直的铁杠。室内全部家具只是一个大的橡木柜。
在那个时代,监禁是最容易通向死亡的路径之一,即使是以最温和的形式出现也是可怕的。它意味着寒冷、无休止的孤独、折磨、饥饿以及经常发生的服毒自杀。杰勒德感到他落进了敌人的魔掌。
“啊,在去鹿特丹的路上那老家伙望我的那一眼多么狠毒!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我父亲的愤怒。我看我不会重见天日了。”说着他跪了下来,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上帝。
忽然,他站起身子向那窗上的铁杠跳过去,牢牢地抓住它。这使他能够通过膝盖紧贴着墙壁向外观看。虽然只看了片刻,但就在那片刻之内,他看见了惟有囚徒才会注意到的东西。
马丁·威顿哈根的背脊。
马丁正在市政厅附近的一条小溪边不动声色地坐着垂钓。
杰勒德又跳到窗前,打起口哨。马丁很快就表明了他所专心的是观察动静,而不是钓鱼。他赶忙转过身去,看见了杰勒德,给他打了一个手势,然后收起他的钓鱼线和弓迅速走开。
通过这一事实,杰勒德看出他的朋友们并没有袖手旁观。不过,他宁愿马丁留下来。能看见他就是一种安慰。他继续握着铁杠,尽可能多看一眼老兵正在消逝的背影。然后,他心情有些沉重地退了回来,着手将那根用生锈的钉子钉住的锈铁杠从石砌的窗台上拔出来。这时,盖斯布雷克特·范·斯威顿正好悄悄地在他背后开门进来。市长的目光立刻落在铁杠上,然后落在窗子上,但他什么也没有说。窗子离地面有一百英尺。如果杰勒德心血来潮想跳出去,他干吗要阻拦呢?他带来了一块褐色面包和一壶水,板着脸一声不响地放在柜子上。杰勒德涌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用铁杠砸破他的脑袋,然后奔下楼去。但市长看见他的目光中有某种凶兆,轻轻咳了一声,马上便有三个棒实实的武装衙役出现在门口。
“我命令把你一直这样关下去,直到你发誓抛开玛格丽特·布兰特,回到教会为止。要晓得,你从摇篮时代起就已经属于教会了。”
“宁死也不干。”
“那好吧,我是仁至义尽了。”说着,市长便扬长而去。
马丁飞速地奔回塞温贝尔根。他看到玛格丽特面色苍白,心情激动,但充满了决心和力量。她正在结束一封给伯爵夫人夏荷洛伊丝的信,恳求她干预盖斯布雷克特的阴谋和暴行。
“别泄气!”马丁一进来就喊道,“我已经找到了他,就关在闹鬼的高塔顶楼上。我可知道那鬼地方。许多可怜虫直着走上去,而脚朝前躺着出来。”
然后,他告诉他们他怎样抬头一望,在一个窄得像墙上一条缝的窗子跟前看见了杰勒德的面孔。
“啊,马丁!他是个什么样子?”
“你是什么意思?他就是杰勒德·伊莱亚斯那个样子呗!”
“脸色苍白吗?”
“有点。”
“看起来很着急吗?像注定要见上帝的样子吗?”
“不,不,看起来就像一个锡酒壶那样亮锃锃的。”
“你在取笑我。等等!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一定是看见了你。他在指望我们。啊,我们该怎么办呢?马丁,好朋友,请你马上把它送到鹿特丹去。”
马丁伸手去接信。
彼得一直在默不作声地坐着,沉思着,而且一反常态,在密切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
“别依赖那些王公贵族了。”他说道。
“哎呀!那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可信赖的呢?”
“知识。”
“真亏您说的,爹!您的学问在这儿帮不了我们的忙。”
“你怎么晓得呢?从前人们就曾经用机智战胜过铁栅。”
“不错,爹。但机智硬不过客观存在。而后者对我们是不利的。想想看有多高吧!全荷兰没有一个梯子够得着他。”
“我用不着梯子。我需要的是一个金克郎。”
“不行的。钱我倒是有。我有九个金安琪儿,是杰勒德交给我保存的。但钱有什么用呢?市长又不会受贿释放杰勒德。”
“有什么用?你只消给我一个克郎,那年轻人今晚就会和我们一道吃晚饭。”
彼得说得如此急切而有信心,以至玛格丽特一时也感到有了希望。但她看到马丁眼里却老是带着一种善意的轻视的表情望着她。
“这超过了人的想像力。”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想象!”老人叫道,“去你的想象!这个时候了还谈什么想象?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我想讲给你们听,从前有个佛罗伦萨的骑士,被关押在一个比关杰勒德的塔更高的塔里。他忠实的扈从的确是站在塔底下把他救了出来,而他使用的工具,马丁,正是你手上握着的那个,再加上我将用一个克郎买来的一点小玩意。”
马丁望望他的弓,把它在手上转了两下,似乎在审问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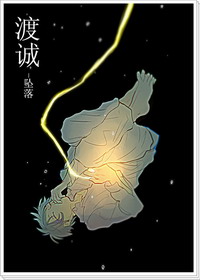
![[主欢乐颂]阿诚的欢乐(悚)之旅[伪装者]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447.jpg)